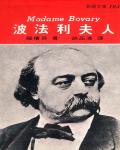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一部
2
由於心靈的疲倦,沙勒沒有再去貝赫多。在嗚咽了很久之後,在吻了他多次之後,在表露了偉大的愛情之後,艾洛薏絲叫他把手放在經文本上發誓不再去。於是,他服從她,但是他內心慾望之強烈與他外在行為之卑恭無法抗衡。由於一種天真的偽善,他認為對他來說抑制自己見她是一種愛她的權利。而且那寡婦很瘦,牙齒又長,她一年四季披著一塊圍巾,尖端在兩肩之間垂下,她僵硬的身材被太短的,像劍鞘的衣裙裹著,露出雙脛以及寬大的鞋,鞋帶在灰色的襪子上交叉地繫著。
「胡歐特的女兒是城裡人?算了吧!他們的祖父是牧羊人,他們有一位表親曾經在一場爭吵中做了壞事,幾乎被法庭審判為重罪。不必那麼神氣,也不必在星期天穿綢子衣服去教堂,像一位伯爵夫人。而且,假如去年沒有油菜收成,那可憐的老傢伙原會難於清理債務。」
那封用藍色火漆封口的信央求波法利先生立刻前往貝赫多農莊去接骨,因為有人斷了腿。可是,從多斯特到貝赫多,即使是經過龍格維勒和聖維克多繞捷徑走,也有六里的路程。波法利太太怕丈夫出事,於是決定讓馬夫先走,等三小時後,月亮昇起時,沙勒再動身,那時,對方會派一個小孩子來接他,為他帶路,為他開柵欄門。
一聽見沙勒肯定的回答,他就穿上鞋子,向沙勒迎面跑去。
當沙勒上樓去向那位父親道別後,動身走進到廳堂裡的時候,他看見她是站著的,額頭貼在窗子上,望向花園。園子裡的豆架已經被風吹倒了。她轉過身來。
那是一座非常體面的農莊。從敞開著的門的上方可以看見那用來耕作的肥馬靜靜的在新馬槽裡吃東西。一些建築物的牆邊堆著一大堆冒出煙來的肥料。院子裡除了雞和火雞等家禽之外還有五六隻名貴的孔雀高高地啄食。羊柵是長形的,倉房很高,牆壁卻很光滑。車棚下有二輛大型送貨車,四把犁頭以及全套的裝備,像鞭子等等。由頂樓落下的灰塵弄髒染成了藍色的羊毛皮。院子是有傾斜度的,越上越高,栽著一些樹,樹和樹之間的距離都是對稱的。池塘附近,迴盪著鵝群歡樂的聲音。
而且,一切都很順利。病人按照常規地恢復了健康。四十六天以後,當人們看見老胡歐特試著單獨在「陋室」裡行走的時候,波法利先生被大家視為能力很強的人。老胡歐特說伊伏多或是甚至盧昂的第一流醫生的醫術也不會比他的更好。www.hetubook.com.com
沙勒的母親不時來看他們夫妻兩個,但是幾天以後,婆媳二人針鋒相對,像兩把刀子似的,妳一句,我一句。犧牲者卻是沙勒。他不該吃那麼多!為什麼老是把藥水送給別人?為什麼那麼固執,不肯穿法蘭絨的衣服?
傷口包紮好了以後,胡歐特先生親自請醫師吃了便飯再走。
他開始尋覓,床上、門背後、椅子下面。鞭子掉在地下了,在麥袋和牆之間。艾瑪小姐看見了那鞭子,俯身向麥袋。由於對女性的禮貌,沙勒搶先去拾鞭子。因為他也在伸手做同樣的動作,他感到自己的胸口輕拂著那在他下面彎著腰的少女的手背。她羞紅著臉再站起來,從肩膀上看他,一面把牛筋鞭子遞給他。
她對自己說:「這就是為什麼當他去看她的時候容光煥發,為什麼他穿新背心,不管會不會有被雨淋壞的危險。啊!那個女人!那個女人!」
但是她病根扎下了。八天以後,當她在院子裡晒衣服的時候,吐了一口血。第二天,當沙勒轉過身去拉窗簾的時候,她說:「啊!我的上帝!」嘆了一口氣,暈倒了。她死了!多麼令人驚訝!
沙勒驚訝於她的手指之潔白。她的手指甲尖端很細,修成杏仁形,又亮又白,比迪葉浦城的象牙還乾淨。可是她的手並不漂亮,也許不夠白。指骨部份也是乾乾的。同時她的手也太長,沒有柔軟的線條構成美好的輪廓。她身上最美的部份是眼睛。雖然是棕色的,但由於睫毛的顏色,棕色眼睛看起來像黑色的。她的目光坦率而又大膽,直直地射向所有的人。
她的脖子露在一條白色翻領的外面,頭髮中分,兩邊的頭髮很光滑,看來像一整片似的。順著頭的形狀,那條中分的線由前面向後傾斜下去,兩側的頭髮幾乎蓋住耳朵。那兩片頭髮在腦和圖書後結成一個大髮髻,鬢邊則呈波浪形。有生以來,鄉村醫師是第一次看見那種髮型。像男人一樣,她在上衣的兩枚鈕釦之間掛著一付玳瑁眼鏡。
辦完喪事以後,沙勒又回到家裡。他發現樓下沒有人,走上二樓的臥室,看見她的衣裙仍然掛在床前。於是,他靠著書桌,一直在痛苦的夢幻中呆到黃昏。畢竟,她曾經愛過他!
沙勒頭幾次去貝赫多農莊看病的時候,他妻子總會問一聲病人的情況。甚至在她的雙份記帳簿上為胡歐特先生保留美麗的、潔白的一頁。但是當她知道他有一個女兒的時候,她就去刺探消息,也因而知道胡歐特小姐曾在雨赫胥林會的女修道院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會跳舞,學過地理,會畫畫,會刺繡,會彈鋼琴。真氣死人!
她老是送他到臺階上的第一級。假如馬還沒有牽來,她就停留在臺階上。他們已經道別,不必再說話。大風吹襲著她,把她後頸上的頭髮吹得很零亂,或是吹動臀部的圍裙帶,那圍裙帶像小旗子般扭曲著。有一次,在解凍時期,院子裡的樹皮正在滴水,屋頂上的雪正在溶化。她站在門檻上,然後去找小陽傘,撐開傘。太陽穿過鴿子頸顏色的絲質陽傘,用流動的光照著她白哲的險。在傘下,她向著溫暖微笑,聽見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張開的傘面上。
他原先答應了三天以後再來貝赫多,但是第二天就來了,然後,很正規地每星期來兩次,除此之外,有時也像是不經意地路過,作一次不預期的訪問。
那是單純的骨折,並不是複雜的那種。沙勒不曾奢望比那還更簡單的骨折。他回憶老師們在受傷者床前的樣子,用所有的好話安慰病人,那些話是外科上的慰語,也像是用來塗抹割切刀的油脂。為了要護骨板,沙勒去車身下面找了一包板條。他選了一條,切成幾塊,用一塊破玻璃把它磨光。女傭人則把一塊布撕成布條,艾瑪小姐則試圖縫小墊子。因為她老是找不到針筒,父親發脾氣了。她什麼也不說。縫著的時候,她被針刺傷了手指。為了吮血,她把手舉向唇邊。
醫師和那少女首先是談病人,然後,談當時的嚴寒天氣以及夜晚在鄉野奔跑的狼群。胡歐特小姐不喜歡鄉村,尤其是現在,因為她幾乎https://www.hetubook.com.com是一個人負責農莊的管理。廳堂裡狠冷,她一面吃飯,一面冷得發抖。往常,當她沉默的時候,她有咬嘴唇的習慣。由於發抖,一部份豐|滿的嘴唇便露在外面。
「對不起,找我的馬鞭。」他說。
至於沙勒,他一點也不試圖知道自己為什麼那麼樂於來到貝赫多農莊。假如他曾經想過,他也一定會把他的熱心歸諸病況之嚴重性,或是他希望其中有利可圖。然而,真是為了上述原因他才覺得在他辛苦的日常業務之中去貝赫多農莊治病是一種迷人的例外嗎?那些日子,他起得很早,鞭策他的馬快跑,然後下馬,在草上擦皮鞋,在進門之前還戴上黑手套。他愛看自己到達院子裡,興奮地感到自己的肩膀依著轉動的柵欄門,在牆上啼喚的雄雞以及來迎接他的男工。他喜歡那兒的倉房和馬槽,喜歡那個一面拍他的手,一面叫他救星的老胡歐特,他喜歡站在廚房裡的乾淨石板上的艾瑪的小靴,高跟鞋使她顯得高些。當她走在他面前的時候,快速地踮起來的木底衝著靴子的皮革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凌晨四時左右,沙勒穿上大衣,把身子裹得緊緊的,上路去貝赫多。熱被的餘溫使他仍然昏昏欲睡,於是他讓馴良的馬搖醒著他。路上有一些車轍,車轍旁邊有一些被荊棘包圍的窟窿。當馬在窟窿前面停下來的時候,沙勒被驚醒了,立刻想起了那折斷的腿,試著記憶他所知道的一切關於骨折的狀況。雨停了,天也開始亮了。那沒有葉子的蘋果樹枝上,棲息著一動也不動的鳥群,在寒冷的晨風中豎起牠們的羽毛。平坦的鄉野伸展著,一望無際。在一些農莊的四周,稀稀疏疏的樹群在廣大的灰色的地面上形成一些深紫的斑點。灰色的鄉野伸展到天邊,地面共長天一色,同樣是灰灰暗暗的。沙勒不時睜開眼睛,然而,由於心靈疲倦,睏了,他不久又進入昏睡的狀態中。在那狀態中,目前的感覺和回憶混在一起,他看見雙重的自己.同時是學生也是丈夫,像剛才那樣睡在雙人床上,又像從前那樣穿越開刀房。在他的腦子裡混融著溫暖的敷藥味和綠色的露水味。他同時聽見他妻子睡覺和病床的鐵輪子滾動聲。當他經過瓦索維勒的時候,他看見一個男孩
hetubook.com•com坐在水溝旁邊的草地上。在路上,從嚮導的言談中,那醫生知道胡歐特該是一個最富裕的莊稼人。前夕晚上,他在一個鄰居家過三王節。回來的時候折斷了腿。他的妻子兩年前就死了。只有「小姐」在他身邊,幫忙主持家務。
初春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安古城一位律師事務所的代書——杜布克寡婦的財產保管者——趁著漲潮坐船走了,騙走了事務所的全部財產。除了一艘價值六千法朗的船的股票以外,艾洛薏絲在聖佛杭司瓦街還有一棟房子。有人大吹特吹地說她多麼富有,然而除了一點家具和裝飾品以外,她什麼財產也沒有帶到夫家來。在迪葉浦城的那棟屋子連打地基的椿子都抵押出去了,只有上帝知道她存了多少錢在律師那兒,船的股票不超過一千銀幣。那麼,那婆娘撒了謊!盛怒之下,老波法利先生在磚地上摔破了一張椅子,一面罵他妻子害了兒子,又在他的車上拴了一匹駑馬,駑馬也應該有更好的韁繩,然而並非如此。兩老來到多斯特,大家解釋時,吵了一架。艾洛薏絲哭著投入丈夫的懷中,求他幫忙對抗他的雙親。沙勒想為她說好話,父母一生氣就走了。
「你是不是來找什麼東西?」她問。
有一天晚上,十一點左右的時候,他們被恰巧停在門口的一陣馬啼聲驚醒了。女傭人開了頂樓的天窗,和一個停在樓下街上的男人說了一會兒話。他是來接醫生的,帶著一封信。拿絲達西打著寒顫走下樓,開了鎖又開了門閂。那男人扔下了馬,突然跟著女傭人走進了屋子。他從有灰色冠毛的瓜皮帽下面抽出了一封用布包著的信,小心地交給沙勒,後者用肘子把自己撐在枕頭上讀。「太太」由於害羞把背轉向信使,面對著街。
「你是醫師嗎?」那孩子問。
沙勒走到樓下的客廳裡。那兒放著一張有帷幕的大床,帷和-圖-書幕是用印度棉織印花布做的,上面印著土耳其人物。床前有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放著兩份餐具,和一些半圓形的銀杯。有蝴蝶花的氣息,有潮濕的床單味道,那濕布味道是從一個很高的、面向窗子的橡木衣櫃發出的。在屋角裡的地上,豎著一袋一袋的麥子,那是倉房裡裝不下的麥子,倉房就在近處,有三級石階通向那倉房。牆是淡成綠色的,有一方牆的油漆正在硝石下剝落。在那方牆中央的一個釘子上掛著一幅畫,裝飾著屋子。那是一幅黑色鉛筆畫,畫面上是智慧女神的頭。畫框是鍍金的,下面有用花體字母所寫的題詞:「給我親愛的爸爸」。
本能地,她恨那個女人了。首先,她只是藉暗示來表達。但沙勒並不懂那些暗示。然後她像是不經意地直說出來,為了怕引起一場大吵大鬧,他裝作沒聽見。終於,她像連珠炮似的詰問他,既然胡歐特先生的病已經好了而且還沒有付錢,為什麼還要再去貝赫多?啊!因為那兒有個人,一個能言善道的女人,一個會刺繡的女人,一個有學問的女人。這就是他喜歡的:他要一個都市裡的女人。她又說:
車轍變得越來越深了。貝赫多就快到了。那小男孩從籬笆的一個縫隙裡鑽了進去,從院子的另一端出來打開柵欄門。馬在濕漉的草地上滑行,沙勒低著頭從樹枝下走過。看家狗開始吠叫,一面想掙脫拴住牠的鍊子。當他走進貝赫多農莊的時候,他的馬嚇壞了,然後退得遠遠的。
走到門口來迎接波法利先生的,是一位穿著藍絨布三疊裙的少女。她把他帶到了廚房裡,那兒灶火熊熊。傭人們的午餐菜在大小不同的鍋裡沸騰,灶頭晾著一些濕衣服。巨大的吹筒、鏟子、箝子,像擦過了的銅一般發亮。沿牆堆著一大排廚房用具,上面映照著灶裡的火焰和從窗玻璃上射進來的晨曦。
沙勒上到二樓去看病人。他看見病人躺在床上,在被子下面流汗,把棉布帽子丟得很遠。病者是一個五十歲的矮胖子,皮膚很白,眼睛深藍,前額是光禿的,而且戴耳環。在他身旁的一張椅子上,有一大瓶燒酒,他不時喝一口,給自己增加勇氣。但是當他一看見醫生,就顯得興緻低落了。有十二小時的功夫,他一直呼天罵地,現在他不再那樣了,而是虛弱地呻|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