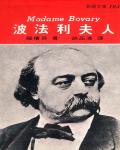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二部
6
「什麼樣的消遣?」
「你說得對,」藥劑師插嘴說,「毛病就在這裡。在金錢方面你必須時時提防。我假定你在公園裡,一個衣著考究,佩戴勳章的人走過來,向你自我介紹,你會以為他是一個外交官。他和你搭訕,你和他交談,他用委婉的話語打動你,請你用一撮鼻煙,為你拾起帽子。然後,你們交往得更密切,他帶你去泡咖啡廳,請你去他的鄉村別墅,在兩杯酒之間,使你認識形形色|色的人,然而大多數的時候,只是騙你的錢,或是引誘你去幹一些邪惡的勾當。」
「別來煩我嘛!」她說,一面用肘子推開她。
然後,他就走進教堂,先在門口做了一個跪姿。
「他!」她做了一個輕蔑的姿勢。
他們彼此向前走了一步,他伸出手,她遲疑了。
「好!」他說,「我們今天總算是把我們的年輕人打發走了。」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嘆著氣。
但是女傭人把貝特帶來了。後者低著頭,搖著一個拴在繩子上的風車。
她抓著扶手上了她家的樓梯。進了臥室以後,一下倒在一張沙發椅裡。
最困難的是獲得母親的同意。然而再也沒有比這更順理成章的事。連上司也勸他進另一事務所,在那兒他更能發揮才能。於是他採取一個折衷措施,打算在盧昂謀一個二等見習律師的位置,卻沒有找到。於是他給母親寫了一封長長的、詳細的信,解釋他為什麼立刻要去巴黎,母親同意了。
蒼白的日光波動著,從玻璃窗上慢慢地落下。家具顯得更靜止了,失落在陰影中,像失落在黑暗的海洋裡。壁爐裡的火已經滅了,鐘永遠響著,艾瑪茫然地驚訝於事物的寧謐——當她的內心卻如此動亂的時候。但是在窗子和女紅桌之間,穿著毛線靴子的貝特在搖搖晃晃地走,試著走近媽媽,想抓住她圍裙帶子的尖端。
沙勒叫她放心,情況並不嚴重,他去找橡皮膏。
這種恐懼很快就變成不耐煩。於是巴黎在遠處向他奏起化裝舞會的音樂,爆出年輕女工的笑聲。既然他應在巴黎讀完法律,為什麼不現在就去?誰在阻止他?他開始在心裡作準備,預先安排生活。他在腦子裡為自己佈置房間。他要在那兒過藝術家的生活。他要在那兒學吉他,他要有一件睡袍,一頂巴斯克地區的帽子,和藍絲絨的拖鞋!他甚至已經在欣賞壁爐上兩把交叉的鈍劍以及上面掛著的一個骷髏和一把六弦琴。
「一路順風。」
「不是他們……」
「可憐的雷翁!」沙勒說,「他在巴黎怎麼生活呢?……他能習慣嗎?」
貝特摔倒在五斗櫃腳下,正好碰著銅環,劃破了臉上的皮,流血了。波法利夫人跑過去把她扶起來,拉斷了掛鈴的繩子,使出全身的氣力叫女傭人,正想大罵,恰巧沙勒出現了。那是晚餐時間,他回家來了。
她的樣子把孩子嚇哭了。
「別說了,波法利夫人!就是今天早晨我還不得不去南迪尤鎮,為了一條生了病的母牛,他們以為是上天降禍。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全部的母牛……對不起。龍格馬,布德!廢紙袋!你們有完沒完?」
然後她用腳跟轉了一百八十度,像一尊雕像順著軸子轉,走上了歸途。但是神父重濁的聲音,孩子們清脆的聲音依然到達她耳邊,在她背後持續著:
「是的,」她說,「你緩和一切痛苦。」
他把教理問答塞進口袋裡,停下了,一面把聖衣室的笨重的鑰匙夾在手指之間搖來搖去。
「先生不在家嗎?」他說。
「我想吻貝特。」雷翁說。
最後,沙勒關上了門,請雷翁親自去盧昂打聽一張美麗的銅圖的價錢。那是沙勒要給妻子的一個感情的驚喜,一份細心巧思。他要把自己穿黑禮服的畫像送給她。但是他要事先知道該花費多少。這件事不至於太麻煩雷翁,既然他幾乎每星期進城。
他又回到艾瑪身邊,打開他的印花布大手絹,用牙齒咬住一個角,一面向她說:「哎!農人真可憐。」
「什麼消息?」
「我曉得是你。」
「我有話告訴你。」沙勒在見習律師耳邊輕輕地說,後者下樓的時候走在他前面。
「哎!他該走得很遠了!」她想。
波法利夫人不想下樓,她要一個人守住孩子。看孩子睡著了以後,她才安心,而且覺得自己真笨,居然為這麼一點小事煩心。貝特不再哭了。現在,她的呼吸不知不覺地在掀起棉布被。她半閉著眼睛,眼角上還殘留著大滴大滴的眼淚。睫毛之間露出兩顆蒼白的,深陷的眼瞳,貼在臉上的橡皮繃帶斜斜地拉緊著皮。
雷翁在手指間感覺到她,他覺得整個人都墜入了那濕潤的手掌。
波法利夫人打開了面對花園的窗,似乎在看雲。
「晚安,」紀尤曼回答說,「走吧!」
「妳真要他們變成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西印度群島或印第安的土著嗎?」
「怎麼?沒有關係?我倒覺得穿得暖,吃得飽的人……總之……」
艾瑪打了一個寒顫。
雷翁對沒有結果的愛感到厭倦。他也感到厭煩,因為生活千篇一律,他討厭沒有興趣、沒有希望的生活。他討厭雍維勒鎮和鎮上的人。一看見某些人,某些房子,他就不能忍受。藥劑師雖然是個老好人,也完全變得不可忍受。然而,一種新的情況既吸引他也使他害怕。
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又說:
「我想知道……」她說。
「你家有什麼事嗎?」
「你瞧,親愛的,」艾瑪用鎮定的聲音說,「那孩子在地上玩,摔破了臉。」
一如往常,歐梅先生六點鐘來了,正是晚飯的時候。
晚飯後,沙勒去藥房退還剩餘的橡皮膏。十一點鐘回來時,他發現妻子站在搖籃面前。
她向四周環顧,目光慢慢地落在那穿道袍的老人身上。他們相對無言。
「啊!你知道那消息嗎?」
「假如我是你,我去弄一個切木機。」
「啊,那倒是真的。」稅務員摸著下巴說,滿足之中帶著輕視。
的確,神父住宅的門響了,布尼賢神父出現了。在教堂裡的孩子們亂轟轟地逃走了。
「是的,我是基督徒。」
他終於說道:「那麼,請原諒我,波法利夫人。妳知道,職責高於一切,我必須把那些小鬼打發走。領第一次聖餐的時間到了。我怕我們會落在後頭!因此,打從升天節起,我要他們每星期三多上一小時課,決不通融。這些可憐的孩子們!引導他們走向天主的道路永遠不會嫌太早!而且祂不是曾經藉祂的聖子之口吩咐我們這麼做嗎?……祝妳健康,夫人。請代我向妳先生致意。」
https://www•hetubook.com•com
「可是我不會使用。」見習律師說。
她轉過身去,低著下巴,伸出額頭。陽光在她額上滑行,像滑在大理石上,一直滑到彎彎的眉毛上,沒有人知道她在天邊望什麼,也沒有人知道她心裡想什麼。
可是那小女孩還是走得更近了,靠著她的膝蓋,一面用大大的藍眼睛望向她,同時一道乾淨的口水從嘴唇上流到她的絲圍裙上。
只剩下他們兩人。
「對不起,我沒有認出妳來。」
「不在。」
「我也不,」歐梅先生急忙地說,「但是他要和別人一樣,否則別人會把他當做是一位耶穌會的信徒。哎!你不知道拉丁區的小伙子們和女演員過什麼樣的生活。而且,學生在巴黎受人重視。只要他們有點才華,最上流的社會也邀請他們,聖日耳曼街有些貴婦人都愛上他們,結果,他們就有找到好對象結婚的機會。」
於是孩子們急急忙忙地圍住大書桌,爬上聖詩歌詠團團員的凳子,打開彌撒經本。其他一些孩子們躡著腳,鼓著勇氣走向懺悔室。但是,那牧師給他們每人一連串的巴掌。他揪住他們的衣領,把他們從地上提起來,重重地把他們放在唱詩班的石地上,好像要把他們栽在那兒。
「不能休息一分鐘,」他說,「永遠被鍊子鎖住!我出門一分鐘也不成!必須流汗流血,像一頭耕種的馬。真是一條窮苦的鎖鍊!」
雷翁在她脖子上吻了好幾下。
「因為妳剛才用手摸頭額。我以為妳頭暈。」
「他起了疑心嗎?」雷翁問自己。他的心在跳,且胡亂猜側。
然後,想了一會兒,他改變了話題:
背對著他的波法利夫人把臉貼在窗玻璃上,雷翁手裡拿著帽子,輕輕地用帽子敲著臀部。
「我?不問什麼……不問什麼……」艾瑪說。
神父不時望向教堂,所有的孩子們都已跪下,用肩膀彼此推擠,一個壓一個地倒下去,彷彿一排紙剪的修士。
「冬天沒有火嗎?」
「啊!」
他的腳碰到了一本又舊又破的教理問答,他一面拾起來,一面說:
他豎起眉毛,裝出一副最正經的樣子說:「下塞納區的農產品改良競賽會今年很可能在雍維勒舉行,至少大家這麼傳說。今天的早報也提了一句。那將會是我們鎮上最重要的事。不過,我們將來再談。我看得見,謝謝。雨斯丹有提燈。」
「妳不舒服嗎?」他帶著關懷的樣子往前走了幾步,「也許是消化不良?波法利夫人,妳應該回家,喝點茶提提神。或是喝一杯涼水,加點糖。」
上了樓以後,他在門口停了下來,覺得自己喘不過氣來。他進去的時候,波法利夫人急忙地站起來。
「就要下雨了。」艾瑪說。
有好幾次,沙勒曾經試圖打斷話題。
她在廣場上遇見了雷斯迪布多瓦,他正從教堂裡出來,為了不使他的日子化整為零,他寧可放下他的苦工,等一下再繼續,因此晚禱的鐘也隨他的方便去敲hetubook.com.com。而且早點敲鐘可以提醒孩子們教理問答的時間到了。
「也許是永遠忙吧?因為我和他一向是這教區裡最忙的人。不過,他是肉體的醫生,」他大笑著說,「我是靈魂的醫生!」
艾瑪走下幾級樓梯,叫費莉西特把貝特帶上來。
但是,他一看見波法利夫人就說:
「基督徒是什麼?」
「既然我說過沒有關係,」他一面說一面吻她的額,「別折磨自己,不然妳會把自己弄病的。」
「但是,」醫生說,「我有點為他耽心……那兒……」
他們走了,歐梅也回家去。
她咬了一下嘴唇,一股血在她皮膚下流動,她的臉全紅了,從髮根到領口。她一直站著,用肩膀靠著板壁。
波法利夫人嘆了一口氣。
「啊!」艾瑪說,「我需要的不是人間的藥。」
「別來煩我!」她說,一面用手阻擋她。
「好吧,再見!」他嘆了一口氣。
「妳身體好嗎?」他又問。
於是,他繼續發表他一般的見解和個人的同情,直到雨斯丹來找他做一碗牛奶蛋黃。
「我不相信他會亂來。」波法利先生反駁說。
「我有大衣。」他回答。
「是的,再見,走吧!」
「好像是!」醫生回答。
「對不起!我在城裡認識一些工人家的主婦,全部都是賢淑的,我向妳保證,真正的女聖人,而她們連麵包都沒有。」
「再見,可憐的孩子,再見,小親親,再見!」
「這些小頑童老是這樣。」神父抱怨說。
「啊!我也是,」神父說,「乍暖的天氣使人有氣無力,是不是?有氣無力得令人驚奇。可是,有什麼辦法?就像聖波勒所說的,我們生來就是為了受苦。但是,波法利先生的看法怎麼樣?」
歐梅俯身向防泥板,用夾著哭泣的聲音說出了這幾個淒涼的字:
有幾個孩子已經到了,在公墓的石板路上玩彈子。有的騎在牆上,搖著腿,用他們的木屐割著滋長在小空地和新墳之間高大的芒刺植物。那是唯一的綠地,其餘的都是石頭,儘管教堂裡有人打掃,石頭上卻永遠掩蓋著一層灰塵。
「不好,」艾瑪回答說:「我有病。」
艾瑪看見他在兩排長凳之間消失,輕輕地走,頭略微偏向肩膀,雙手向外攤開一半。
「別來煩我!」少婦又生氣地說。
然後他張開了手,他們的目光又相遇了,他終於走了。
「不在家。」
到了菜市場下面的時候,他停了下來,躲在一根柱子後面,為了向那棟白屋和它四扇綠百葉窗瞧最後一眼。他相信在臥室窗子後面看見一個人影。但是原來是兩邊分開的,被圓圈掛住的窗簾的斜褶子慢慢地動了,一下子全拉上了,直直的垂著,比一方石灰牆還更靜止,雷翁開始跑開。
她又說一遍:
艾瑪想:「真奇怪,這個孩子這麼難看!」
在公路上,他遠遠地看兒他的上司的馬車。上司身邊一個穿粗布衣服的男人在牽著馬。歐梅和紀尤曼在談話,也在等他。
那是四月初,迎春花已經開了。微風吹過掘好了的花壇。花園,像女人一樣,似乎在打扮自己,為了夏天的節日。透過涼棚的柱子,向遠處的四周望去,可以看見草原裡的那條河在草上勾畫出蜿蜓的線條。晚煙正在光禿的白楊樹間飄過,氤氳著一種紫色使白楊的輪廓變得朦朧,那顏色比掛在枝枒上的輕紗還要蒼白,還要透明。在遠處,家畜正在行走著,和-圖-書你既聽不見牠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牠們的叫聲。掛在牠們脖子上的鈴鐺一直響著,似乎在空氣裡延續了它寧靜的悲鳴。
「為什麼?」
臨到吻別的時候,歐梅太太痛哭著,雨斯丹嗚咽,堅強的歐梅先生並不表露他的情感,要親自把他朋友的大衣送到公證人的柵欄門口。公證人用車子送雷翁去盧昂。時間匆促,雷翁只剩下向波法利先生辭行的時間了。
母親向傭人說:「帶她出去。」
「算了吧!」藥劑師說,一面把舌頭弄得咯咯有聲,「在館子裡吃著鬧著,化裝舞會,香檳酒!樣樣有份,我向你保證。」
說那句話的時候,她像一個從夢中醒來的人。
「由於食物的改變,」藥劑師繼續說,「由於一般經濟導致的紊亂。巴黎的水,你是知道的。餐館裡的菜餚,以及一切有香料的食物都使人上癮。不論你怎麼說,那種食物比不上一盤素菜煮肉。至於我,我一向偏愛家常菜,比較衛生。因此,我在盧昂唸藥劑學的時候,我在一家宿舍包伙,同老師一起用餐。」
雲在西方匯集,在盧昂那邊,它們的流蘇迅速地翻捲,一大條一大條的太陽光從雲後面穿過,像一簇懸掛著的兵器中的金箭,而天空其餘的部份卻白得像瓷器。但是一陣大風吹彎了白楊,突然下雨了,淅淅瀝瀝地打在綠葉上面。然後,太陽又出來了,雞叫了,黃雀在濕潤的灌木叢中撲著翅膀,積在沙地上的水灘流著的時候,帶走了豆球花樹的粉紅落葉。
他把她交給母親。
一陣沉默,他們互相注視。混雜在一種痛苦的思想中,互相擁抱,一如兩顆跳躍的心。
「什麼?」那好心人驚訝地說:「他沒有給妳開個什麼藥方?」
他並不急。有一個月的功夫,伊維替他搬柬西,從雍維勒到盧昂,從盧昂到雍維勒:一些箱子,一些手提箱,一些包裹。當雷翁新定做了一大衣櫥的衣服,將三把沙發椅翻新,買了許多絲綢手帕,總之,準備了周遊世界也用不完的東西後,他還是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著行期,結果他母親寫了第二封信來催他動身,這樣他才可以在放假之前參加考試。
「神父在哪裡?」波法利夫人問一個小男孩,有柵欄的旋轉門太鬆了,那男孩在轉著玩。
為什麼進城?歐梅猜想那是年輕人的把戲,一種計謀,可是他錯了。雷翁沒有鬧戀愛。他從來沒有那麼憂鬱過,歐梅太太能從他剩在盤子的菜餚中覺察到。她想知道詳情,於是向畢內打聽消息。稅務員用傲慢的聲調回答說他不曾受警察的賄賂。
流著眼淚的藥劑師說:「吻我吧!這是你的大衣,我的好朋友。小心著涼!當心身體!好好保重!」
她用懇摯的目光凝視神父。
「那是布德木匠的兒子,他父母有的是錢,讓他胡鬧。然而,假如他願意,他會學得很快,因為他聰明。有時,為了開阮笑,我管他叫李布德(像我們去馬羅姆時走的那條山路),我甚至叫他我的李布德(在法文中,「我的」發音和「山」相同,因此是雙關語)。有一天,我把我發明的那個姓說給主教聽,他都笑了……他讚許地笑了……波法利先生身體好嗎?」
「沒有火有什麼關係?」
「他馬上就要來了。」他回答。
由於重複的鐘聲,那少婦的思想在步入迷途了,迷失在少年時代和住校時代陳舊的回憶中。她想起了大蠟燭臺,比m•hetubook•com•com祭壇上插滿了花的瓶子和有小柱子的神位還高。她真願和昔日一樣,置身於一長條白面紗之間。修女們跪在祈禱凳上,她們僵硬的帽子在白色面紗上形成許多黑點。星期天望彌撒的時候,偶一舉首,她就看見聖母柔和的面孔,在氤氳昇起的、微藍的香煙之間。於是,她感動了,覺得自己軟綿綿的,而且完全被遺棄,像一片鳥羽在暴風雨中迴旋。不自覺地,她走向了教堂,只要虔誠能使她的靈魂皈依宗教,只要生活能在其中完全消失,她準備接受任何信仰。
「當然!比方說,城裡的工人。」
「那是真話,」沙勒回答說,「但是我尤其想到疾病,比方說,傷寒呀,外省去的學生就愛生那種病。」
然後,他一步就跳進了教堂。
可是他覺得雷翁很奇怪。他常常攤開雙手,往椅背上一靠,含含糊糊地抱怨生活。
「還是我!」雷翁說。
穿布鞋的孩子們在那兒跑,那就像是為他們設的地板。你能聽見他們的喧嘩和鐘聲交雜。一根長繩索從掛鐘的地方自高處垂下來,垂向地面。鐘聲隨著繩子的搖擺漸漸轉弱。一些燕子正在飛過,一面輕輕地叫,用翅翼劃破天空,然後快速地回到簷瓦底下的黃巢裡。教堂的末端,點著一盞燈,也就是說一個懸著的玻璃杯裡的一根燈芯。從遠處看,那燈光像在油裡顫動的一個白點。一道長長的日光穿過教堂中部,使得兩側和角落顯得更加陰暗。
「但是,有些女人有麵包而沒有……」艾瑪說那些話的時候扯曲著嘴唇。
他快速地,仔細地向四周瞧了一眼:牆、書架、壁爐,好像要鑽進一切。
「好啦,雷翁,上車吧!」公證人說。
「別人也可憐。」她回答。
「你是基督徒嗎?」
「他們什麼也不尊敬。」
「妳不是要問我什麼嗎?究竟要問什麼?我不知道。」
「是那個人,因為受了洗……受了洗……受了洗……」
「沒有什麼大事,只是我太太今天下午有點激動,你知道,女人會因任何事情而煩心,尤其是我的太太。我們反感就是我們的錯,因為她們的神經組織原來就比我們的更脆弱。」
有一天傍晚,窗子是開著的。她坐在窗口,正在看教堂管理員雷斯迪布多瓦修剪黃楊木。猝然她聽見了晚禱的鐘聲。
他在藥房裡呆了很久。雖然他並不曾顯得焦急,歐梅先生還是努力使他放心,要他振作起來。於是他們談到種種威脅兒童的危險,以及傭人的粗心。歐梅太太也知道傭人的粗心和迷糊,因為從前有個女廚師把一小盆炭火打翻在她的肚子上,她胸口上至今還有疤痕。因此,父母親總是要多多提防。儘量不要磨刀,地板也不打蠟,窗戶裝上鐵柵,壁爐也裝上結實的爐門。歐梅家的孩子們雖然自由,但是每走一步,後面總是有人跟著。一點點傷風,父親就要他們吃藥丸。直到四歲多,他們都戴著厚厚的頭罩,毫不通融。其實,那是歐梅太太的意思。她丈夫心裡很難過,唯恐智慧器官因壓力而產生不良的後果,他甚至說:
她裝做沒有聽見。他又說下去:
然後,他在椅子上轉動著身子說:
「你等著瞧!你等著瞧,李布德!」忽然,那位神父用生氣的聲音教訓一個孩子,「看我不給你一個耳光,搗蛋鬼!」
「就照英國規矩吧!」她說,伸出手,一面勉強自己笑。
稅務員說:「那是因為你缺少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