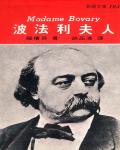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二部
10
當歐梅跑出櫃臺去把沙發椅放在原來的地方時,畢內問他要半兩糖酸。
「糖酸?」藥劑師輕蔑地說,「我不知道糖酸是什麼,你也許是要蓚酸吧?是不是?」畢內解釋說他要一種腐蝕劑,親自配成銅水用來擦去獵具的鐵鏽。艾瑪心顫了。藥劑師笑起來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後悔曾經依順他,相反地也不知道她是否希望不更強烈地愛他。她因感到自己脆弱而覺得羞辱,那羞辱變成僧恨,可是感官的逸樂又沖淡那份僧恨。那並不是愛,那像是一種永恆的誘惑。他只是在征服她,她幾乎害怕起來。
何多夫曾經久久地想看手槍那回事。假如那句話是認真的,那就非常可笑,他想,因為他自己沒有理由恨那好心的沙勒,因為他不是善妒的人——在這方面,艾瑪也曾向他大發其盟誓,他也覺得不甚得體。
那稅務員試著用那句話掩飾他剛才的驚恐,因為知府下過命令禁止打鴨子,除非是在船上。畢內雖然尊重法律,但是發現自己犯了法。因此他隨時隨地都以為聽見地保來了。但是那種不安卻掃他的興,他一個人躲在桶裡為自己的快樂和慧黠喝采。
可是她那麼美麗!他曾佔有過許多女人,其中沒有一個像她那麼爽直。這種樂而不淫的愛對他來說是新奇的,那新奇把他從苟合的習慣中拔|出|來,既滿足他的驕傲也滿足他的感官。他的中產階級的良知使他輕視艾瑪的瘋狂,卻又覺得那瘋狂很可愛,因為對象是他自己。確定被愛以後,他就不在乎了,他的態度也不知不覺地改變了。
我希望你們收到信的時候身體健康,也希望這隻火雞和其他的一般好,因為我覺得牠更肥,也更大,假如我敢這樣說的話。下一次,為了換換口味,我將送你們一隻公雞,除非你們寧願要火雞。要把籃子和兩隻舊的一起還給我。我碰到一件倒楣的事。一夜刮大風的時候,車棚頂被風吹到樹林裡去了。收成也不好。總之,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來看你們。現在離開家真不容易,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我可憐的艾瑪。
雨夜的時候,他們就躲在車棚和馬廄間的診斷室中。她點起一枝廚房裡用的蠟燭,是她把那枝蠟燭藏在書後面的。何多夫呆在那兒,就像在自和圖書己家裡一樣。書架、書桌,總之整個房間都使他覺得好玩,他不自禁地取笑沙勒,令艾瑪很窘。她希望看見他嚴肅,甚至有時更戲劇化,比方說那次當她以為聽見園徑上有走近他們的腳步聲的時候。
艾瑪沒有回答。他又說:
就是在那個時候,艾瑪追悔了!
「請給我半兩硝鏹水。」
何多夫總是扔一把沙子在百葉窗上作為信號。她驚跳起來,但是有時必須等些時候,因為沙勒有在爐火旁邊談話的怪習慣,而且沒完沒了。她十分焦急。假如她的眼睛能做得到的話,它們會叫何多夫從窗口跳進來。終於,她開始晚妝;然後拿起一本書靜靜地讀,像是對唸書很有興趣。但是在床上的沙勒叫她:
「可是有些人並不在乎。」
「妳的小女兒好嗎?」歐梅太太突然問艾瑪。
再見,我親愛的孩子們。我吻妳,我的女兒,也吻你,我的女婿,也吻小外孫女,吻她的雙頰。
「雨斯丹,」藥劑師叫,「給我們拿硫酸來。」
有幾分鐘的功夫,她把那張粗紙拿在手裡。錯字一個連著一個,艾瑪在字裡行間追尋著溫情,那溫怕像是把半個身子藏在荊棘籬笆裡的母雞。墨水是用爐火烘乾的,因為有點灰從信紙上滑落到她的衣裙上,她幾乎以為看見父親彎著身子向爐心拿火箝。她有多麼久不再這樣了:在他身邊,坐在矮凳上,在壁爐邊,拿一根柴就著水草的熊熊火焰燃燒,而水草卻發出爆裂聲。她回憶夕陽滿天的黃昏。有人走過的時候,小馬就叫、就跑……窗外有一個蜜蜂窩,有時蜜蜂在日光下旋轉,像跳躍的金球一樣敲著玻璃窗。那時她多麼幸福!多麼自由!有多麼多的幻想!現在一點也沒有了。在每次的心靈歷險中,她都花費了一點幸福,一點自由,在前前後後的情況中:在少女時期,在婚姻中,在愛情當中——她不斷地在生之旅程中失落幸福和自由,像一個旅人在路上的每個客棧裡留下一點什麼東西。
他一連失了三次約。常他再來的時候,她表現得很冷漠,幾乎是輕視。
此外,她變得很多情了。從前是要交換小照,交換剪下的髮絲,如今她要一枚戒指,一枚真正的結婚戒指,以示永恆的結合hetubook•com•com。她常常和他談到晚鐘,或徒大自然之聲;然後和他談她的母親以及他的母親。何多夫的母親已經死了二十年了。而艾瑪依然用甜言蜜語安慰他,像安慰一個失去了母親的嬰兒,有時甚至一面望著月亮一面說:
「好,我就來。」她回答。
「啊,那是因為天氣太熱。」她回答。
他假裝沒有注意到她憂傷的嘆息和她正在抽出來的手帕。
「再給我一點……」
她因他的勇敢而驚恐,雖然她在其中感受到一種令她起惡感的粗俗和失態。
「是啊!」她結結巴巴地說,「我是從孩子的奶媽家回來的。」
「天氣不太暖和,風好刺骨喔!」
晚上,何多夫發現她比往常更嚴肅。
「有人來了。」她說。
「隨時為妳服務,夫人。」他用冷冷的語氣說。
至於我,身體還好,只是去伊伏多趕市集的那天感冒了。我是去那兒找一個牧羊人,我把原先那個辭掉了,因為他很講究吃。真難對付這些強盜。他也不誠實。
她甚至想知道自己為什麼討厭沙勒,也想知道是否最好能愛他。但是他對她情感的轉變沒有什麼反應。當她正為自己犧牲的意願感到尷尬的時候,藥劑師恰巧提供她一個機會。
(這裡空了一行,就像那好心人放下了筆,想一想。)
整難個冬天,何多夫在夜間便到花園裡來,每周兩、三次。艾瑪故意把柵欄門的鑰匙拿掉了,沙勒以為鑰匙丟了。
她呼吸困難了。
那稅務員帶著一種狡黠的樣子說:
「妳在浪費時間,我的美人……」
那小女孩正在草地上打滾。有人在翻弄新刈的草,她就在草堆裡,臥在一堆草上。女傭人拉著她的裙子。雷斯迪布多瓦在旁邊割草,每當他走近,她就用兩隻手在空中揮舞。
某一天早晨,當她那樣走回家的時候,她突然覺得看見一枝短槍的長管瞄準了她的臉。還有一隻小木桶一半埋在溝邊的草地裡,槍管就斜斜地從木桶裡伸出來。嚇得快要昏倒的艾瑪還是向前走,一個男人從桶裡出來了,就像從盒子裡跳出來的彈簧一樣人。他的綁腿一直扣到膝蓋上,便帽簷蓋著眼睛,嘴唇在發抖,鼻子是紅的。那是在窺伺野鴨子的畢內隊長。
然後,因為看www.hetubook.com.com見她的耳梢有點髒,她立刻按鈴要熱水,替她洗,為她換衣服、換襪子、換鞋,問一千次她的身體好不好,好像她剛旅行回來,最後,一面哭,一面再吻孩子。她終於把孩子交給女傭人,後者因那過份的母愛而感到驚訝。
「啊,好極了,好極了。至於我,像妳所看見的,我天一亮就在這兒。但是天氣壞透了,除非鳥正對著槍口。」
「帶她到我這兒來!」她的母親說,一面跑過去吻她。「我多麼愛妳,我可憐的孩子,我多麼愛妳!」
去年冬天有一個販子路過你們那地區,他拔去了一個牙,他告訴我說波法利工作勤奮。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我看見了他的牙,我們在一起喝了一杯咖啡。我問他有沒有看見妳,他說沒有,但是看見馬棚裡有兩匹馬,我的結論是事業蒸蒸日上。那就好了,親愛的孩子們,願上帝帶給你們所有的幸福!
「難道他永遠不走了?」她想。
「妳呼吸的聲音好像很急促啊!」歐梅太太說。
他又鑽到桶裡去了。
「我能肯定我們各自的母親在天之靈也贊同我們的愛情。」
然而,因為蠟燭耀眼,他轉向牆,入睡了。於是,她屏住氣溜出去,帶著微笑,帶著心跳,衣冠不整。
向你們問好
「半兩松香和樹膠,四兩黃蠟,一兩半骨灰,用來擦亮我軍裝的漆皮。」
茉莉的葉子落了,星星在光禿的枝椏間照耀。他們聽見河水在他們背後流著,也不時聽見河岸上的枯蘆葦的簌簌聲。四周一團團的陰影在黑暗中鼓起來,有時,那些陰影一起顫動,豎立起來,又彎下去,像迎面而來淹沒他們的黑色巨浪。夜間的寒冷使他們擁抱得更緊。他們覺得他們的嘆息也更高聲,他們只能隱約地看見的對方的眼睛也顯得更大。在沉寂中,他們低聲耳語著,像水晶一般鏗鏘的落在彼此的心靈上,而且迴盪不息。
看見是艾瑪的時候他才放了心,立刻搭起訕來:
晚飯後,沙勒看見她愁眉不展,帶她去藥劑師家散散心。她在藥店裡看見的第一個人又是他,那稅務員。他站在櫃臺面前,紅瓶子的亮光照著他。他說:
「妳這麼早就出來了?」
然而www.hetubook•com.com,外表卻是空前未有的平靜,因為何多夫能順利地按照自己的意欲完成那通姦行為。六個月以後,當春天來到時,他倆面對面,就像一對夫婦維持著「家」的火焰。
「是不是用來對抗妳的丈夫?可憐的孩子!」
那是老胡歐特因紀念治癒腿傷而派人送火雞來的時候。送禮物來的日子總附上一封信。艾瑪割斷了把信掛在籃子上的繩子,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親愛的孩子們:
然後,他向想上樓去看歐梅太太的艾瑪說:「不必了,她就下來。妳烤著火等她吧……對不起,你好,醫師(藥劑師非常歡喜說醫生那兩個字,好像那樣稱呼對方他就與有榮焉)……當心,別弄翻了乳缽!還是去拿小客廳裡的椅子吧!你明明知道不應該搬動客廳裡的沙發。」
但是,一心在唸發票的畢內可能什麼也沒有聽見。他終於走了。擺脫了他以後,艾瑪嘆了一口氣舒陽一下。
「你帶了手槍沒有?」她問。
然後,何多夫用一個手勢結束了他的下文:「我一彈指就會把他碾碎。」
「再見,畢內先生。」她打斷了他的話題,一面轉身。
「別說話!」她的丈夫大聲說,他正在帳簿上寫數字。
「妳原該在遠處說話的!」他大聲說,「看見槍的時候,總該警告一聲。」
「為什麼?」
「來嘛!艾瑪,」他說,「該睡了。」
第二天,艾瑪和情人又計劃他們的幽會。她想用禮物賂賄她的女傭人。但是最好能在雍維勒找到一棟秘密的屋子。何多夫答應去找。
你們的慈父德歐多.胡歐特
一縷四月的陽光照著架子上的瓷器;火在燃燒;她感覺到便鞋下面地毯的溫軟。陽光很清亮,大氣也很溫煦,她聽見女兒爆出的笑聲。
然而究竟是誰使她那麼不快樂?那擾亂她的大災禍又在哪裡?她仰起頭,向四周環顧,像是要尋找那使她痛苦的原因。
那是在涼棚下。從前,在同一條木長凳上,在夏天晚上,雷翁老是憐愛地望著她。現在,她幾乎不再想他了。
他吹滅了蠟燭。
「保護你自己嘛!」艾瑪說。
我很難過,因為還不認識我親愛的小外孫女貝特.波法利。我在花園裡為她種了一株喬麥李樹,在妳的臥室外面,我不許人碰那棵樹,除非是將來做煮李子的時候。我會把煮李子放在櫥櫃裡,留給她,當她來的時候。
https://m•hetubook.com.com艾瑪後悔那麼急急忙忙地離開了那個稅務員,他一定會作一些不利於她的猜測。奶媽是最壞的藉口,因為全雍維勒鎮的人都知道她的小女兒已經回到父母家裡一年了。而且附近沒有人住,那條路只通向雨歇德。那麼,畢內猜到了她是從哪裡來,他不會守口如瓶,他一定會宣揚出去的。她折磨了自己一整天,設法編出一切可以想得出來的謊言,她眼前老是有那個帶著獵袋的渾蛋。
「妳為什麼沒有帶她來?」她又低聲問。
漸漸地,何多夫的顧慮感染了她。當初,愛情曾經令她陶醉。除了愛情以外,她什麼都不想。但是,因為如今他已變成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她害怕失去他,甚至怕他不安。當她從他家回去的時候,她用不安的目光向四周張望,窺伺每個從遠處走過的人影以及村子裡的每個天窗,人們可能從天窗裡看見她。她傾聽腳步聲,呼叫聲和犁頭的聲音。白楊樹的葉子在她頭上搖曳,她停下來的時候比白楊葉子還更蒼白,抖得更厲害。
「會過去的,」他想,「只是一時的任性。」
「說實話,這種天氣不宜於打獵,太潮濕。」
他不再像從前那樣用甜言蜜語使她感動得哭,他的愛撫也不再像從前那樣強烈得使她瘋狂。她一直投入在那偉大的愛情中,生活在那偉大的愛情中,那偉大的愛情好像在減退,就像河水被河床吸乾了,她看見了泥淖。她不願相信那事實,她變得加倍溫柔,而何多夫卻愈來愈不掩飾他的冷漠。
何多夫穿著一件很寬的大衣,用大衣把她整個人包住,用臂膀摟住她的腰,默默地把她拖到花園的末端。
「小聲點!小聲點!」艾瑪說,一面用手指著藥劑師。
藥劑師開始切蠟的時候,歐梅夫人下樓來了,手裡抱著薏爾瑪,拿破崙在她身邊,阿達莉跟在她後面。她在靠窗的那張絲絨長凳上坐下了,男孩坐在小凳上,他姊姊在裝棗子的盒子四周轉來轉去,在她爸爸身邊。後者在裝滿漏斗,塞瓶口,貼標籤,打紙包。他四周的人都不說話,只不時聽見天秤裡的砝碼聲以及藥劑師低聲對學徒的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