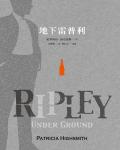三
「哈!哈!」艾德緊張地笑了。
湯姆穿上自己那件在威尼斯買的粉紅色襯衫。然後打電話去曼德維爾飯店,用湯瑪斯.雷普利的名字訂了個房間。他會在晚上八點左右到達,他說。
「你就乖乖坐在這裡,或者站著,看你喜歡哪個。」艾德說,指著那張斜放的辦公桌,後頭有張椅子。
記者們開心地低頭猛記。
「真是了不起!了不起啊!」雷納說,看著湯姆的眼光帶著一種真心的欽佩。「我看過很多照片,你知道!自從我去年那回把兩腳綁在後面模仿羅特列克以來,還沒見過模仿得這麼好的!」雷納瞪著湯姆。「你是誰?」
傑夫和湯姆面面相覷。艾德靠著一牆書沉默站著。湯姆低聲說:「真的,兩位,如果那幅油畫一直就放在衣帽間,你們就不能派個人去偷走或把它給燒了嗎?」
「你確定你畫了《時鐘》嗎?」莫奇森問。
「不用了,謝謝,我很好。」然後莫奇森先生對著湯姆說。「畫中有一個藍黑色的時鐘——你記得嗎?」他微笑,好像自己在問一個很單純的謎語。
「六點了,」傑夫宣布,抬起手腕看錶,袖釦金光閃閃。「我現在應該私下去跟幾個記者說德瓦特來了。這裡是英格蘭,不會有——」
純鈷紫只用來畫陰影,可以說並不是《時鐘》的主要顏色。莫奇森的眼睛很尖。湯姆覺得《紅色椅子》——比較早的德瓦特真跡——也有同樣的純鈷紫,他很好奇上面是否標示了作畫年代?如果他可以說《紅色椅子》是三年前的作品,並設法證明,就可以打發掉莫奇森了。湯姆心想,這個稍後再跟傑夫和艾德確認吧。
傑夫和艾德一樣都專注聽著,趁著這個空檔,傑夫說,「但畢竟這幅畫是跟其他德瓦特的作品一起從墨西哥運來的。他每次都會同時寄兩、三幅畫的。」
湯姆希望莫奇森能接受,但他不是那種人。
傑夫開始默默收拾著書架邊緣和辦公桌上的空杯子。
「德瓦特先生,很意外在這裡見到你。是什麼讓你決定來倫敦的?」
此時湯姆還站著。一股輕微的寒意掠過他身上。湯姆露出微笑。「我從來無法描述我的作品。如果裡頭根本沒有鐘,我也不會驚訝。莫奇森先生,我的作品名稱未必是我取的,你知道嗎?怎麼會有人替那幅畫取名為《週日正午》,我是完全不明白的。」(之前湯姆匆匆瀏覽了一下這次展出的二十八件德瓦特作品清單,可能是傑夫或某個人很考慮周到地打開,放在辦公桌的吸墨紙上。)「是你取的嗎,傑夫?」
「別再問了,拜託。」傑夫在門邊說。
「——不會有蜂擁而上的場面,」傑夫堅定地說。「我會控制好的。」
傑夫帶著雷納回來,那是一個整潔的小個子年輕人,穿著一套愛德華時代流行的長西裝,上頭有很多鈕釦和天鵝絨鑲邊。雷納看到湯姆打扮成德瓦特的模樣,立刻爆笑出來,傑夫噓聲示意他安靜。
「沒有,快告訴我們吧。」傑夫說,已經咧嘴微笑,準備要大笑一場了。
傑夫又靜靜鎖上門。「要不要坐下,莫奇森先生?」
傑夫對畫的事情比較懂。他先開口,有點吃力,「我想,如果他把一個專家扯進來,那就嚴重了。看起來他會這麼做。他有關紫色的說法可能有點道理。有人會覺得是線索,往下有可能挖出更糟糕的。」
莫奇森先生塊頭很大,一張愉快的臉。「你好嗎,德瓦特先生?」他微笑著說。「能在倫敦見到你,真是意想不到的好運啊!」
「啊,可以,」湯姆說。「他們會知道我在哪裡。」
「德瓦特,啊——」
「我沒有——不,我沒法說這次展覽中我有哪件特別偏愛的作品。謝謝你。」德瓦特抽菸嗎?管他去死。湯姆伸手去拿傑夫的「卡拉文A」牌香菸和-圖-書,在兩個記者擁上來要替他點菸前,自己先拿起桌上的打火機點著了。湯姆身子往後稍退了一下,免得鬍子被火燒到。「我最喜歡的作品或許是早期的——《紅色椅子》、《墜落的女人》,或許吧。不過已經賣掉了。」湯姆忽然憑空想到《墜落的女人》這件作品名,的確是有這幅畫。
「引起我興趣的,是這幅畫裡面的紫色。那塊紫。這是純鈷紫——你大概可以看得比我更清楚。」一時之間,莫奇森先生的笑幾乎帶著歉意。「這幅畫是至少三年前畫的,因為我是在三年前買的。但如果我沒搞錯,你五年或六年前就放棄用鈷紫,改用鎘紅混合群青的紫色。詳細日期我沒法確定。」
湯姆舉起一隻手,擺出害羞而禮貌的道別手勢。「謝謝各位。」
「或者衛斯柏禮飯店。」艾德說。
又有三名男子進來,湯姆注意到傑夫逼著其中一個人待在外頭。
「德瓦特,請容我介紹《電訊報》的蓋德納先生,」傑夫說。「還有這位是——」
「應該是有些印刷品提到過吧?」湯姆問。「我在想要重新更正年代——好解決這個紫色的問題。」
展覽室傳來的嘈雜嗡響現在比較小聲了。湯姆看著臉色有點蒼白的艾德。我可以消失,但你們不行。——湯姆心想。他挺起雙肩,手指比出一個V字形。「打起精神吧,班伯瑞。我們會度過這一關的。」
「巴克馬斯特畫廊是德瓦特唯一授權代理的畫商。你那幅畫是直接跟我們買的。」
雙方還沒來得及打招呼,門上就響起了叩門聲。湯姆朝著辦公桌駝背而立,駝得簡直就像害了風溼似的。房裡僅有的一盞燈就放在通往展覽室的那扇門邊,離他至少有十呎,但湯姆注意到柏金斯先生帶著附了閃光燈的照相機。
「這點我知道,」莫奇森說。「我也不是在指控你們,或指控德瓦特先生。我的意思是說,我不認為這件作品是德瓦特的真跡,我沒法告訴你們是怎麼回事。」莫奇森輪流看著他們三個人,有點對自己的一時激動感到難為情,但還是堅信自己講的是對的。「我的推論是,像德瓦特作品中這麼微妙但卻這麼重要的淺紫色,一個畫家一旦改用了別種顏色,就絕對不會回頭去用他以前用過的某種顏色或任何顏色組合。你同意嗎,德瓦特?」
「來廁所弄吧。」艾德打開了洗手台熱水的水龍頭。
「你好嗎?」湯姆說。
「給我看一張某年某個編號畫作的收據嗎?從墨西哥運來的畫作,連作品名稱都沒有?如果德瓦特根本沒給作品取名呢?」
「好,不過我想跟雷納說一聲。」傑夫咧嘴笑了。「我帶他來見你。」他走出去了。
「沒錯。《時鐘》背後有作畫年代。是三年前,就像德瓦特的簽名一樣,用黑色的顏料寫的。」莫奇森說,把他那幅畫翻面,讓大家看那個簽名。「我在美國找人分析過這個簽名和年代,我對這件事就是仔細到這個地步。」莫奇森微笑著說。
「可是我——」
湯姆又笑了一下。「我想他們對《泰晤士報》或《藝術評論》之類的興趣不大。」
「墨西哥帶給你靈感嗎?我注意到這回展覽中沒有任何一幅畫是墨西哥背景的。」
艾德帶他來到一個小浴室,門口原先被一個可以拉開的書架擋住了。湯姆匆匆喝了口水,走出浴室時,兩名男記者跟著傑夫進來,他們一臉的驚訝和好奇。一個五十來歲,另一個二十來歲,不過兩人的表情很像。
艾德和莫奇森也彼此問候了一下。
「德瓦特。你的作品這麼多,我想你可能忘了一幅畫——應該說不記得。沒錯,《時鐘》是你的風格,主題也是你很典型的——」
「那兩幅沒有這種技法。裡頭有紫色,但都是兩種和_圖_書顏料混合而成的。你們談的那兩幅是真跡——無論如何,都是比較後來的真跡。」
湯姆就沒那麼高興了。他很想趕緊擺脫這一身偽裝。這個狀況是個麻煩,而且他還沒解決掉。
「我沒有什麼時期,」湯姆說,「畢卡索有不同的時期。這就是為什麼你永遠說不準畢卡索——就算你想也不可能。你不可能說『我喜歡畢卡索』,因為你不會想到任何一個時期。畢卡索很愛玩。這也沒關係。但他這麼玩,就毀掉了一個原先可能是真誠而完整的人格。畢卡索的人格是什麼?」
「我有一幅您的畫作——《時鐘》。事實上,我這回還帶來了。」此時莫奇森滿面笑容,著迷而尊敬地凝視著湯姆,湯姆希望他因為親眼見到他而驚喜得眼花了。
「老天,為什麼不是?」湯姆的友善程度也不輸莫奇森。
這個問題是隨口不經心問起,還是特別有針對性?湯姆納悶著。「當然了。」湯姆說。
「還記得自己畫過嗎?」
「他們不曉得你是德瓦特?」
莫奇森望著傑夫。「康斯坦先生,你說你收到《時鐘》時,同時運到的或許還有兩幅畫?」
湯姆脫掉身上那件破舊的外套。「《紅色椅子》有創作年代嗎?」
「是的。只是一時興起。」湯姆露出那種疲倦而帶有哲思的笑容,那是一個多年來獨自凝視著墨西哥群山的人會有的笑。
「我想有個小女孩——背對著觀者,可以這麼說吧?」
湯姆嘆了口氣,食指摸著自己的小鬍子。「我說不上來。看起來我不像你這麼擅長理論。」
「這幅《時鐘》,你是幾年前畫的?」莫奇森問。
「當初可不是當成舊作賣給我的。還有《浴缸》,標示的年代是去年,上頭用的也是純鈷紫。」
「你這次回來是一時興起嗎?」年輕的柏金斯問道。
莫奇森慢條斯理地把雙手插|進長褲口袋,望著傑夫。「謝謝,但我更有興趣的是我的理論——我的意見,而不是錢。既然我都來了倫敦,這裡的油畫鑑定水準和全世界任何地方一樣好,說不定還是最好的,我打算把《時鐘》拿給一位專家看,而且拿來跟幾件沒有爭議的德瓦特真跡比較。」
湯姆扮出德瓦特那種駝背的姿勢。「那種氣氛,真是——太壓抑了。當時在西班牙。我們訂了一個套房,你知道,我和赫綠思住在裡面,樓下陽台有隻鸚鵡唱著歌劇《卡門》——唱得爛死了。每一次我們一那個,唔,那隻鸚鵡就唱起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家都探出窗子吼著西班牙語,『閉上你的髒嘴!誰教那隻臭鳥唱《卡門》的?宰了牠!拿去煮湯!』笑成那樣真的沒辦法做|愛。你們試過嗎?唔,據說笑是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唯一差別。而做|愛當然沒有這種區別性。艾德,能不能幫我把這些鬍子給弄掉?」
「這個,」傑夫說,「你不必知道。我們只要說——」
中間有一段暫時的沉默。
湯姆並不憂慮。他應該要表現得憂慮些嗎?他只是輕輕聳聳肩。
「你打算做什麼?」艾德問。
「啊,那當然。」艾德說,他在廚房裡泡茶。「貝納德老是待在家裡。他那邊有電話。」
「我知道那是我的畫,」湯姆說。「畫的時候我可能在希臘,甚至是愛爾蘭,因為我不記得日期了,而畫廊標示的年代可能不見得是我畫的時間。」
「還有外頭那幅叫《浴缸》的畫也是用了純鈷紫,」莫奇森說,對著展覽室點了個頭。「但是其他都沒有用。我覺得很好奇。通常一個畫家放棄了一種顏料之後,就不會回頭去用了。以我的意見,用鎘紅和群青混合出來的紫色要有趣得多。那是你新選擇的紫色。」
傑夫臉上僵著的笑容更大了,不過有點心神不寧。「啊,沒錯。你應該會見到他,當然了。不過要先見過記者才行。」傑夫很緊張不安,急著要離開,他臉上的表情好像要再說些什麼,不過還是沒說就出去了。https://www.hetubook.com.com鑰匙在鎖裡轉動。
湯姆低聲笑起來。很放心自己猜對了。「我想我是比較喜歡小女孩吧。」
「能不能告訴我們你所居住那個村子的村名?」
回到傑夫的工作室,他們發現貝納德.塔夫茲已經離開了。艾德和傑夫似乎很驚訝。湯姆有點不安,因為貝納德應該要知道事情的進展才對。
兩個人握了手。
「嗯,沒錯,」莫奇森說。「不過你不畫小男孩的,不是嗎?」
「墨西哥個頭啦,」艾德說,端著他那杯茶走進來。「德瓦特會到英格蘭各地拜訪朋友,連我們都不知道他在哪兒。先等個幾天。然後他才會回墨西哥。搭什麼交通工具?誰曉得。」
現在那扇門發出推開的聲音,傑夫一邊肩膀頂著。門沒打開,湯姆看到了,然後冷靜的雙眼回到向他發問的那個人。
「這是我的畫。」湯姆說。
「很抱歉,我還沒決定要住在哪裡。」湯姆說。
「我不太明白問題出在哪裡,」湯姆說。「如果我自己在這幅畫上寫了三年前的時間,那麼就是我在墨西哥畫的。」
「這次展覽中,你最喜歡的作品是哪一幅?你覺得你最偏愛的是哪件?」
「柏金斯,」那名比較年輕的男子說。「《週日報》……」
傑夫開了門讓他出去,然後又鎖上。
「這件作品在哪裡?我沒見過這幅作品,不過我聽過名稱。」
「還有個辦法,讓貝納德再畫幾幅——至少兩幅——用上純鈷紫的顏料。這樣就算是證明他兩種紫色都在用。」不過湯姆說的時候,自己都覺得很沒勁,而且他明白原因何在。湯姆覺得,他們可能無法再繼續指望貝納德了。湯姆的目光從傑夫和艾德身上轉開。他們一副不太相信的樣子。他試著站起來,挺直身子,感覺到德瓦特的偽裝外表給了他信心。「我跟你們提過我的蜜月嗎?」湯姆用德瓦特那種沒有抑揚頓挫的聲音問。
「好吧,咱們聽聽看他的說法吧。」湯姆以德瓦特緩慢而自信的語調說。他想炫耀自己應對得遊刃有餘,但是沒成功。
「我不認為《時鐘》是你的作品。」莫奇森說,帶著美國人那種友善卻堅定的態度。
「哈!哈!不會有什麼?」艾德插嘴道。
傑夫進了那間小浴室,在裡頭忙著整理玻璃杯和菸灰缸。
艾德幫著莫奇森把他的畫包好,還提供了繩子,因為莫奇森原來捆畫的繩子已經割斷了。
「我真沒法告訴你,你看起來有多麼像——德瓦特!」傑夫一拍湯姆的肩膀。「希望這一拍不會害你的鬍子掉下來。」
他們小心翼翼用了好多水,才把絡腮鬍拆下來。然後把暫時性的染髮劑沖掉。最後湯姆聽到傑夫開心地說,「不,謝了,我稍後再打來。」
傑夫笑了。「不,我想是艾德取的。莫奇森先生,要不要喝杯酒?我去吧檯幫你拿一杯。」
然後問題開始滿天飛,儘管傑夫建議每個記者輪流發問。但是沒用,每個記者都想搶先問自己的問題。
莫奇森的目光從傑夫回到湯姆身上。「你可能覺得我很自以為是,但如果能容我多說兩句,德瓦特,我想有人偽造你的畫。我願意冒更大的險,以我的性命打賭,《時鐘》不是你的作品。」
「啊,莫奇森先生。請進,請進。」傑夫說。他轉向湯姆。「德瓦特,這位是莫奇森先生。從美國來的。」
莫奇森點了一根切斯菲德牌香菸。他的眼珠是褐色的,一頭淺褐色的鬈髮,強壯的下巴稍嫌多肉,就像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樣。「我希望你看看我那幅畫。我有理由的。請等我一分鐘,我寄放在衣帽間了。」
湯姆像個隱士般,害羞的雙眼看著傑夫辦公桌上那塊皮革鑲邊的吸墨墊。「我忘了。《墜落的女人》,我想是賣給一個美國人了吧。」
湯姆對著那幅畫微笑。「當然認得。」
「你能不能至少描述一下你在墨西哥住的房子,德瓦特?」愛麗諾問。
莫奇森其實沒完全說對,那兩幅也是假的。湯姆搔著自己的絡腮鬍,不過下手很輕。他保持一種沉默、有點頑
https://www.hetubook.com.com皮的神態。
「很謝謝你跟我見面,德瓦特。幸會了。」莫奇森伸出一手。
「那個叫莫奇森的傢伙也來了嗎?」湯姆用德瓦特的口吻問道。
「只要說,」艾德說,「德瓦特剛剛接受了一場精彩的記者採訪,這樣就夠了。」
(這有點棘手,但湯姆解決掉了。他的畫作向來是源自想像。)
「我可以透過畫廊跟你聯繫嗎?」莫奇森對湯姆說。「比方明天?」
「但是莫奇森先生,」傑夫說,「我們只需要——」
「你打算要無限期住在墨西哥嗎,德瓦特先生?」
莫奇森回到房內,手臂底下夾著一幅用褐色紙包起來的畫。那是一幅中等尺寸的德瓦特,或許兩呎乘三呎。「這幅畫我花了一萬元買的,」他說,露出微笑。「你或許會以為,我留在衣帽間真是太大意了,不過我是傾向於相信別人的。」他在一把小刀的輔助下拆開包裝紙。「你認得這幅畫嗎?」他問湯姆。
傑夫溫和催著記者們該離開了,相機開始打起閃光燈。湯姆低頭看著,然後應記者要求抬頭讓他們拍了一、兩張。傑夫迎進來一名穿著白色外套、端著飲料托盤的侍者。托盤一下就空了。
傑夫也捶回去,喊道,「暫時不准再進來了,拜託!」
「我想大概是《鳥之幽靈》。不是嗎?」
又有四男一女進來。在眼前的情況下,湯姆最害怕的莫過於女人的眼睛了。傑夫介紹說她是愛麗諾什麼的,曼徹斯特什麼報的記者。
「而且明天德瓦特就不在了。他會回到墨西哥,」傑夫壓低聲音說。「現在回去忙你的吧,雷納。」
「德瓦特——你在墨西哥是一個人住嗎?」愛麗諾問。
等到莫奇森離開辦公室,傑夫和艾德嘆了口大氣。
「莫奇森先生大概會想再跟你見面,」傑夫說。「還會帶著那個專家。所以你得消失。你明天就會離開,回墨西哥——對外的正式說法是這樣。或許甚至今晚就走。」傑夫喝了口保樂茴香酒。他看起來比較有信心了,或許是因為剛剛的記者採訪,甚至加上莫奇森的會面都進行得相當順利,湯姆心想。
湯姆微笑,「我還不知道。」他說,這是實話。
傑夫.康斯坦胖了些,滿面紅光——也可能是他用日照燈晒出來的。他的襯衫袖口裝飾著方形的金袖釦,藍黑條紋的西裝看起來是全新的。湯姆注意到有一塊遮禿髮片蓋住了傑夫頭頂的禿頭處,湯姆知道那裡現在頭髮一定很少了。通往畫廊展場的門關著,門後傳來一陣喧譁,很大一部分是出自一個女人,她大笑的聲音彷彿一隻鼠海豚飛過洶湧的海面,湯姆心想,不過他現在沒有寫詩的心情。
湯姆說,「傑夫,我們先回你的工作室吧?你能不能再把我從後門變走——就像灰姑娘?」
艾德正在大笑,傑夫則拋開壓力,放鬆地倒在沙發上——湯姆知道這只是暫時的。
「我敢惹這種麻煩,真是膽子太大了,我知道。不過我在費城的一個美術館看過幾件你的早期作品。如果容我這麼說,德瓦特先生,你——」
艾德和傑夫面面相覷,然後艾德趕緊說,「不行,有太多圖錄刊登過了。」
「別喊我德瓦特先生,」湯姆暴躁地說。「叫德瓦特就好了。」
「或者他們會識破我們。」艾德回答,比出一個比較粗魯的手勢。
「當然,你們可以連絡到貝納德吧。」湯姆說。
「恐怕我沒法告訴你,」湯姆坦白地說。他明白莫奇森的意思了,至少時間這方面他明白,然後他補充,「有可能是四、五年前。這是一幅舊作了。」
「能不能打電話去幾家飯店查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他?」
「你喜歡最近完成的這批畫作嗎?你認為這是你最好的作品嗎?」
「好吧,莫奇森先生,你希望我們怎麼處理《時鐘》?把錢給你?」傑夫問。「我們很樂於退款,因為——剛剛德瓦特才證實這幅作品是真跡,而且坦白說,現在這幅畫的價錢已經不止一萬元了。」
(這個湯姆辦得到。一棟平房,有四個房間。前面有一棵芭蕉樹。每天早晨hetubook.com.com十點有個女孩來幫他打掃,中午出門幫他採買一些東西,帶回來剛出爐的薄玉米捲餅,他配著紅色的菜豆當午餐。沒錯,肉比較少,但是有一些山羊。那個女孩的名字?璜娜。)
「沒錯。現在我想起來了——我想另外兩幅被倫敦的收藏家買走了,現在借展給我們——《橙色穀倉》和——你記得另外一幅嗎,艾德?」
然後傑夫說,「他住在曼德維爾飯店,就在威格摩街旁邊。」
「這裡有水嗎?」湯姆問。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這幅作品?」
「某些評論家說——」
「向您致敬,」雷納鞠躬說。他退向門,然後補充道,「外頭人幾乎走光了,酒也差不多喝光了。」然後迅速走出去。
「飯店,」傑夫說。「他沒說是哪家。」
「有,」傑夫說。「是六年前的作品。」
從傑夫點頭的表情,湯姆看得出那是實話,不然就是傑夫的演技太厲害了。
「你想念倫敦嗎?你覺得倫敦看起來怎麼樣?」
那個記者又追問:「你對你的銷售成績滿意嗎,德瓦特?」
「就是那幅沒錯。」傑夫說。
「德瓦特,某些評論家說——」
湯姆心想,即使電話也不方便講太久,會不安全。
「我不會告訴你們我住的村名。」湯姆緩緩說。「這樣對那邊的居民不公平。」
「好吧——這事情有多嚴重?」湯姆問。
「是的。」
傑夫扯著嘴角勉強笑了,不過他保持沉著,彷彿莫奇森還在房裡。
有個人用拳頭捶著門。
湯姆沒作聲。莫奇森擁有的這幅畫中,那個鐘用了黑色和紫色。筆觸和顏色都類似湯姆家裡的那幅《椅中男子》(貝納德畫的)。湯姆不太明白莫奇森攻擊的是什麼樣的紫色。畫中一名穿著粉紅和蘋果綠洋裝的小女孩拿著那個鐘,或者比較像是她一手放在鐘上頭,因為那個大鐘是擺在一張桌子上。「老實告訴你,我忘了,」湯姆說。「也許我那兒的確是用了純鈷紫。」
湯姆換回他自己的長褲和襯衫。趁莫奇森還沒跟他那位專家談之前,如果能設法引誘莫奇森到他家,或許可以做點事情解決這個狀況——至於做什麼事,湯姆還不曉得。「莫奇森在倫敦住哪裡?」
「唔,我就直截了當說了吧,德瓦特先生,我——我對你在《時鐘》這件作品中的某種技巧改變很有興趣。當然了,你知道我講的是哪件作品吧?」莫奇森問。
「非常好。」湯姆和氣地說。
「這位是艾德.班伯瑞,」傑夫說。「這位是莫奇森先生。」
艾德.班伯瑞帶著他來到一棟建築背面的一扇暗紅色門前,按了電鈴。湯姆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然後門打開了,傑夫站在那兒,對著他們滿臉笑容。
他們經過一條短短的甬道,然後進入一個舒適的辦公室,裡面有一張辦公桌和一架打字機,一些書,從地板到天花板的乳白色掛毯。靠牆放著一些油畫和素描集錦。
湯姆緊緊握住。「幸會,莫奇森先生。」
「風再大都不會掉的。」艾德插嘴。
「你匿名去過歐洲嗎?我們知道你喜歡隱姓埋名——」
「啊,是的。」湯姆說。
(誰不會滿意?)
「村裡的人也喊你德瓦特嗎?」
「以前是,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發音很不一樣。現在他們喊我菲力頗。除了菲力頗先生,我不需要另一個名字了。」
「再會。」湯姆舉起一隻手。
「——說你的作品很像畢卡索立體派時期,當時他作品中開始出現分裂的臉和形體。」
「德瓦特,如果你明天能撥出十分鐘,那就感激不盡了。能不能請教你住在——」
「好,謝謝。」莫奇森在一張直背椅上坐下。
傑夫還沒拿起聽筒,電話就響了。湯姆聽到傑夫跟對方說德瓦特已經搭了北上的火車,傑夫不知道他要去哪裡。「他很孤僻,」傑夫說。「另一個記者,想做個專訪。」掛掉電話後,傑夫這麼說。他打開一本電話簿。「我先試多徹斯特飯店,他看起來就像是住那種豪華飯店的人。」
「喊我德瓦特就行了,我比較喜歡這樣。」
「湯姆!太好了!」傑夫低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