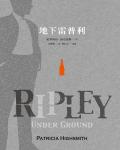四
的確是很好笑,湯姆心想,但還不到爆笑的程度。他想跟莫奇森說,實情才更好笑呢。湯姆露出微笑。「所以你明天要把你的畫帶去給那個專家看了?」
「有趣,真有趣。因為我想我那幅《椅中男子》就有點符合你的說法。《椅中男子》大概是四年前的作品了。我很希望讓你看看。唔,那你打算怎麼處理你的《時鐘》?」
「你有貝納德的消息嗎?」湯姆問。
湯姆禮貌地表示遺憾,然後掛了電話。
「是的,他留話說星期三。伯爵明天會到達米蘭。你明天可以到米蘭嗎?」
「是嗎?畫名叫什麼?」
「麻煩你告訴瑞夫斯,我會再跟他連絡,大概明天吧。他會在哪兒?」
他很希望今晚能見到莫奇森。莫奇森跟貝納德會一起吃晚餐嗎?他真不想等到他們結束。湯姆把西裝掛起來,然後把兩件襯衫放進抽屜裡。他到浴室裡,在臉上又拍了點水,然後看看鏡子,好確定臉上的膠水都洗掉了。
「我打算明天下午離開。」
「真的?」莫奇森的雙眼開始矇矓了起來。「你家離巴黎有多遠?」
然後湯姆走向他。「打擾一下。我想我今天在德瓦特的畫展上見過你。」湯姆講話帶著美國中西部的口音,r音發得特別重。
他喝著淡啤酒,閱讀一份《標準晚報》,等了十分鐘,沒等到莫奇森先生。這附近餐廳很多,湯姆知道,但他實在很難跑到莫奇森的桌邊,自稱白天在德瓦特的展覽見過他,就因此跟他交上朋友。或者他可以說,他還看到莫奇森進了後頭的房間去見德瓦特?沒錯。湯姆正打算要冒險出去探索當地的餐廳,剛好看見莫奇森走進酒吧,對著跟在後面的人打手勢。
「會的,大概——啊,總之十二點以前會到家。」
「是啊。」
「我感覺他知道的事情沒全說出來。我不太相信他也涉入。他不像那種會騙人的類型,看起來也不像有錢人。不過他似乎了解倫敦的藝術圈。他只是警告我,『別再買德瓦特的作品了,莫奇森先生。』你想這是什麼意思?」
「是嗎?你的理由是什麼?」湯姆問。
「麻煩給我蘇格蘭威士忌。你呢?」他問湯姆。
「麻煩告訴他——」湯姆思索著該怎麼講比較好。「就說你——不要說我——剛好知道M先生有事,要等幾天才會進行他那幅畫的相關事情。我主要是擔心貝納德會爆發。這方面你會去處理吧?」
「我不曉得那幅。」莫奇森說。
「不了,不過也沒必要。你過來的話,說不定會碰到M先生,那就不好了。」
「我還拿給他看呢!他說那是他的畫,但在我看來,他並不是百分之百確定。他沒說,『老天在上,那是我畫的!』他只是看了兩分鐘說,『當然了,這是我畫的。』或許我太冒和-圖-書昧了,但我跟德瓦特說,我覺得他有可能忘了自己幾年前畫過的一、兩幅作品,沒取名的。」
「你會不會剛好知道貝納德現在人在哪兒?」
他實在坐不住,於是離開房間,大衣搭在手臂上。他打算去散步,或許到蘇荷區,找個地方吃飯。到了樓下大廳,他隔著玻璃門望向飯店的酒吧。
湯姆跟著他走進電梯。莫奇森把他的畫放在衣櫃角落裡,依然是當天下午艾德包起來的樣子。湯姆充滿興趣看著那幅畫。
「喔,」莫奇森的口氣有點失望。「那另一幅呢?」
「《紅色椅子》,」湯姆說,「還有——」
「他正在曼德維爾飯店的酒吧跟莫奇森喝酒。」
「不行,我明天沒辦法去米蘭。很抱歉。」不管這個接電話的男子是誰,湯姆都不想告訴他,說他已經邀了伯爵下次來法國時住他家。瑞夫斯不能指望他隨時就丟下一切——湯姆已經這樣幫過他兩回了——飛到漢堡或羅馬(儘管湯姆很喜歡短程旅行),假裝偶然到這些城市,然後邀請「宿主」(湯姆心目中老是這麼想那些帶著貨物的人)到他維勒佩斯的家裡住。「我想不會太麻煩的,」湯姆說。「你能不能告訴我伯爵在米蘭的地址?」
「好吧,我去。」莫奇森說,他一直沒坐下。
「是——沒錯。」
「你要不要坐下談?」莫奇森站著,但指著他對面的椅子。「要不要喝杯酒?」
「喂,湯姆!我才要跟艾德走下樓梯,就聽到了電話響。怎麼了?」
讓湯姆想不到、甚至驚駭的是,他看到後面那個人是貝納德.塔夫茲。湯姆迅速溜出酒吧另一頭的那扇門,門外就是人行道。貝納德沒看到他,湯姆很確定。他東張西望想找個電話亭,或者找別家飯店可以讓他打電話的,結果沒找到,於是他從大門回到曼德維爾飯店,取了鑰匙回到他的房間,四一一號房。
莫奇森坐下。「我的那幅叫《時鐘》。能碰到同樣擁有德瓦特作品的人,真是太好了——你還擁有兩張!」
「我覺得你看起來像美國人。我也是。你喜歡德瓦特嗎?」湯姆盡可能裝得天真而坦率,但也不要有那種愚蠢相。
「我現在人在飯店房間裡。現在不管你做什麼,傑夫——你在聽嗎?」
「啊,我們今天晚上不吵他了。他心情很煩。」
然後他們互道晚安。
回到房間,湯姆打到傑夫的工作室,響了三聲,四聲,五聲,然後傑夫接了,湯姆鬆了口氣。
想要談愛情……
「我有兩張他的油畫,」湯姆驕傲地說。「今天展出的那些,我可能會買其中一幅——如果還沒賣光的話。我還沒決定。《浴缸》。」
「還有一件事,我不太喜歡巴克馬斯特畫廊的那些人。傑夫https://m•hetubook.com.com.康斯坦。還有那個記者艾德.班伯瑞,他顯然跟康斯坦很熟。他們是德瓦特的老朋友,這點我明白。我在紐約長島的家裡訂了《聆聽者》週刊和《藝術評論》雜誌,另外也訂了《週日泰晤士報》。我常常看到班伯瑞寫的文章。通常都是吹捧德瓦特的宣傳報導,或是有關他的專文評論。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他們只讓媒體的人進去,不過我還是想辦法混進去了。」莫奇森告訴湯姆。「你知道,我這回來倫敦有個相當特殊的理由,今天下午我在畫廊裡,一聽說德瓦特就在裡頭,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什麼?」
「晚上我跟M先生談過了,談得很投機。他明天會跟我去法國。這樣就會耽擱一些事情,你知道。」
他穿上了睡衣褲,然後打電話到傑夫的工作室。
「別跟貝納德說我看到他了。別跟貝納德說我住曼德維爾。而且不要緊張。不曉得,我們就先假設貝納德不會洩漏機密吧。」
「琴酒加通寧水,」湯姆說。他補充道,「我住在曼德維爾飯店,這兩杯酒就記在我帳上吧。」
「這個我們稍後再來爭吧。告訴我你那兩幅是什麼樣的畫。」
手錶上的指針已經接近十二點。湯姆思索著該跟傑夫.康斯坦說些什麼。另外又該怎麼處理貝納德。湯姆想妥了一篇勸人安心的說詞,而且他明天下午離開之前,還有時間去看貝納德,不過湯姆怕如果太努力想勸貝納德,反倒會讓他更沮喪、更消極。如果貝納德已經跟莫奇森說,「別再買任何德瓦特的畫了,」那個意思似乎就是貝納德不會再仿造任何德瓦特作品了,這麼一來,當然對生意將會非常不利。另一個更糟的狀況是,貝納德好像快崩潰了,很可能會跑去找警方或一、兩個買了德瓦特假畫的人坦白。
「不。我住法國。」
「到時候我會再想辦法打給你。不過如果我沒打也別擔心。不要打給我,因為——我房裡可能會有別人。」說到這裡湯姆忽然笑出聲。
「如果你受騙了,那我想我也一樣。」如果說要幫莫奇森出機票錢,對他只會是羞辱,湯姆心想,於是沒提。「我家很大,而且現在家裡除了管家之外,只有我一個人。」
是啊,湯姆心想。的確很令人吃驚。「但你說過,你跟德瓦特談過。談到了你買的這幅畫嗎?」
「是啊,我是美國人。」
曼德維爾飯店相當闊氣,但絕對不像多徹斯特那麼奢華。湯姆在八點十五分抵達,登記入住,寫了他在塞納河畔維勒佩斯的地址。他想過要給個假名和一個英格蘭鄉下的地址,因為他跟莫奇森先生見面可能會惹出不小的麻煩,因而必須趕緊消失;不過相對地,他可能也有機會邀莫奇森到法國,這麼一來,和_圖_書湯姆可能就得用上他的真名。湯姆請一位大廳服務生幫他把行李拿到房間,然後自己走到酒吧看一下,希望莫奇森先生可能會在那兒。莫奇森先生不在裡頭,不過湯姆決定點一杯淡啤酒等等看。
傑夫立刻接了電話。「喂,怎麼了?」
湯姆皺著眉頭,似乎很懷疑,事實也的確如此。湯姆認為,即使畫家沒給作品取名,也會記得自己畫過,或許素描之類的就比較不會記得。但他沒打斷莫奇森。
運氣不錯。這會兒莫奇森一個人坐著,正在簽帳單,酒吧通往街上的門才剛開起來,搞不好貝納德剛離開。不過湯姆還是在大廳裡四處看了一圈,免得萬一貝納德只是去上洗手間,可能還會回來。湯姆沒看到貝納德,他等到莫奇森站起來要離開,自己這才走進酒吧。湯姆擺出沮喪且若有所思的表情,事實上他的心情也的確是如此。他看了莫奇森兩次,好像正在想著哪裡見過,其中一次莫奇森和他目光交會。
瑞夫斯不在,一個德國口音的男子說。
「對,諸如此類的。」
「真是一幅好畫。」湯姆說。
「巴黎?」那人驚訝地說。「我知道瑞夫斯打過電話到慕尼黑的四季飯店找你。」
「我就是不知道啊。我從他那裡什麼都問不出來。可是他大費周章跑來這裡看我,說他打電話到倫敦其他八家飯店過,然後才找到我。我問他怎麼知道我的名字,他說,『喔,閒話傳得很快。』很奇怪,因為我唯一談過話的,就是巴克馬斯特畫廊的人。你不覺得很怪嗎?我明天約了一個泰德畫廊的人碰面,但就連他都不曉得我是要找他談一幅德瓦特的畫。」莫奇森喝了點他的蘇格蘭威士忌,然後說,「那些畫是從墨西哥運來的——我明天去見泰德畫廊的瑞摩爾先生,除了把《時鐘》拿給他看之外,你知道我還打算做什麼嗎?我要問問,我或他有沒有權要求巴克馬斯特畫廊拿出收據或帳冊,就是有關那些墨西哥運來德瓦特畫作的證據。我有興趣的不是畫名,德瓦特先生也告訴過我,他不見得每幅畫都取了名字,我要查的是畫的數量。這些畫作運來英國時,當然會經過海關或什麼單位,如果某些畫沒有登記,那就有問題了。如果德瓦特本人也被蒙在鼓裡,而少數幾幅他的畫作——唔,比方有人說是四、五年前完成的——其實是在倫敦這裡畫出來的,那不是很令人吃驚嗎?」
「為什麼你不直接跟貝納德談呢?」
「什麼?」湯姆問。
「啊,老天,」傑夫哀嘆道。「不——不,貝納德不會https://m.hetubook.com.com洩密的。我不認為他會。」
「我不是收藏家,不過我還有很多其他油畫。」湯姆坐在最大的一張椅子上。「也希望你能看看。一幅蘇丁,兩幅馬格利特。」
「你今天晚些會在家嗎?」
「真的?那是傑作啊!《紅色椅子》。你住在倫敦嗎?」
湯姆眉頭深深皺起來。「真的?如果有人偽造德瓦特的作品,那就很嚴重了。那人說了些什麼?」
「沒有。」
我們在一起
「湯姆,你今天太了不起了,」傑夫說。「謝謝。」
現在貝納德真正的心理狀態到底怎麼樣?另外他到底打算做什麼?
「嗯。可是他的目的是什麼?」
「怎麼了,沒錯,我是在那兒。」莫奇森說。
「《椅中男子》。」
「輝煌飯店。」那名男子匆匆說。
媽媽不同意
「你知道嗎。」湯姆把畫撐在寫字檯上,將所有燈打開,站在房間另一頭觀賞。「這幅畫的確跟我的《椅中男子》有點類似。你何不去我家看看我的畫?我家離巴黎很近。如果你覺得我的畫也可能是偽造的,我就讓你帶回倫敦來給專家看。」
曼德維爾飯店的牆壁給人一種隔音的感覺——也或許是幻覺。湯姆已經好久沒唱過這首歌了。他很高興憑空忽然想到這首歌,因為這是一首歡欣的歌,湯姆覺得這樣會帶來好運。
莫奇森想查閱他們畫廊裡的收據,找出從墨西哥運來畫作的紀錄,如果他把這事情告訴傑夫,湯姆心想,傑夫一定會很恐慌。他明天上午一定要警告傑夫這件事,去找路邊的電話亭,或是郵局裡的公用電話。湯姆擔心飯店的接線生會偷聽。當然了,他希望能對莫奇森放棄他的理論,但如果辦不到,那麼讓巴克馬斯特畫廊準備一些看似真實的資料也不壞。
他們針對德瓦特古怪的個性聊了幾分鐘,然後湯姆說他看到莫奇森進入畫廊後頭的房間,他聽說德瓦特就在裡面。
莫奇森解釋了。他解釋自己為什麼覺得有人在偽造德瓦特的畫,湯姆專注聽著。問題在於,過去大約五年來,德瓦特使用的紫色都是群青加鎘紅所混合出來的(那就是在他死前了,湯姆這才明白,這個技法是德瓦特本人開始用的,而不是貝納德),但在《時鐘》和《浴缸》中,又回到他早期所使用的鈷紫。莫奇森自己也畫畫,他告訴湯姆,只是嗜好而已。
「那麼——你的意思是,會設法說服他之類的。」
傑夫也笑了,不過有點虛弱。「好吧,湯姆。」
「想到——只是或許,德瓦特畫得不夠多,於是康斯坦和班伯瑞就容忍少數幾幅偽作,好賣出更多德瓦特的作品,我還不敢說德瓦特也知情。但如果德瓦特健忘到連自己畫了幾幅畫都不知道,那不是很好和*圖*書笑嗎?」莫奇森大笑起來。
一名侍者過來。
十分鐘後,湯姆下了一層樓,回到自己的房間。莫奇森提議過兩人一起吃晚飯,但湯姆覺得最好說他約了人十點在貝爾格維亞區碰面,所以時間不太夠。莫奇森託湯姆幫他一起訂明天下午到巴黎的機票,莫奇森要來回票。湯姆拿起電話,訂了明天的兩個機位,星期三下午兩點,飛往巴黎奧利機場。湯姆自己有回程機票。他把班機資訊留給一樓櫃檯,請他們轉告莫奇森。然後湯姆點了一個三明治和一小瓶波爾多梅多克地區的葡萄酒。吃過之後,他小睡到十一點,然後請接線生替他接漢堡的瑞夫斯.米諾。花了快半個小時才接通。
「我不是專家,相信我,但我讀過幾乎每一本有關畫家和繪畫的書。不必是專家或用顯微鏡,就可以看出一種純色和混合色的不同,不過我的意思是,你絕對不會看到一個畫家回頭去用一個他刻意或無意間捨棄不用的顏色。我說無意間,是因為畫家選擇一個或更多新顏色,通常是無意間做出的決定。德瓦特並不是在每幅畫中都使用淺紫色,不見得。但我的結論是,我的《時鐘》還有其他幾件作品,順帶說一聲,包括你有興趣的《浴缸》,都不是德瓦特的真跡。」
「哦?我也有一張他的畫。」莫奇森以同等坦白的語氣說。
湯姆想搶付帳,但莫奇森堅持要簽他的帳。
「因為那樣不好。」湯姆不太高興地說。有些人就是一點心理學都不懂!
湯姆掛斷了。
「啊,這點沒有人能否認!」
「嗯,」莫奇森說,思索著。「那倒是可以。」
爸爸不贊成
「明天上午在米蘭的輝煌飯店。他搭今天晚上的火車到米蘭了。他不喜歡搭飛機,你知道。」其實湯姆並不知道。真奇怪,像瑞夫斯這種人居然不喜歡搭飛機。「我會再打給他。另外我現在不在慕尼黑,我在巴黎。」
「謝了。喝一杯也好。」
「好,那我就把泰德畫廊的約往後延。」
湯姆微笑,傑夫那種狂喜的口吻讓他很開心。「貝納德那邊你處理一下。我離開前會再打給你。」
「我們現在就上樓去我房間看吧!」
「我明天上午都會待在工作室的。」
莫奇森點了根他的切斯菲德牌香菸。「我的故事還沒說完。剛剛我才跟一個英國人喝過酒,他叫貝納德.塔夫茲,也是個畫家,他好像對德瓦特的作品有同樣的懷疑。」
湯姆決定冒個險,因為他受不了瑞夫斯了,他說,「我是湯姆.雷普利。瑞夫斯有留話給我嗎?」
「要我去飯店找你嗎,湯姆?你大概很累,沒辦法過來這裡。或者你可以過來?」
湯姆決定不要再去跟貝納德多說什麼。貝納德知道當初就是湯姆建議由他偽造的。湯姆去沖了個澡,開始唱起一首義大利民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