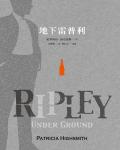十
「他有點個人危機,在倫敦。他對自己的作品很沮喪。另外我想他——他和他女朋友分手了,或者是她提出分手。不曉得。」
湯姆也努力思索著正確的答案,或許是「原創性」吧。但「知名度」這個字眼也掠過他的腦海。他等著貝納德說話。
「別擔心,你需要的東西我都有。」湯姆覺得克里斯看著他和貝納德,或許在推測他們兩個是怎麼認識的、到底有多熟。「餓了嗎?」湯姆問貝納德。「我的管家很愛做三明治。」茶點只有四個小三明治。「她叫安奈特太太,需要什麼儘管說。」
今天有個很可怕的風暴來襲。每個人都很緊張。風雨交加。
湯姆很好奇傑夫和艾德是不是給貝納德吃太多鎮靜劑了,搞得他現在不吃藥就不行?貝納德喝完茶,湯姆帶他上樓到那個小客房。
次日天色陰沉,九點左右開始下雨。安奈特太太出去關緊一扇老在砰砰響的護窗板。她一直在聽她的廣播節目,警告湯姆說廣播裡說有個嚴重的風暴即將來襲。
我想妳。妳收到那件紅色泳衣了嗎?我請安奈特太太寄航空的,給了她很多錢,所以如果她沒寄航空的,我就要打她了。每個人都問起妳什麼時候回家。我跟葛瑞夫婦喝了下午茶。沒有妳在身邊,我覺得很孤單。等妳回來,我們可以睡在彼此的懷抱裡。
湯姆在信封上貼好郵票,帶到樓下,放在走廊的小几上。
「要不要給你一件毛衣,貝納德?來一杯白蘭地暖暖身子怎麼樣?」
「沒關係。」貝納德望著湯姆。「莫奇森看了《椅中男子》後,說了些什麼?」
湯姆心中一陣刺痛,他可以理解貝納德的痛苦。
「好吧。如果你堅持的話,那我就等到明天再走。」他兩手插|進後褲口袋裡,走向落地窗。
湯姆沒吭聲,然後他說,「當然了,這種事把我們都嚇壞了。如果德瓦特還活著的話,或許就可以打發掉這事情。危險的就是這個——被人發現他其實已經死了。但我們會度過這個難關的,貝納德。」
畫框底部墊著一些報紙和一大塊用來擦顏料的抹布,是從舊床單上剪下來的。湯姆俯身認真畫著,不時後退看看。這是一幅安奈特太太的人像,或許頗具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的風格,這表示安奈特太太絕對看不出畫的是她。湯姆不是刻意模仿德庫寧,剛開始畫這件作品時也沒刻意想到他,但眼前這幅畫像看起來,無疑就是德庫寧風格。安奈特太太的蒼白嘴唇咧開,成了一抹粉紅色的笑容,泛灰黃的牙齒參差不齊。她穿著一件灰紫色的家居服,頸部有一圈白色的縐褶。整幅畫都以相當狂亂的長筆觸構成。這幅油畫的幾幅草圖,是湯姆在客廳裡把拍紙簿放在膝蓋上匆匆畫出的速寫,當時安奈特太太根本沒發現他在畫她。
此時風發出呼呼聲,後院裡一棵大hetubook.com.com樹都被吹彎了——他們兩個都看著窗外,目睹了這個景象,湯姆覺得好像整座房子也跟著彎了,他本能地矮下身子。怎麼有人在這種天氣裡還能保持冷靜?
「是啊,我匆匆忙忙就趕來了。」貝納德說。
「你說服他放過我。就當是同情我,可憐我。我不要被人可憐。」
是貝納德,一身又髒又溼,站在前門內的門墊上。湯姆覺得他深黑色眉毛下那對深色眼睛似乎下陷得更深了。貝納德看起來嚇壞了,湯姆心想。然後緊接著,湯姆想到貝納德看起來就像個死神。
現在安奈特太太隨時會走進來拉上窗簾了,湯姆心想,這樣至少可以平息一下眼前混亂的狀況。
但克里斯擁有狄奇那種冷靜,或者是源自於整個家族的遺傳,他只是微笑,對風暴帶來的騷動樂在其中。
狄奇.葛林里的一個堂弟來訪幾天,他名叫克里斯,是個很有教養的年輕人。他首次來訪巴黎幾天。想想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第一次看到巴黎?他很驚訝巴黎麼大。他家在加州。
中間停電了半小時,湯姆說這種事在法國鄉間常常發生,即使是很輕微的風暴,也會造成停電。
湯姆大笑。「可是你今天一定走不了!這是我住這裡三年來碰到過最壞的天氣。飛機降落時很不順利吧?」
那兩個聲音在講英語,但他聽不見在講什麼。克里斯和另一個人。貝納德,湯姆心想。有英國口音。沒錯,老天!
克里斯望著湯姆,眉頭專注地皺了起來,就像狄奇。「那傢伙瘋了!」他耳語道。「真的瘋了!」
「你得跟克里斯共用浴室,」湯姆說。「從這個走廊過去,穿過我太太的房間就是了。」湯姆走出來,房門沒關。「赫綠思不在家,她去希臘了。希望你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貝納德。你到底有什麼事?到底在擔心什麼?」
貝納德向湯姆微笑。「喔,好吧。」他說,好像只是為了讓湯姆高興一下。
「進來客廳吧!要喝點茶嗎?等安奈特太太下來,我請她去泡茶。坐吧,貝納德。」
貝納德搖搖頭。「我覺得自己好像走到盡頭了。如此而已。這回的展覽就是盡頭了。這是我能畫出的最後一次展覽了,最後一幅畫是《浴缸》。現在他們又想讓他——你知道——讓他復活。」
「你看!」克里斯指向草坪。
「一開始,他說那是假畫。但我說服他,讓他相信是真跡。」
「不是很熟。」
「莫奇森甚至跟我談到畫的品質。啊,基督啊!」貝納德在床上坐下,往後一倒。「莫奇森現在在倫敦做什麼?」
湯姆想到那幅畫中的鈷紫。現在對湯姆來說就像一種化學毒藥。對貝納德也是吧,湯姆心想。「你好久沒看過《紅色椅子》了。」湯姆說著站起來,那幅畫就在貝納德身後。
湯姆用法文跟她說,「妳可能得去幫貝納德先生準備那個小房間。」那是另一個客房,很少用,裡頭有一張單人床和_圖_書,他和赫綠思稱之為「小臥室」。「另外今天晚上貝納德先生要在這裡吃晚飯。」然後湯姆跟貝納德說,「你怎麼來的?從梅朗搭計程車?還是從莫黑?」
「不是。」但湯姆覺得很不安,因為他跟貝納德撒謊。湯姆撒謊很少會覺得不安的。湯姆可以預料,有一天他得告訴貝納德莫奇森死了。這是唯一能讓貝納德放心的辦法——至少是在偽造假畫方面,讓他放一部分心。但湯姆不能現在告訴他,眼前的暴風雨令人心驚肉跳,而且貝納德的心理狀態很不穩定,要是現在說了,貝納德一定會大怒而失控。「我馬上回來。」湯姆說。
湯姆坐下來寫信給赫綠思。寫信給她向來對他有鎮靜效果。碰到對自己的法文沒把握時,他通常都不會費事去查字典,因為他的錯誤可以逗赫綠思開心。
「我只能想到一個說服的方法,很瘋狂的方法。」
親愛的赫綠思:
湯姆緊握住貝納德的手腕。「貝納德,你是想搞得大病一場嗎?」
「很好,我會換衣服的。」貝納德說,還是一副敷衍的口氣,然後慢慢爬上樓梯,手上拿著鞋子。
而且我辦到了——湯姆真想說,但他和貝納德一樣保持一臉嚴肅。「唔,過去五年,本來就該讓大家以為他還活著啊。如果你不想再畫,我相信他們不會逼你的,貝納德。」
「希望你不介意我——這副樣子。」貝納德說。
安奈特太太從樓上下來,抱著一些毛巾或什麼的。「馬上去,湯姆先生。」
「這個問題大概不公平,」克里斯說。「我想,大部分優秀的藝術家不會在私生活中展現人格,或是浪費熱情。他們表面看來似乎再平凡不過。」
「我不認為莫奇森能被人說服,」貝納德說。「你不會跟我撒謊,好讓我心裡好過一點吧,湯姆?因為我實在受夠謊言了。」
貝納德立刻從床上起來,走向窗子,此時一陣大風夾著大雨,猛撲在玻璃窗上。
現在克里斯在客廳裡,坐在沙發上看書。他驚跳起來。「我想問一下——」他輕聲說。「你的朋友是怎麼回事?」
當然,是貝納德。湯姆打開落地窗,走進雨中,現在冷冷的大雨被吹得四處亂撲。「嘿,貝納德!你在做什麼?」湯姆看到貝納德沒反應,還抬著頭慢吞吞行走,於是湯姆衝向他。湯姆在階梯頂端絆了一下,差點整個人摔下去,還好在階梯底部穩住身子,一隻腳踝扭到了。「嘿,貝納德,進來!」湯姆大喊,一跛一跛走向貝納德。
湯姆保證不介意。現在安奈特太太也進來了,湯姆替他們介紹。
湯姆把調色刀小心翼翼架在松節油杯子上。出了畫室關上門,急步下樓。
「不曉得。但我知道他不會去見專家,也不會做任何事情了,貝納德——因為我已經說服他相信我們的說法。」他安慰地說。
「對,從梅朗。我在倫敦一張地圖上查到了這個小鎮。」貝納德身材細瘦而稜角分明,像他的字跡,站在那m.hetubook.com.com邊搓著手。連他的西裝外套似乎都溼透了。
貝納德不記得了。他雙眼緩緩移向——他自己畫的——壁爐上的那幅《椅中男子》,然後又移開目光。
湯姆的努力有了回報,貝納德臉上出現一抹很淡、卻真誠的微笑。「是的,真美。」貝納德輕聲說。
「啊,他們會試的,傑夫和艾德。但我已經畫夠了,太夠了。」
「你剛認識他,我是說,親眼看著他的時候,就感覺到這種人格嗎?」
「你得去換掉這些溼衣服,」湯姆說。「我去找些衣服讓你換。」湯姆正在脫自己的鞋。
妳寂寞的丈夫 湯姆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你認識他?」克里斯問。
克里斯也過來陪著湯姆。「你全身都溼了!」克里斯說著笑了一聲,伸出一隻手想抓貝納德的胳臂,但顯然不敢碰他。
「我真不希望打擾你太久。」貝納德說。
「唔——如果貝納德想私下跟我談,這房子裡面有很多房間,可以讓我們講話。別擔心了。」
湯姆想不透,他究竟該拿貝納德怎麼辦?如果警察回來找他,到時候貝納德在場,就像昨天早上克里斯在場那樣,該怎麼辦呢?貝納德的法文不錯,湯姆心想。
貝納德緊張地望著克里斯,好像期望他先坐下之類的。但接下來,湯姆才明白貝納德是看什麼都很緊張,即使看著茶几上的一個菸灰缸也不例外。他們的談話跟之前一樣陷入膠著,貝納德根本只希望克里斯離開。但湯姆看得出來,克里斯似乎沒搞懂,反而以為他在場可能會有幫助,因為貝納德顯然處於一種狀態。他講話結結巴巴,雙手顫抖。
湯姆出了房間到走廊上。
安奈特太太端著茶和茶點過來。
「什麼意思?」湯姆問,微笑著,心裡有點驚恐。
「我想他們明白的。別擔心了。我們可以——嗯,德瓦特可以再度隱居。在墨西哥。接下來幾年,我們就說他繼續在畫,但是拒絕展出任何作品。」湯姆邊說邊來回踱步。「過了幾年之後,我們就說他死了,把他那些新作全都燒了,諸如此類的,這樣就再也沒有人會看到他了!」湯姆微笑。
「我在想——既然他的狀況這麼怪——是不是我離開比較好。就明天早上吧,甚至今天晚上」
「是啊,沒錯。」克里斯微笑著說,似乎很高興多了人來作伴。
「你需要休息,貝納德。要不要吃安眠藥?我有一些劑量很低的苯巴比妥,四分之一格令的。」
「可是我覺得打擾到他了。貝納德。」克里斯扭頭望向樓梯。
「啊,今天晚上絕對不行,克里斯。這種天氣怎麼走?不,你不會打擾到我的,待在這裡沒關係。」
「是人格,」貝納德謹慎地說。「那造就了德瓦特。」
「不必了,謝謝。」貝納德把茶杯放回碟子上,發出三次清脆的碰撞聲。
「你好。」貝納德說。他腳邊放了個粗布旅行袋。
「我沒提到你,絕對沒m.hetubook.com.com有。」你瘋了——湯姆很想說。貝納德瘋了,或至少暫時精神錯亂了。然而剛剛貝納德說的,卻正是湯姆在地窖裡殺掉莫奇森之前所試圖做的:說服他放過貝納德,因為貝納德再也不會畫任何「德瓦特」了。湯姆甚至試圖讓莫奇森了解貝納德很崇拜德瓦特這位死去的偶像。
克里斯已經回自己房間了,湯姆看到裡頭開了燈。暴風雨讓整棟大宅暗得不自然。湯姆進了自己房間,從最頂端的抽屜拿出伯爵的牙膏。把底部往上捲一點,這管牙膏就可以留著自己用了,免得丟進垃圾桶可能會被安奈特太太看到:很難解釋,又實在太浪費了。湯姆從盥洗槽拿了自己的牙膏,放進克里斯和貝納德共用的那間浴室。
「那是什麼?」一棵樹倒了,湯姆原先這麼以為,小事一樁。他看了好一會兒,才看出克里斯所看到的,因為外頭太暗了。湯姆認出一個人影緩緩走過草坪,他第一個念頭是莫奇森的鬼魂,驚跳了一下。但湯姆不相信世上有鬼。
三個人一起走向屋子,但走得很慢,因為貝納德似乎想淋到每一滴雨。貝納德心情很好,在落地窗旁脫掉鞋子、免得弄溼地毯時,還講了些開心的話。他也把西裝外套脫掉了。
午餐後,湯姆上樓到他作畫的房間。有時畫畫能有助於紓解緊張。他站在他的工作台前,畫布豎直了靠在一個沉重的鉗台上,後頭還有幾本沉重的藝術書籍和園藝書籍。
「你能不能告訴我,」克里斯朝貝納德開口,「讓一個畫家好或不好的因素是什麼?比方說,我覺得現在有好幾個畫家的畫風都很像德瓦特。我一時想不起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名氣不大。喔,對了,有一個是帕克.拿諾里。你知道他的作品嗎?讓德瓦特這麼好的原因是什麼?」
貝納德可能完全沒聽到這段話。他說,「你跟他提出要買《時鐘》,或是類似的事情嗎?」
「不。我說服他說,德瓦特一定是又回去用他早期的那種顏料——可能一、兩幅,或是三幅。」
「安奈特太太,麻煩燒點水泡茶好嗎?」湯姆問。
樹林的方向傳來一聲不祥的劈啪聲,感覺很接近,湯姆朝窗外望去。松樹和楊樹的樹頂依然被風吹得彎折,但即使樹林裡有什麼樹被吹倒,他站在這裡也看不到,只能看到一片灰綠色的幽暗森林。有可能剛剛到了一棵樹,甚至是一棵小樹,蓋住那個該死的墳墓,湯姆心想,希望如此。湯姆剛調了一些紅褐色顏料,正要畫安奈特太太的頭髮——他希望今天能完成這幅油畫——此時聽到了樓下傳來的人聲,或者他以為自己聽到了。兩個男人的聲音。
貝納德轉向他們,露出微笑,雨水從他前額的黑髮流下來。「我喜歡這樣。真的。我覺得好喜歡這樣!」他甩掉湯姆的手,舉起雙臂。
「這位是克里斯.葛林里,」湯姆說。「這位是貝納德.塔夫茲。或許你們已經自我介紹過了。」
「貝納德!」湯姆說。「歡迎!」
「你跟他熟hetubook.com.com嗎?」
「我在這裡真沒見過這樣的。」湯姆午餐時說。
「對。」貝納德又坐下。「可是不像——不像德瓦特那麼好。」
「是的。」貝納德說得更堅定了。但這番對話讓他坐立不安,或許是覺得很痛苦吧。同時他的深色雙眼似乎正在努力思索,想針對這個主題找點話來講。
此時他們又回到貝納德的「小臥室」,門關上了。
「你是畫家嗎?」克里斯問。
安奈特太太問貝納德要不要把外套掛起來。
「要不要我拉上這些窗簾?」
風雨讓湯姆焦躁不安。這天早上他和克里斯是別想去觀光了。到了中午,風暴更加惡化了,高大楊樹的頂端都被風吹彎,看起來像鞭子或劍尖。偶爾樹上會有一根樹枝——大概是比較小或早已枯死的——被吹落朝屋子撲來,撞到屋頂後滾下,發出聒噪的聲響。
湯姆皺臉往後縮了一下,但貝納德沒有。湯姆進了自己房間,拿了睡衣褲和一件馬德拉斯細棉印花布的睡袍給貝納德,還有室內拖鞋,加上一把包在塑膠盒內的全新牙刷。他把牙刷放在浴室裡,以防萬一貝納德沒帶,其他東西則拿進貝納德房間。他告訴貝納德,如果需要什麼,他就在樓下,然後說接下來他就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怎麼可能?莫奇森把他的想法跟我說過——那些淺紫色。他說得沒錯。我犯了三次錯,《椅中男子》、《時鐘》,然後這回是《浴缸》。我不曉得是怎麼發生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根本沒在想。莫奇森是對的。」
貝納德站起來轉身,雙腿還是抵著沙發。
現在開始打雷了。湯姆挺直身子呼吸,胸部因為緊張而發痛。在他的電晶體收音機裡,「法國文化」電台正在訪問一個聲音很難聽的作者:「在我看來,雨布洛(還是厄布藍?)先生(爆擦音)……似乎偏離了——就像幾位評論家說過的——你到目前為止對反沙特主義觀念的挑戰。但現在似乎顛覆了……」湯姆突然把收音機關掉。
貝納德點點頭。「啊,是的。」他清瘦的雙手緊緊抓住一邊膝蓋。
「要不要梳洗一下?別擔心克里斯和我。我們不會吵你的。如果你要一起吃晚餐的話,就八點到樓下。要是想喝杯酒,就提早下來。」
貝納德憂鬱的雙眼看著地上,讓湯姆覺得自己好像講了個笑話,聽眾卻沒聽懂。或者更糟,好像他褻瀆上帝,在大教堂裡講了一個爛笑話。
「喔,不,不,謝了。」
「你不進來嗎?拜託,貝納德。」
「貝納德,你沒帶行李箱吧?」湯姆問。湯姆知道他沒帶行李箱,擔心他會住得不舒適。
湯姆點點頭,很怪異地發著抖——每次他跟一個腦袋不太正常的人相處,就會發抖,那是一種筋疲力盡的感覺。這回提早發生了:通常要二十四小時之後,他才會開始發抖的。湯姆小心翼翼活動著腳踝,走了幾步。應該不嚴重,他心想。「你說得可能沒錯,」他跟克里斯說。「我上樓去找些乾衣服給他。」
「不用了,謝謝。」
「是貝納德!」克里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