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的東西,心想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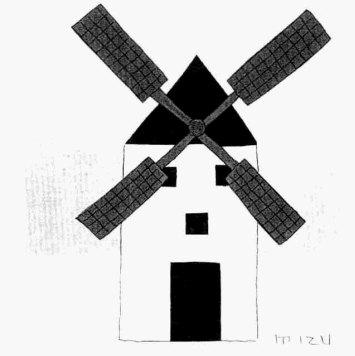
大衛.希爾頓的季節
我才剛成爲二十九歲,從那年春天開始寫小說(般的東西)。寫小說(般的東西)是我有生以來頭一回。養樂多燕子隊是球團創立以來,在從未經驗過冠軍之下正迎接第二十九個年頭的球季。不用說,這兩個事實之間並沒有任何關連。只是純屬巧合而已。
神宮球場的開幕賽,開賽的下午一時我一邊躺在草地上一邊喝著第二口啤酒。廣島隊投手是高橋(里),然後走進第一個打席的是他。看到他的身影可能有幾個觀眾笑了。而另外幾個則可能體内忽然感覺到類似新鮮預感般的東西。笑的原因當然是他那奇怪的打擊姿勢。站在擊球區中,簡直像蹲下般笨拙地彎著身子,邊團團轉著筆直站立的球棒頭,邊半挑戰、半畏怯般盯著高橋投手的手套。我甚至想到,這裡或許真的是鬥牛場啊。
晴朗。
他的名字當然是Dave Hilton(大衛.希爾頓),那年最佳球員的二壘手,到夏天即將結和*圖*書束時打擊率守住頂尖的男人。您可能還記得他的名字。七八年是爲他存在的球季,而且那才是兩年前的事而已。
但結果對我來說的大衛.希爾頓,則是穿著有破綻毛衣抱著超級市場紙袋的一個窮相美國人。
那個球季,他每打完球就全力衝刺,而且有時繼續嘗試絕望性的頭前滑壘(head-first slide)。報紙(不是體育新聞那種)用整版專欄全面讚美那比賽。他在緊要關頭日本職棒球季決戰的第四戰最後一局,將今井雄太郎的曲球以難以相信的揮擊打進西宮球場左翼的幸運區。而且整年之間從神宮球場的選手出口到球員休息室間的短短路程中,我沒看過比他更認眞和球迷握手的選手。
這篇稿子是為《數字》(Number)雜誌1980年10月5日號所寫的。相當久以前了。我在家裡翻找舊資料時無意間忽然冒出來。因為很懷念所以稍微整理後收錄進來。這次開幕比賽的廣島隊投手,我記得一直是外木場,其實是高橋(里)。內容上有幾個細微事情上的錯誤(當時還沒有維基Wikipedia網站),為了保持文章的流暢而維持原來的樣子。hetubook•com•com
再見,Dave Hilton。
那年年初,我搬到神宮球場附近(幾乎只因爲是在神宮球場附近),一有空閒時間每天都到外野席去報到。比起少年時代一樣常去的甲子園球場,當時的神宮完全看不出是職業棒球賽的球場。說是偏僻地區的鬥牛場或許氣氛更接近。外野沒有椅子席位,半禿掉的草地斜坡一下起雨來就變得泥濘不堪,風強的日子,耳洞裡全是沙子。雖然如此無風的晴朗午後的神宮球場外野席,至少東半邊球場是最舒服,而且最溫暖人心的外野席。手寫式得分板頂上坐著幾隻無聊的烏鴉,在春天的陽光下戴著燕子隊https://www.hetubook•com•com球帽,好事的孩子們在斜坡上到處躺著玩耍著。
(img310)
而且,雖然是事後想起來的,那裡還有一個,新鮮預感般的東西。這並不容易說明。就算光是瘦瘦的駝背外國選手已經是夠「新鮮」了,但那如何能跟「預感」結合起來呢?不過預感這東西說得誇張一點,如果是被神所愛的人一時的光輝,那裡確實有。只有他的周圍,有春天的陽光特別多照一點般的氛圍。看來也像是他從亞歷桑納(大概)的小鎮帶進東京的運動場來的,他的靈魂的一片,受到那陽光照射而正閃爍著光輝。
那是個美麗的季節。養樂多燕子隊,一九七八年。
那是即將迎接日本球季大賽的十月初一個陰雲的星期天。接近傍晚時分,眼睛看不出程度的初秋細雨開始微微濡濕路面。我和妻子走出廣尾的超級市場時,巴士招呼站附近帶著小孩的美國夫婦正要招計程車。那小個子的美國人把兒子放在肩https://www.hetubook.com.com膀上,左手抱著超級市場的紙袋。孩子對著站在身旁少女般的母親笑著,她轉向丈夫微笑,父親邊笑邊以淺藍色眼珠一直仰望著兒子。
然而這裡還有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我現在要談的,就是關於他的簡短故事。不,也談不上故事。我對他的了解,並不足以到說故事的地步。只是接近片段而已。他的一個片段。藉著所謂季節這利刃切取下來,他的靈魂的一片。那一片在一時之間在人們心中——至少在我心中——徘徊之後,終將逐漸失去那鮮度,消失到壓倒性的時光之流中去。
正當廣岡當教練,正當松岡是主力投手,正當若松是強棒。查理.曼紐兒(Charles Fuqua Manuel)敲了一支全壘打到後樂園球場的最上層,大矢以捕手如鐵壁般守住本壘。
有什麼打動我的心。和在開幕賽中我所感到那預感類似的東西,還在那裡。而且我感覺到有生以來,從沒看過這麼不含雜質的純粹幸和_圖_書福情景。他們說起來,是穿著樸素、外表平凡的美國一家人。但他們臉上沒有所謂陰影這東西。簡直就像在下著小雨的黃昏射進來的一線陽光那樣,他們的微笑明亮而光輝。那使他們成爲某種特別的存在。打動我的心的,或許是那樣的光輝中令人有點心痛程度的幸福感。
Dave Hilton……字有點晃動也沒辦法啊,你正抱著兒子和紙袋,要招計程車嘛。
然後七八年的球季就結束了,一切都變了。那美好的季節再也沒有回來過。但我(或你)又能怪誰呢?從亞歷桑納來的和我同年齡眼睛溫柔的青年,消失到所謂season季節的時光流沙中去了。只不過是這麼回事而已。
這是當時他的簽名。
回到七八年的四月一日。
那是了不起的安打。球把左場和中場間切成兩半,格烈特和山本浩二追到球時他已經站上二壘壘包。我想那是整個球團七八年球季的第一支安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