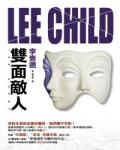8
「我想他不會的,問題出在那個簽名是假的。」
我說:「因為太多花招了。兇手做了六件事:把他脫|光、把兵籍號碼牌拿走、切掉他的性器官、拿樹枝戳他、倒優格在他身上,還有用皮帶勒他。真的要表達自己的看法,拿其中兩、三件出來做也就夠了。我感覺兇手是試著要讓我們知道他的想法,而不是很自然的要表達些什麼,太過火了一點。」
還不到五分鐘,桑瑪就回電了。
我又聳聳肩說:「有一點。如果我能開著七十噸的坦克橫掃千軍,哪還需要什麼心理戰?」
她問:「那人是誰?」
「那不可能,除夕夜那天,蓋伯在電話上知道我被派來這裡,還感到很訝異。」
「也許妳會提供專業的意見。」
「今晚的案子跟心戰課程無關。」
「書裡?」
我說:「嗯,我知道。」
諾頓坐在一張陸軍的制式大書桌後面,桌上到處都是打開的教科書。因為還要查閱的書實在太多,所以她把電話機從桌上移開,放在地板上。她眼前有一本橫格黃紙筆記簿,上面有一些手寫的筆記。桌燈打在簿子上,紙的顏色反射在她的頭髮上。
她說:「還有他背上的液體。」
桑瑪說:「但是這種調動有意義嗎?為什麼要把你調過來,但是又把蓋伯調走?這樣不是兩相抵銷了?」
我們在那裡等著,天空沒有月亮與星星,除了汽車的頭燈與怠速中的引擎之外,沒有任何光線與聲音。我想到了里昂.蓋伯,韓國的美軍憲兵部隊是陸軍最大的憲兵單位之一,儘管不是最體面的工作,但可能是最有事可做,而且當然是最難做的一份差事。大家都搶著當那裡的憲兵指揮官,這意味著他在退休時可能會是二星中將,這比他過去所奢望的結果都要好太多了。如果喬伊說得對,而且部隊真的開始要砍人,蓋伯已經獲得了免死金牌。有十分鐘的時間,我為他感到很高興,然後我又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他的處境,又為他擔心了十分鐘,但是並未得出結論。
「裝甲部隊上我們的課,讓你覺得很奇怪嗎?」
她說:「皮帶這個部分讓我懷疑,不是只有同性戀才會自|慰,只要是男人都會有這種高潮的生理反應,跟是不是同性戀無關。」
我找了一張訪客椅坐下。
「那又怎樣呢?」
「真的嗎?」
屍體趴在一棵樹下一堆結霜的落葉上,全身一|絲|不|掛,中等身高、身材結實。是個白人男性,但他身上的肌膚到處都是血漬。他的手臂與肩膀上到處都是深可見骨的刀痕,從後面我可以看到他的臉被人打得腫了起來,臉頰凸出。他的兵籍號碼牌不見了,一條細細的皮帶緊緊勒在他脖子上。皮帶上有銅環,皮帶尾端長長地拖在後面。他的背上沾有一種淡淡的粉紅色黏稠液體,一根斷掉的樹枝被|插|進他的肛|門裡,地面上留有黑色血漬。我猜當我們翻動他的身體時,就會看到他的生殖器被人切斷了。
她沒有回話。我把那些清單整理成整齊的一疊,放回檔案夾裡面,然後把最上面那張紙條拿掉——希望你媽沒事。我把紙條丟進抽屜裡,把檔案夾交給她。
「心戰課程裡沒有。但這裡的人大多會看雜誌,或者看A片。」
「但是那個壞人要贏實在太容易了,他可以用那一件投訴案逼你退役,或者把你送進監牢。」
我點頭說:「就憲兵而言,我還挺聰明的。」
「你需要的是哪一種人?」
她說:「顯然他是個同性戀,可能因此被殺害。如果不是的話和_圖_書,至少殺他的人對他的性向也一清二楚。」
「那脖子上的皮帶呢?」
她說:「殺人手法不是課程內容。」
「一般人都想得到那些手法。」
「做妳這種工作的人。」
「最後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她搖搖頭:「不過那已經是個老笑話了。」
「背後到底有什麼陰謀?」
「我們的確還在基地裡?」
我說:「蓋伯的確有被升遷的價值。只不過這個升遷來得太早,那可是一份一星少將的差事,國防部必須向參議院報准,一般都是在秋天才會往上呈報,不是在一月。有人在驚慌失措中臨時進行這個部署。」
「她的看法跟我一樣,也覺得這是一樁被偽裝成針對同性戀的謀殺案。我問她有沒有哪一個手法是心戰課程裡面教過的,她並沒有正面回答。她說一般人也想得出那種手法,還說她討厭被問東問西的。」
她說:「你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我給意見吧?那都只是前奏而已,因為你自己就可以判斷了。」
我說:「他們會呻|吟,然後把優格倒在愛人的背上。」
她說:「少校,有什麼可以為你效勞的?」從這句話聽來她像是波士頓人,而且在這深夜被人拖來這裡,並不是很高興。
我聳聳肩說:「不過我不是為了偏袒陸軍,我不是說這傢伙一定不是同性戀,也許他是,但我不在乎。也許殺他的人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只是想說,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這都不是他被殺的原因。只是兇手希望別人以為那是動機,不過他們想讓別人有這種感覺,其實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兇手才精心地布置了那麼多線索。」接著我頓了一下,「不過這些手法像是從書裡學來的。」
我點點頭。
我回到悍馬車,用無線電通知我的中士發生了什麼事,要她找到桑瑪中尉,請她用無線電的緊急頻道呼叫我。等了兩分鐘後,來了一輛救護車,接著是兩輛悍馬車,它們載著我在離開辦公室前打電話通知的鑑識專家。大夥兒下車後我叫大家等一下,因為還不急著進行採證。
我說:「我不知道。我想他應該已經面目全非,因為毆打他的人下手實在太重。我們得用指紋來確認他是誰,或者牙齒,但前提是他曾留下紀錄。」
「這些都是妳的第一印象,那妳的意見呢?」
她說:「抱歉,雖然你叫我不要碰,但我還是稍微移動了一下屍體。」
她問我:「諾頓說了些什麼?」
「你們上課時會教這些東西嗎?」
「也許這是一場兩個人的角力比賽。一個好人,另一個是壞人。有一個會贏,一個會輸。」
「為什麼?」
我打電話給幾個專家,到汽車調度場要了一輛儀表板上夾有一支手電筒的悍馬車。發車後我遵照那個大兵給的方向,穿過基地裡有住人的區域,朝著西南走,經過一條崎嶇不平的沙地通道,到了基地的荒地。我在一片漆黑中開了一哩多的路程,才看到遠處有另一輛悍馬車正亮著頭燈。那位大兵的車斜斜地停在距離通道二十呎外的地方,他用遠光燈打進樹叢裡,整個林子裡面充滿了駭人的陰影。他靠在車頭引擎蓋旁站著,低頭看著地上。
「為什麼?」
「他說我不能讓妳參與特調組的案子,這是一般的憲兵業務。」
「我猜你會在他的嘴裡發現他的睪丸跟陰|莖。如果只是被打而已,雙頰應該不會那麼腫,顯然兇手有話要說,那是一種同性戀恐懼症的表現,把他認為被不當使用的器官移除,似乎在m.hetubook.com.com模仿口|交的情況。」
我說:「好,大夥們,幹活了!」我坐在車裡看著四處彌漫的黑煙,手電筒的光線不斷照射在地上,相機閃光燈的明亮藍光不斷閃爍著,忙著捕捉周遭的動作。我又用無線電聯絡我的中士,要她把基地的太平間打開,並且找一個病理科醫師一早到太平間待命。三十分鐘後救護車倒車開進路肩,大夥們把用白布蓋好的屍體裝進車裡。他們把門關上,拍兩下後車就開走了。他們蒐集了許多裝滿證物的塑膠袋,貼上標籤,用封鎖犯罪現場的膠帶纏繞在樹幹上,封起了一個長五十碼、寬四十碼,大致上呈長方形的區域。
我說:「幹得好。」
她的臉做了一個表情後才說:「好。」
我點點頭。
結束通訊後,我下了車,跟那一群醫務跟鑑識人員會合。大家都在寒冷的室外站著,而且都沒把引擎關掉,讓電池繼續充電,暖氣也持續開著。空氣裡彌漫著柴油引擎的廢氣,堆積形成一團黑煙。我要鑑識人員先把沿路的衣物記錄下來,不要碰它們,也不要動到陳屍處。
她問我:「如果我們看到的是花招,那真正的理由是什麼呢?」
「我想跟她見面。」
「還有,我討厭被問東問西的。」
我說:「那是優格。」
「威拉說你不能再跟我一起工作。」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我把車停在他的車旁邊,從儀表板上把閃光燈拿下來,走進外面的冷空氣裡之後我馬上解答了自己的疑惑。從通道上就開始有散落的衣物,一路通往林子裡。斜坡的頂端擺了一只靴子,那是部隊配給的制式黑色戰鬥皮靴,又老又舊,不是擦得很亮。往西一碼外是一只襪子,然後依序是另一只靴子、一件戰鬥服的外套以及一件綠褐色的汗衫。這些衣服被排成一條直線,兇手以誇張的手法模仿夫妻之間的情趣遊戲:男人回家後發現老婆的貼身衣物散落一地,沿著衣服登上階梯後,一路領著他們走向臥房。不過,外套與汗衫上面沾滿了黑色的血漬。
她說:「嗯。」她沒有露出微笑,而且她還看我會不會笑。
我說:「大概是這樣。」
她說:「只有三角洲特遣隊。」
我說:「我的工作就是保護陸軍。」
「你為什麼要找諾頓去現場?」
我還沒想完,桑瑪就出現了。她開著悍馬車,前排乘客座位裡坐著一位沒有戴帽子、穿著戰鬥服的金髮女性,與桑瑪相距四呎遠。她把車停在通道中央,頭燈朝著我們這個方向打過來。她留在車上,那位金髮女士下車後掃視了一下人群,走進了幾輛車頭燈交會的區域,直接找上我。為了表示敬意,我先向她行禮,看了一下她的名牌,上面寫著:諾頓。她的衣領上縫了代表中校的橡樹葉軍徽,年紀比我稍長,但沒大幾歲。她長得又高又瘦,如果本來沒有從軍,靠她的臉蛋就可以讓她當上女演員或模特兒。
他點頭說:「我們在距離圍籬一哩遠的地方,不管從哪個方向算都是這樣。」
我點點頭。
「你先說。」
「還有,他的肛|門被|插入異物,兇手的意圖非常清楚。」
她說:「嗨。」
她還是不發一語,然後在燈下仔細端詳我,也許正在打量我。
我說:「中尉,我准許妳隨意發言。」
「那個辦事員為什麼要對你說謊?」
「但兇手有可能上過你們的課?」
「因為妳在這裡服役,如果要從別處調人來,還要好幾個小時。」
「他說上面有蓋伯上校的簽名。」www.hetubook•com.com
我說:「至少你沒暈倒。」
我點點頭。
「你們會討論如何質疑敵人的性傾向嗎?」
「我也不知道。不過,肯定有人在後面主導。我哥說我應該查出來誰那麼希望我能在這裡,因此大老遠從巴拿馬把我調過來。所以我才會去問那個辦事員。現在我們也可以問一個跟蓋伯有關的問題:誰那麼希望他被調離岩溪鎮,還特地找了一個混球來取代他?」
「我問的不是這個問題。」
我說:「嗯。」
她點點頭,把頭髮往後甩。
她說:「因為工作。」
我又沿著衣物走回通道上,走到大兵身邊。他還是瞪著地上。
我說:「好,那是歸我們管沒錯。這傢伙是陸軍的,又死在陸軍的地盤裡。我們在這裡等,直到我下令之前,不要讓人進去那裡,清楚嗎?」
她說:「全身赤|裸以及兵籍號碼牌不見的情形也是一樣。把他身上有關陸軍的東西拿走,就等於把陸軍裡的變態都趕出去。」
她還是沒有微笑:「我們的確也教裝甲部隊。我記得,如果裝甲部隊沒有獲得跟步兵一樣的東西,克拉瑪將軍會很不高興。裝甲兵與步兵之間的競爭是很激烈的。」
我把手電筒給她,對她說:「沿著衣服走到最後,不要碰任何東西。只要牢記妳的第一印象,然後我們談一談。」
我說:「除了我以外。」
「現在怎麼辦?」
我點點頭,說:「好。」
她不發一語,只是把手電筒拿走,然後就離開了。前面二十幾呎的路程因為憲兵大兵的車輛還向著樹林,有它的頭燈照射著,所以光線很充足,她的陰影在她前面跳著舞。接著她走出了頭燈的照射範圍外,我看到她的手電筒光線繼續往前移動。接著我看不到光線,只有在遠處隱約從枯樹下方往高處透露的反光。
我說:「嗯。」
「妳為什麼跟他見面?」
「剖析犯罪不是我的專長。」
「優格呢?」
「你們也教裝甲部隊?」
我說:「我打電話到岩溪鎮,要一個辦事員查一查把我從巴拿馬調來這裡的派令影本。」
「所以你不是針對我?」
她並未微笑,只是對我說:「你我都是軍官,應該知道依法同性戀是不能服役的。不過這個結論是出於我們的判斷,不是為了為陸軍辯護。」
桑瑪說:「這兩件事不是同一個人做的。不管是誰把你調過來的,那個人都願意讓蓋伯離開,而且還有足夠的權力把你留下來,幫你把投訴案擋下。那個人的權力大到威拉知道自己沒辦法對付你,即使他可能想,也動不了你。你知道這樣有何意義嗎?」
我跟她說:「樹林裡發現了一具男屍,我要妳幫我找之前妳說的那位心戰女軍官過來。」
她直視著我:「你是不是要問我,樹林裡的案子是不是我們的課程造成的?」
大部分位於鄉間的陸軍基地都很大,就算部隊使用的設備不多,設備周圍還是會留有許多不用的空地。這是我第一次到博德堡來,但我猜這裡也不會有什麼兩樣。這裡的地勢就像一個整齊的小鎮被一塊馬蹄形的國有貧瘠沙地包圍著,旁邊有低矮的小丘陵與淺淺的山谷,覆蓋著不怎麼茂密的樹林與灌木叢。在這基地的漫長歷史中,裡面曾經種過的樹一定包括了比利時亞登高原的櫸木、中歐的堅硬冷杉,還有在中東四處飄揚的棕櫚樹。一代代步兵在這裡接受時有更迭的訓練理論,裡面有老舊的戰壕、散兵坑,還有用來射擊的土坑。裡面會有靶場、裝有鉤刺鐵絲網的障礙物以及https://www.hetubook.com•com獨立的小屋——心戰軍官用這些小屋來訓練男性軍人的情緒穩定度。這裡也會有一些混凝土地下碉堡以及與政府單位一模一樣的建築物,讓特遣隊用來訓練解救人質的任務。至於那些越野的跑步訓練場地,往往有些被整得不成人形的步兵菜鳥會在場上累得步履蹣跚,甚至有些人會倒地不起或死掉。整個基地外圍會有一層生鏽的古老鐵絲網,牆邊每隔三個崗哨就會掛有「國防部所有,軍事重地」的牌子。
我說:「我同意。問題是,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些都是騙人的。」
我問她:「妳有查過諾頓以外的女軍官嗎?」
我離開座椅,往門邊走去。
「你為什麼要我去一趟?」
我又打了一個呵欠。我說:「關於這一點,我沒話說,問題不在於要在我跟蓋伯之間進行選擇。」
「長官,你的意思是?」
「窒息呢?」
她說:「見過一、兩次,你問這個做什麼?」
她聳聳肩說:「那暗示著一種自|慰的技巧。在高潮的過程中,輕微程度的窒息會帶來快|感。」
「但是被調到韓國,的確算是高升。不是嗎?」
我說:「我也不知道。我還沒那麼聰明。」
我說:「別擔心。」
我第一個疑問是:一個在夜裡開車巡邏的傢伙怎麼會發現遠遠地藏在樹林偏僻處的屍體?
她說:「可能是草莓口味的,或者覆盆子。這是個陳年的橋段了。同性戀怎樣假裝高潮?」
「只有這樣才講得通,蓋伯不可能忘記自己在四十八小時前才剛剛把我調過來。」
「結果呢?」
她說:「好。」然後就帶著檔案朝門邊走。
我不發一語。
「諾頓中校嗎?」
我不發一語。
「這裡的人似乎很喜歡做一件事,就是提醒安卓雅.諾頓,要她記住自己是個像書呆子一樣的學者,其他人才是真正在外面幹活的人。」
她點頭說:「會討論到,那是必須的。切除敵人的性器官是很常見的,史書上到處可見,曾經發生在越戰,過去十年來阿富汗的婦女也這樣對待她們抓到的蘇聯士兵。我們會討論這種事的象徵意義,還有傳達了什麼訊息,以及它所製造出的恐懼。很多書專門討論這種可怕創傷所造成的恐懼,這對敵軍總是有效。我們也討論用異物傷害敵人,並且把被戕害的屍體展示出來,被丟得到處都是的衣服也是常見的。」
「我知道我自己是個教書的,不需要常常有人來提醒我。」
「最近沒見過?」
我說:「我要妳幫我看看。」
我在辦公室外面停留了一下,中士端了杯咖啡給我。走進辦公室,桑瑪在裡面等我。因為克拉瑪的案子已經結案,她來把她列的清單拿走。
我讓他們獨自完成善後的工作,在黑暗中把車開回基地的主要辦公區。我問了一個哨兵,找到心戰部門的方向。那是一座低矮的磚造建築,從它綠色的門窗看來,當初它蓋好時應該是軍需官的辦公室。它距離基地總部挺遠的,大概就位於總部與特遣隊營區之間的中間點。建築物周遭一片漆黑寂靜,但是中間走廊以及其中一間辦公室的燈光是亮的。停好車後我走進去,經過那些鋪著暗色瓷磚的走廊,走到一扇上半部裝有卵石花紋玻璃窗的門前。有燈光從玻璃後方透出來,門上用噴漆噴著「諾頓中校」的名字。敲門進去後我看到一個整齊的小辦公室,裡面很乾淨,聞得到女性的香味。我沒有再對她敬禮,我想我們之間已經不需要那樣客套。
「好什麼?」
諾頓說和*圖*書:「一點都沒錯。」
她反問:「你有什麼看法嗎?」
「為什麼是我?」
她回頭看我,「你不會比蓋伯重要,那是不可能的。」
她瞪著我,「這表示有人覺得你比蓋伯還重要。所以蓋伯走了,可是你卻還在。」然後她把頭別開,陷入沉默。
「我不知道這件事,我剛被調來,我只是希望做妳這種工作的人來給意見。」
我說:「那些刀傷跟毆打又該怎樣解釋?」
她說:「那是憎恨的象徵。」
「從現場的跡象看來,應該有些地方是妳能了解的。」
她消失了大概十分鐘,然後手電筒的光線又往我們的方向移動。她循著原路從樹林裡走出來,直接走到我面前。臉色慘白的她把手電筒關掉,遞還給我。
我不發一語。
「我要妳帶她過來。」
諾頓不發一語。我說:「太過火了。那就好像把人射殺之後又想勒死他,然後戳死他、淹死他,讓他窒息,然後再痛毆他。難不成想把他當成謀殺案的展示道具嗎?」
我問他:「這裡的精確位置是哪裡?」
我問她:「妳在爾汶堡見過克拉瑪將軍嗎?」
我說:「嗯。晚安。」
「什麼?」
我說:「謝謝妳的幫助。」
她點頭,「她們都有不在場證明,那晚是全年最容易拿到不在場證明的一個晚上,因為沒有人自己過除夕夜。」
他說:「是的,長官。」
我說:「這些手法都是騙人的。」
「何以見得我會有意見?」
我在通道邊緣查看地面的狀況:那是像岩石一樣堅硬的地面,地上已經結霜了。我不會破壞現場,因為根本沒有腳印,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沿著衣物走到最後。最後我終於懂了為什麼他還沒跟我講完電話就已經吐了兩次——如果我在他這年紀,可能會吐個三次。
「我沒有要妳剖析犯罪,只是要妳很快地給點意見,這樣我才知道自己追查的方向是否正確。」
「就一個憲兵而言嗎?」
「兇手不見得是你們的學生。」
她終於點點頭,「我同意。你是個聰明人。」
她呆住了。
她說:「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看不出我們的課程和那件案子的關聯,沒有具體的跡象顯示出這一點。」
她說:「我不記得。」
「妳看到了?」
我看看她——沒戴手套還敢碰屍體,她真是強悍。也許大家都低估她,以為她只能待在教室裡。
「我說過了,只是需要妳的專業意見。」
「可能嗎?」
「妳現在教的是誰?」
「爾汶堡不是只有裝甲部隊,別忘了,那裡還有陸軍新訓營。以前都是要上課的人來找我們,現在換我們主動找他們。」
她頓了一下,然後點點頭,「不是。被選擇的是博德堡和岩溪鎮。有人覺得博德堡這個地方比較重要,這裡發生的事情比特調組總部發生的事情更為敏感。」
「我只想找人幫忙。」
「當然,整個課程的重點就是要打擊敵人對自己性向的信心。除了性向之外,還有生殖力、性能力以及各種能耐。不管何時何地,在整個歷史上,這都是最核心的戰術。這是一石二鳥的戰術:一方面擊潰敵人,另一方面靠比較為我軍建立信心。」
她說:「一小時後來我辦公室。」她走回桑瑪的悍馬車,桑瑪倒車後掉頭,往暗處加速開去。
她說:「沒有,最近沒有。有什麼問題嗎?」
我累了,打了個呵欠之後,我說:「就當作一般謀殺案來辦。我們連被害人是誰都還不知道,我想明天就會查出來。明天七點見,好嗎?」
她說:「他的性器官被切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