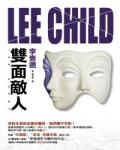9
我問他:「結果是怎麼一回事?」
他點頭後又換了坐姿,拉一拉褲管,看來很不舒服。「你有留下公車的票根嗎?」
「還有呢?」
我點點頭,問醫生:「死亡時間呢?」
起來後他走出辦公室,在他身後把門關上。我坐著看訪客椅上的塑膠坐墊又恢復原來的形狀。墊子動得很慢,當空氣又跑回墊子裡的時候,發出了嘶嘶的聲音。
桑瑪說:「我已經傳真出去了,今天就知道結果。」
我問:「可能是鐵鍬嗎?」
「誰在乎呢?」
「你覺得你是因為卡邦才被調來的嗎?」
他說:「而且我查過了,你出現在大門口的時候,是氣喘吁吁的。」
他說:「我不是同性戀。」
「可以猜猜看嗎?」
醫生說:「有可能,也許比輪胎扳手更為合理。總之我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型,你把東西帶過來,我會告訴你是不是。」
「那還用說。」
我說:「沒錯。」
「什麼樹林?」
「他可能是用跑的。」
我問他們:「還有別的嗎?有沒有什麼事會讓他遭到殺身之禍的?」
「上校,你來告訴我。」
我說:「嗯。」
「像是生活方式上的問題呢?」
「有可能。」
我說:「我不能保密,如果我能保密,也許我會。但是因為命案現場的種種跡象,讓人很難不產生聯想。」
他瞪著我說:「你在說什麼?」
「什麼?當然不是!」
「你覺得陸軍希望這件事傳開來嗎?希望大家都知道三角洲特遣隊裡面有一個違法的隊員在隊上待了四年?你瘋了嗎?」
「那麼,你一直到昨天十一點都不在基地裡嗎?」
「和別人起衝突呢?」
「是草莓還是覆盆子?」
威拉點頭說:「假設你有辦法找到這傢伙,你會對他做什麼?」
「不記得了,你問這個做什麼?」
他說:「我想你答應了,你沒那麼笨。」
醫生說:「那個液體是優格。」
他點頭說:「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個白癡,還是你故意這樣做。」
我說:「他被殺了。兇手跟動機都還不知道。」
「在哪裡?」
我不發一語。
他不發一語。
他說:「沒錯。」
我說:「偵查犯罪是我謀生的本事,我說他不是。」
他瞪著我,好一陣子都不發一語。
我問他:「你們有人不見了嗎?」
我說:「那根本就不是一個地點,只是個靠近車道的地方。」
但我錯了。
「還不算有。」
桑瑪在五分鐘內就出現了。我有一堆事情要跟她說,但是每件事都在她的意料之中。她調出一張基地裡面所有人員的清單,還有進出基地的紀錄,藉此進行初步的篩選。她已經派人去把卡邦的寢室封起來,我們隨時都可以過去搜索。她還安排我們去找他的指揮官,這樣我們對於他的個人生活與專業表現就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聽說他死得很慘。」
我說:「真的。」
我不發一語。「而你剛剛也同意,用兩個小時的時間殺人是綽綽有餘的,特別是九點到十一點之間的兩個小時,剛好也是你沒有辦法提出不在場證期的兩小時。」
「冷戰結束了,陸軍即將改變。現狀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所以每個軍種都必須繃緊神經,縮減員額,你知道一件事嗎?」
我不發一語。
他搖頭說:「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沒錯,也沒有與你為敵,我只是要整頓特調組。以後你會感謝我,你們每個人都會。這世界在改變,我可以看得到遠景。」
「我要下去找你。」他把電話掛斷後,我把話筒擺回話機上。
他問我:「你不希望什麼事曝光呢?」
「但是,如果兇手要誤導辦案方向,那必須以某些事實為根據,對吧?我的意思是,假設他知道他是個賭鬼,他們可能會在他嘴裡塞欠債還錢的紙片,或者在他身邊丟撲克牌。這樣我們才會覺得他被殺的原因是賭債。你懂嗎?如果沒有任何根據,誤導方向的策略就不會奏效。如果在五分鐘內就會被排除的事,根本就顯得很愚蠢,兇手也太不聰明了。」
我說:「我跟桑瑪中尉講話,只是一些客套話而已。」
威拉說:「我記得你哥,他以前是我的同事。」
「接著怎樣?」
他說:「卡邦自從當兵以後,十六年來只投訴過這麼一個案子,這我也查過了,像他這種傢伙,必須低調一點,但是整個特遣隊都會覺得這件事很不尋常。因為卡邦是第一次投訴,他們會覺得你們之前就發生了衝突,所以這是個人恩怨,難道他們會更喜歡你嗎?」
我沒有回話。
「好吧。應該說,他是個同性戀。」
他說:「待著別走。不要去別的地方,不要做任何事,不要打電話給任何人。我直接下令給你,那裡靜靜等著。 」
他又陷入了沉默,在椅子裡往左邊斜坐。
驗屍室中間有兩張凹下的鐵桌,桌子上方都架設著明亮的燈座,下方因為排水而不斷發出聲音。桌邊有許多用鍊子吊著的蔬果秤,是用來幫取出的器官秤重的,桌旁還有一些鐵製推車上面擺著空的玻璃罐,準備用來分裝器官,其他的推車則鋪有綠色帆布,上面擺著一排排刀鋸、鉗剪。這整個地方因為鋪有地鐵站常見的白色磁磚而閃閃發亮,裡面的空氣很冷,而且彌漫著一股福馬林的甜味。
他轉身回到桌子,完成死者腦部的檢驗,把頭蓋骨擺回去。為了把骨頭密合,他試了兩次,同時用海綿把裂縫漏出的東西擦掉,然後把他的臉擺回原位。他用手指把皮膚撥一撥、擠一擠,當他把手拿開時,我看到的那一張臉,就是之前我曾在脫衣舞酒吧和他說過話的那個特遣隊士官,只是此刻的他正茫然地直視著他上方的明亮燈光。
他說:「可能是軍用短刀。」
「我有老婆小孩。」
我不發一語。
我問他:
hetubook.com•com「他是在陳屍現場被殺的嗎?」「不是。」
他把頭別開,這樣讓我覺得更不尋常了。
那位上尉喃喃自語地說:「你說卡邦是個玻璃?」
那位士官說:「這樣會讓他的人生留下污點,太不應該了。他是個好人,也是個好軍人,同性戀不是一種罪。」
「有可能。但要看他到底為什麼被殺掉。」
我說:「我會拘留他。」我想應該還會派人在外面守著——我腦海裡浮現的是卡邦的特遣隊兄弟們,他們焦急地踱步的模樣,好像隨時準備開槍報仇。
大門裡面有一個鋪著磁磚的大廳,大廳的左、中、右三個方位各有一個入口:走左邊是到辦公室去,右邊是到冷藏室——所以我直接走右邊,準備去面對刀鋸齊下、屍水流瀉的驗屍場面。
我又坐了一個小時。沒去別的地方,也沒做任何事,也沒打電話給別人。我的中士又倒了更多咖啡給我喝。我跟她提到,請她幫我打電話給桑瑪中尉,要她來一趟。
「我不知道,必須要算一算他步行的距離。」
「基地裡的樹林。」
「那理由到底是什麼?」
我問他們:「有沒有任何可能的方向?」
醫生說:「鈍器造成的創傷,在頭部的後方,我想兇器是像輪胎扳手一樣的東西。其他所有的傷都是死後造成的,只是錦上添花。」
所以跟他一起出去的,是他認識而且信任的人。我想像當時的場景,他很輕鬆地在和人聊天,也許跟他在脫衣舞酒吧時一樣,露出那種微笑。也許他帶著攻擊他的人去某處,完全沒有戒心。接著我想像那個人從大衣裡面拿出了輪胎扳手或者鐵鍬,一出手就把他打得腦袋開花。然後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必須要下三次重手才能把他打死,完全在他意料之外。而且像卡邦這種傢伙,很少會這樣被殺個措手不及。
我說:「在嘴裡發現的嗎?」
我說:「有人殺了他。」
「什麼事?」
「用調查的方式。」
其中一個比較老的士官小聲地反問我:「例如什麼事?」
我沒有回話,他對我眨眼睛。
他又說了一次:「天啊!誰幹的?」
我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有可能。」
我說:「還不知道。」
我說:「你必須直接對我下令,一字一句講清楚。」
「先把地點講好。」
醫生說:「很難確定,可能是昨晚九點或十點,但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他說:「有採到指紋。」
我說:「我很抱歉。」
他說:「好,等一下再說這件事。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看過屍體?」
罐子旁邊擺著一小疊立可拍照片,一共有四張,拍的都是致命的傷口。第一張照片拍的是屍體被發規時的樣子,那傢伙的頭髮又長又髒,全身是血,我沒有辦法辨認出許多細節。第二張是泥土與血漬都已經被清埋掉了。第三張則是頭髮已經被剪掉。第四張裡面,頭髮則已經完全被剃刀剃掉了。
他說:「幫幫陸軍,同時也幫幫你自己。」
「我很確定他們的指揮官不想調查,相信我。你可以把這句話當作《聖經》裡面出來的。」
「那跟什麼有關?」
「死因呢?」
我說:「本來我不想講的。」
我說:「這件事跟逮捕無關。」
「不管你是不是,我都不在意。」
我說:「好。」過去十五年來,軍用短刀的生產數量是以百萬為單位的,可能只有獎章的生產數量能夠相提並論。
他說:「我並不認為人是你殺的,就算是你也不會做那麼扯的事。不過,如果是你,那又怎樣?陸軍的這些玻璃就應該被殺光,他們都是謊話連篇的傢伙。你唯一的錯,只是因為他投訴你而已。」
那傢伙說:「你知道為什麼。」
我說:「你在浪費時間,而且你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因為如果你要與我為敵,一定會吃不了兜著走。」
「他是同性戀嗎?」
他從口袋裡面拿出一張投訴書的副本,在桌上打開攤平後推到我面前。投訴書上面有序號,還有日期、地點與時間。日期是一月二日,地點是博德堡憲兵指揮官的辦公室,時間是〇八四五,接著是兩段經過宣誓的口供。我大概看了一下,語氣非常重,而且很正式:我親眼目睹了一位目前正在服役、名字叫做李奇的憲兵少校用腳去踹一位老百姓的右膝。接著,李奇少校又馬上用額頭去攻擊另一位平民的臉部。據我所知,兩位平民並未先行挑釁,而且他們也來不及自衛反擊。後面有卡邦的親筆簽名,下面有打字的數字,那數字我之前曾在卡邦的檔案裡看過。我抬頭看牆上那一具慢慢往前走、完全不出聲的時鐘,腦袋浮現卡邦從酒吧慢慢走到停車場上的模樣,他看了我一下,然後就去找那一群靠在車子旁邊的軍人,拿起啤酒瓶喝酒。我又低頭看著桌上,打開一個抽屜,把那張紙放進去。
「因為我可能需要知道。為了證明我自己沒有犯錯。」
「你知道的時候,會告訴我們嗎?」
「什麼時候會查出是誰?」
「真的很慘。」
我說:「謀殺案。」
「我在十一點回到這裡。」
威拉繼續說:「根據規定,如果投訴與軍紀有關,特遣隊指揮官辦公室也會有一份副本。其他地方也都存有副本,所以消息很快就會走漏了,接著他們會來找我問問題。我該怎麼跟他們說?我可以說你絕對不是嫌犯,也可以說你一定有嫌疑,但因為某種技術上的問題,我不能辦你。我可以想像那些充滿正義感的特遣隊員會怎麼解決這種不公平的問題。」
我說:「幹得好。」
他點頭說:「你的手下由你去交代,我去找那個心戰中校跟醫生。」
我們不發一語地坐了一陣子,兩人只是隔著桌子瞪著對方。我穩和圖書穩地坐著,威拉還是不斷換坐姿,拉褲管。我把手伸到他看不見的地方緊握著,想像著往他胸口正中央打下去,一拳就了結了他這個大爛人的生命。為什麼不呢?我可以寫一份報告,說他也是受訓時死掉,誰叫他一天到晚都在做更換坐姿的訓練。他滑倒後,胸骨撞到了桌角。
他搖頭說:「我們對這件事沒什麼意見,不管他是誰殺的,兇手肯定不會是我們的人,那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會做這種事,可是除了特遣隊以外,沒有人知道,所以這不會是他的死因。」
「這個叫做卡邦的傢伙是個同性戀,他是個超級大玻璃。像這種都是菁英的單位裡居然有個變態?在這個節骨眼,你想陸軍會希望大家知道這件事嗎?你應該在報告裡面寫他是訓練時出意外死的,交代過去就好了。」
經過整整四個小時後,威拉終於現身了。他一到我辦公室外面,我就聽到他的聲音。我很確定我的中士沒有問他要不要咖啡,她的直覺也挺厲害的。他打開我的房門後直接進來,他沒有看我,只是隨手把門關上,轉身後找了一張訪客椅坐下。他一坐下就開始不斷變換坐姿,他的褲管也像是熱到會燒傷他的皮膚,害他不停拉來拉去。
那位上尉並未回答,只是趨前打開一個抽屜,拿出一個檔案交給我。就跟其他我見過的特遣隊檔案一樣,為了讓大家使用,檔案被徹底地消毒,裡面只有兩頁資料。第一頁上面有姓名、階級與編號等個人資料,還有一個叫做克里斯多夫.卡邦的傢伙的個人簡歷。他是個已經服役十六年的老兵,還沒結婚。他曾當過四年步兵、待過四年空降師、四年遊騎兵連隊,在特遣隊的D隊也已經四年了。他是個比我大五歲的上士,資料裡面沒有提到他有參加過哪些戰役,也沒說他得過哪些獎章。
「既然他不是因此而被殺掉,我想說出來之後,也許你能夠保密。」
我點點頭,不發一語。
他說:「我們成交了嗎?」
我點頭說:「根據我的判斷,沒錯。」
他點頭說:「所以,如果那個玻璃在九點或十點被殺,兇手有可能在十一點才簽名進入基地?」
我說:「一定有人知道,否則,兇手就是你們隊裡的人。」
我走到清晨室外的寒冷空氣中。
「你們想知道嗎?」
我想到門口穿著靴子的衛兵,他們幫我做了進入基地的紀錄。
我說:「我猜,應該是為了讓某件事像石沉大海一樣。」
「什麼時候?」
「如果是經過訓練的人,有可能躲過巡邏人員。」
他把這件事講清楚後就走了,我得繼續遵守威拉的命令。
「他們的士官希望進行調查。」
威拉說:「事實上,我想,對於靠這種事謀生的人來講,事實應該很重要。這個基地的範圍幾乎有十萬英畝,鐵絲圍籬是在一九四三年就架起來的,這些是所謂的事實,不管是我還是你,要發現這些事實並不難。難道你沒有想過,並不是每個進出基地大門的人都必須走大門?你有沒有想過,在紀錄上不在這裡的人,有可能從圍籬潛入基地?」
「昨晚九點或十點。」
「一定是。」
「哪裡?」
所以決定因素終究是動機,也就是我最開始思考的地方:他到底是為什麼被殺的?
上尉問我:「他在哪裡?出了什麼事?」
我把檔案擺在辦公桌的抽屜裡,打電話到憲兵指揮官辦公室,詢問是不是有人擅離職守或者不假外出。死者可能已經被列為失蹤軍人,直接從清單裡面查出他是誰就可以。但是沒有這樣的紀錄,一切都很正常,基地裡的每一個軍人都還活蹦亂跳地活著。
「如此一來,他在基地大門時有可能已經喘不過氣了。」
我把時間用來想事情。命案現場沒有兇器,鑑識人員也沒採集到有意義的線索。兇手沒有在樹枝上留下衣服上的線,地上沒有足印,卡邦的指甲裡面也沒有留下兇手的皮膚。這些都很容易解釋,兇器被帶走了,之所以沒有留下衣服的線,是因為兇手穿的是戰鬥服——多虧了陸軍總部的精心研發,我們的戰鬥服是不會裂開留下衣線的。幫陸軍代工的美國各家紡織廠都必須經過很嚴格的品質考驗,因為陸軍使用的斜紋布與府綢都必須耐穿耐扯。地上整個結霜了,硬到不會留下腳印,北卡羅萊納州可能有一個月的時間都會結厚厚的霜,現在時間才過一半。而且他完全沒有料到對方會下手,所以沒有時間轉身回應,也沒辦法出手去抓或去踢兇手。
「你覺得那些士官們會相信這套說詞嗎?你是個特調組調查員,這種事對你來講就像家常便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查出投訴者的名字。」
我說:「從人事資料跟進出門的紀錄就可以查出來。」
「一樣。」
「昨晚九點或十點。 」
他說:「但你的動機是什麼?我想你跟卡邦不熟,你們的社交圈並沒有交集。至少我希望是這樣。」
那傢伙頓了一下。「我想這點我並不清楚。」
「天啊!為什麼?」
「樹林的外圍。」
他們一致說:「沒有。」
「你在開玩笑吧?」
那位士官搖頭說:「這樣一來,大家就只會記得他是個同性戀。」
「所以這過去十六年來他都沒跟人在一起過?」
「據我所知並沒有。」
我說:「別跟我說。要打電話報喪的人是你。」
「我還得證明嗎?」
他問我:「死亡時間是什麼時候?」
「那真正的動機又是什麼?」
我點點頭,「這的確不是他被殺的原因。我們姑且說他在死前是同性戀好了,但是他在部隊裡待了十六年,他撐過了七〇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還有整個八〇年代,但為什麼一直到現在才出事?時代已經在改變,狀況對他愈來愈有利,他也和*圖*書愈來愈擅長掩藏這個身分,還會跟好友們一起去脫衣舞酒吧。沒理由一直到現在才突然發生這種事。如果要出事,早在四年前、八年前、十二年前或者十六年前就出事了。每當他到了一個新單位,認識了新的同袍,都可能會出問題。」
「那麼,輪胎扳手呢?」
威拉說:「有趣的是,投訴你的人剛好就是這位克里斯多夫.卡邦上士。」
我說:「我以為屍體會腫得更厲害,還有更多瘀傷。」
「那麼,原本只要四小時車程的一段路,你卻花了六小時。中間有兩個小時的差距,你解釋是因為你坐車比較慢。」
我還是說:「不太可能。那這樣要怎麼跟卡邦上士相約見面呢?」
「昨晚九點或十點。」
「六個小時?我才四個小時就到了。」
他微笑說:「記得是誰載你到基地的嗎?」
「有人在午夜發現了卡邦的屍體。」
「陸軍討厭改變。」
我回想著卡邦在我腦海裡留下的畫面,他在距離脫衣表演舞台六呎的地方閒逛著,不管誰在台上用手肘、膝蓋匍匐前進、屁股翹得高高、用乳|頭摩擦著舞台,他都跟她們保持六呎的距離,手裡拿著一瓶啤酒,臉上笑得很開心。一個同性戀的男人在酒吧裡廝混似乎是很奇怪。但接著我腦海裡想起他那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樣,還有他揮手叫那個一頭深褐髮的妓|女離開時的尷尬神情。
我說:「大概像個小男孩一樣,要找我比比看誰能尿比較遠。像這種大案子,他想要下來親自指揮辦案。他要提醒我,我還是歸他管。」
我開著悍馬車,經過諾頓中校的心戰學校,打算前往三角洲特遣隊駐紮的營舍。在陸軍把所有惡棍都集中關在堪薩斯城的李文沃斯堡之前,這裡也曾是個監獄,所以它是一個可以獨立運作的營舍,原有的鐵絲網以及圍牆非常適合它現在的用途。在營舍旁邊有一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巨大飛機機棚,機棚看來好像是從附近的基地被拖過來,拼回原狀後被用來存放特遣隊的貨架、卡車、裝甲悍馬車,也許還包括一、兩架能夠進行快速反應任務的直升機。
「有線索嗎?」
我說:「我想應該沒有。」
我說:「我需要白紙黑字的命令。」
「然後呢?」
我不發一語。
「啊?」
「可以把人名給我嗎?」
他說:「你這幼稚的傢伙。」
「那他的動機是為了讓某件事情永遠不會曝光。」
我點點頭。不管卡邦是不是同性戀,他總是這世界上最恐怖的部隊的一分子,他的兄弟將會挺身為他報仇。有片刻的時間我覺得自己很羨慕卡邦——如果有天晚上我在樹林裡面被人幹掉了,我很懷疑會有這樣三個硬漢在隔天早上八點闖進人家的辦公室,摩拳擦掌的要幫我報仇。接著我又看一下他們三個,心想:只要我把他的名字洩漏出去,這個兇手就死定了。
醫生說:「一點也沒有,兇手突然下毒手,他一點反擊掙扎的機會也沒有。」
「在兇手殺人後又繞到大門簽名進入基地,必須花多久時間?」
「那你會用什麼方式找出兇手呢?」
我點頭說:「兇手不是老百姓。」
「為什麼?」
「人名?我還以為他因為惹事而被你逮捕了。」
我的電話響了,結果打來的是威拉上校,坐在岩溪鎮蓋伯上校辦公室裡面那個大混球。
「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我點點頭。當我們講話時,桑瑪中尉可能已經埋首在那一疊疊清單裡面了。
太平間是在艾森豪當總統時就已經蓋好的,到目前還是很適合這種用途。在軍中,驗屍的程序沒那麼繁瑣,跟民間大不相同。我們都知道昨晚那個死者不是踩到香蕉皮而滑倒摔死的,所以我並不在意什麼是他的致命傷。我想要知道的是他大概的死亡時間,還有身分。
我不發一語。
「陸軍應該要改變了。」
威拉說:「那我們來猜猜看好了。假設兇手會因為殺人而獲得利益,你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說:「我也是,妳也是。難道妳是同性戀嗎?」
「為了掩飾真正的動機嗎?」
我又說了一次:「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他說:「少校,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他問我:「你在哪裡?」
我說:「通常來講,殺了卡邦上士是為了阻止他在未來採取某種行動,或者為了掩飾卡邦曾經參與或者知情的一樁犯罪。」
「換言之,就是要讓他閉嘴。」
威拉說:「猜猜看。要多久時間?」
第二張資料裡面則有十枚用墨水採的指紋,還有一張在酒吧裡面我跟他講話,現在陳屍於太平間鐵桌上那傢伙的照片。
年輕的那一個士官說:「去查一查遊騎兵。看有誰請調到三角洲特遣隊,但是特訓時沒有過關,但還想證明自己真的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我說:「嗯。」接著我環顧四周,那枝折斷的樹枝就被擺在一輛推車上,旁邊擺著一個罐子,裡面裝著死者的陰|莖與睪丸。
我說:「一定有人知道,但我想這不是他真正的死因。只是有人想讓他看來像是因為這樣而被殺,也許至少我們可以澄清這一點。」
我把檔案收起來,夾在我的手臂下面。
他說:「看著我的嘴唇。我說:不要調查。寫一份狀況報告,說他在訓練時出意外死掉就好。說是夜間操練、跑步、做體操,什麼都好。說他失足絆倒摔到頭,這樣就可以結案了。這是我的直接命令。」
「那麼,你的嫌犯是在那一段時間裡待在基地的任何人?」
「什麼時候?」
「在辦公室裡。不然我會在哪裡接電話?」
「不管是什麼,一定都會讓陸軍很尷尬。就像克拉瑪死在汽車旅館的問題一樣。」
「但是除了特遣隊的人之外,沒有人知道。」
我說:「只有這
和-圖-書兩種可能性,一定是其中之一。他在外面有交往的對象嗎?」
我說:「跟我哥通電話。」
「例如什麼事?」
「接著呢?」
「你覺得這跟他的死有關?」
那兩個老士官裡面的一個說:「卡邦的事是真的嗎?」
「為什麼?」
威拉說:「現在我應該怎麼做?我該去他們隊上暗示我不能動你嗎?還是我們來個交易,我幫你擋住那些特遣隊的傢伙,你就乖乖聽我的話?」
她說:「病理醫生說這顯然是打壓同性戀的行為。」
他說:「大家都說同性戀會破壞凝聚力,他們應該來看看我們特遣隊的操練情形,看看卡邦的表現怎樣。」
我又點點頭。九點或十點是有道理的——天色已經完全變暗,距離要被發現之前會有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壞人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把他騙出來,等到屍體被發現,他已經逃得遠遠的。
我不發一語。
我又說了第三次:「不太可能。」
「沒有頭緒。」
「有自衛造成的傷口嗎?」
我要桑瑪擬好適當的通知與報告,並且轉寄各單位,然後我就回辦公室了。謠言傳得很快,回辦公室後我發現有三個特遣隊士官正等著問我話。他們都是典型的特遣隊人員:短小精幹、有點不修邊幅,一看就知道是狠角色。其中兩個的年紀比另一個還大。年輕那個留了落腮鬍,一身黝黑的皮膚看來好像剛剛從天氣很熱的地區回來。他們都在我的辦公室外面踱步,我那個有小男嬰的中士跟他們在一起,我猜她現在不再固定值晚班。她看著他們的表情好像這三個人時而踱步,踱到不耐煩就開始騷擾她。和他們比起來,她算是很客氣,幾乎可以算是溫柔。我帶著他們走進我的辦公室,關門後在我的桌子坐下,任由他們站在我桌前。
我不想講得太深入,只是說:「任何你覺得可能的事。」
病理醫師又點點頭,不發一語。
「希望很快。」
「我沒有測試口味。」
「我想是你開車,我換了兩趟公車,最後還搭便車。」
「一、兩個小時吧。」
我說:「我必須以憲兵身分問你們幾個問題。」接著我問的都是一般性的問題:卡邦有跟人結怨嗎?曾跟人發生爭執嗎?有被威脅嗎?跟人打過架嗎?這三個傢伙一直搖頭,每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句。
我站在桑瑪旁邊,看到死者趴在桌上,他們已經把天靈蓋切除,還從前額把他臉部肌膚拉了下來,那張人臉被反蓋著,好像一件毛毯被鋪在床上一樣,擺在他的下巴上。他的頰骨跟眼球都暴露在外面,病理醫師正仔細解剖著他的大腦,好像在找什麼,之前他已經用鋸子鋸開頭顱,像蓋子一樣把頭蓋骨取下。
我說:「不太可能。如此一來,那個人必須在一片漆黑中步行超過兩英里,那一定會被整夜都在外面巡邏的人員發現。」
威拉說:「我們都知道特遣隊很照顧自己人,他們就像祕密幫會一樣。所以,他們現在會怎麼做?他們的人在投訴一個臭屁的憲兵少校後被人打死,這個憲兵少校必須要保住自己的飯碗,而且憲兵少校也沒辦法清楚交代,在他們的人死掉那一晚,他去哪些地方。」
我問他:「誰是跟他最近的親人?」
她問我:「威拉又怎麼了?」
「真的嗎?」
「所以可能有人與那個同性戀碰面,殺了他之後從鐵絲圍籬逃出去,然後再繞回大門,簽名進入基地。」
「所以囉。」
「你想要讓陸軍蒙羞嗎?」
我說:「你這根本是欲加之罪,之前你沒有說出投訴的人是誰,昨天我也還沒看到這張投訴書,連他的名字都還不知道。」
「那又怎樣?」
那位上尉說:「那就閉上你的臭嘴。長官!」
右邊那張空著的桌子很乾淨,左邊那張的桌旁則站滿了人,人群中有病理醫師和一位助理,一個辦事員則在旁邊做筆記。桑瑪也在那裡,她站在後面觀察著,他們也許已經進行到一半了。所有的工具都用上了,有些玻璃罐已經裝了器官,排水管正嘈雜地排水,從人群的縫隙中我可以看到死者的雙腿。他的腿已經被清洗過了,透過上面的燈光照射,那雙腿看來泛著藍光,本來沾在腿上的污土與血漬都已經不見。
桑瑪說:「感覺起來像是一個人幹的。」
「做什麼?」
「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我聳聳肩,「我昨天兩點才下飛機,直到五點都在你那裡。」
他又說了第三句:「天啊!」
「沒有,不曾有過。」
「為什麼?」
他說:「下一個要討論的是,你說那個屁精的死因跟性向無關。你的證據是什麼?」
「交代什麼?」
「你可以證明嗎?」
我說:「犯罪現場被布置得太過火了。」
我又點點頭:「博德堡似乎是個很尷尬的地方。」
我問:「卡邦在這裡有與人結怨嗎?」
醫生說:「用刀的人是一個右撇子。」
「那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絕對不可能。」
他說:「你犯了錯。」
我不發一語。
「因為你一定會查出來,我希望你有心理準備,不想讓你感到訝異。」
「回來後呢?」
「幾個人攻擊他?」
病理醫師點點頭,「或者就在附近。沒有跡象顯示其他可能性。」
我點頭說:「他有提到。」
「他是同性戀,而且有人知道。但這不是他被殺的原因。」
「那麼,可以用地圖來約定。」
我說:「你已經鑄成大錯了,因為你與我為敵。」
我待著沒去別的地方,也沒做任何事,也沒打電話給別人。我的中士拿了一杯咖啡給我,我沒拒絕。威拉上校可沒命令我就算渴死也不能喝咖啡。
一小時後我聽到辦公室外面傳來聲音,那位年輕的特遣隊士官又回來了,只有他一個人——就是留著落腮鬍、皮膚黝黑的那一個。我要他坐下和-圖-書,想著剛剛我聽到的命令:不要去別的地方,不要做任何事、不要打電話給任何人。我想跟人講話也算是做一件事,因此等於違反了「不要做任何事」的命令。但話說回來,嚴格來講,呼吸也等於是一件事、新陳代謝也是一件事,就連長頭髮、長鬍子、長指甲、體重下滑等等也都算是一件事,所以我不可能「不要做任何事」。所以我認為這一部分的命令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沒有,他是個好軍人。」
我不發一語,他對著我微笑。
「你覺得?」
接著他們就離開了,我坐著咀嚼他們最後丟出的那句話。想要證明自己比較厲害的遊騎兵?我很懷疑,這是不可能的。三角洲特遣隊的士官不會跟自己不認識的人出去,而且還被人打爆了頭。他們受到長時間的嚴格訓練,目的就是要確保自己不會有這種下場。如果一個遊騎兵和卡邦單挑,那躺在樹下的一定不是卡邦。如果遊騎兵有兩個,我們會發現兩具遊騎兵的屍體,至少卡邦身上會出現反抗的傷痕,不會那麼容易就被撂倒。
「卡邦未婚。」
威拉說:「醒醒吧,少校!合作一點,蓋伯走了,現在我說了算。」
「我不知道,所以才要調查。」
病理醫師瞥我一眼,「我已經說過了,所有的傷口都是他死後才刻意弄出來的,當時他已經沒有心跳與血壓,血液停止流動,所以沒有浮腫與瘀傷。而且也沒流很多血,所有的血都只是因為重力而流出來的。如果他被割傷時還沒死,血會流得到處都是。」
我帶著卡邦的檔案回到太平間,帶著桑瑪一起去軍官俱樂部吃早餐。我們獨自坐在角落,跟任何人都離得遠遠的。我點了蛋、培根與吐司,桑瑪則是一邊吃著燕麥粥和水果,一邊看著檔案。我喝咖啡,桑瑪喝茶。
「陸軍總是最不稱頭的,你看空軍有那些華麗的飛機,海軍有潛水艇跟航空母艦,海軍陸戰隊則是所向無敵。而我們呢?所謂陸軍,就是要在泥巴裡打滾。我們是最下面的一層,李奇。陸軍是最無聊的,華府的觀點就是這樣。」
他說:「我要知道你昨天做的每一件事,你要親口告訴我。」
所以我把早餐跳過去,先看了犯罪現場的報告。報告厚厚一疊,但卻沒有任何有用的資訊。裡面只是把現場撿到的制服與衣物列出來,仔細描述它們。也描述了屍體,紀錄時間與溫度,用成千上萬的文字來說明那幾十張拍立得照片。
那位士官說:「我覺得卡邦是個同性戀。」
「你大老遠下來問我問題?」
「你問過,我也回答了。」
「他不是因為性向而被殺的。」
「然後呢?」
「啊?你之前沒說他的死跟性犯罪有關。」
「我不是魔術師,猜不出來。致命傷大概都是同一個人下手的,看不出是不是有其他人站著旁觀。」
「科學家的任務不是猜測。」
「那你為什麼要跟我說呢?」
我說:「我能為你效勞嗎?」
我不發一語。
我不發一語。
「用的是哪一種刀子?」
「這是一個封閉的基地。」
「你說犯罪偵查是你謀生的差事。」
「沒什麼然後,只是認為我應該要告訴你。」
他說:「我想你已經知道答案了,否則你來這裡做什麼?」
「啊?」
我不發一語。
「那不是真的。」
「還有別人知道嗎?」
「真的嗎?」
所以我們沒有具體的資訊。但我們的優勢是:嫌犯都在基地裡,逃也逃不掉。這是個封閉的基地,而且不管在什麼時候,陸軍都很擅長把人的行蹤紀錄下來。我們可以從一疊一疊的紀錄開始,從最簡單的兩個選項開始篩選每個名字:可能,不可能。然後我們可以逐一查核每個可能的人選,根據全世界每個警探辦案的三個通則來追查:手段、動機與機會。手段跟機會沒有什麼意義:根據定義,除非一個人有機會殺人,否則是不會被列為嫌犯的。任何一個有辦法在陸軍服役的人,體能都足以用輪胎扳手或者鐵鍬來攻擊沒有戒心的受害者。這可能是成為一個嫌犯的最基本要件。
「名字呢?」
那位上尉頓了一下,吐出一口氣。「我想他媽媽還在,不知道住在哪裡。我會通知你的。」
我趨前一步,更仔細地看一下,發現屍體很乾淨。灰白的屍首透著一點粉紅色,我隱約聞得到香皂的味道,還有血跟其他有機物的濃厚味道。他的鼠蹊部已經爛得失去了原形,手臂與肩膀的刀傷則是非常明顯,深可見肌肉與骨頭。冷冷的傷口的邊緣呈現藍色的外觀。刀鋒劃過他左上臂的一個刺青——圖案是一隻抓著卷軸的老鷹,卷軸上寫著「母親」兩字。整體而言,這傢伙的死狀甚慘,不過比我之前所想像的已經好太多。
我說:「我同意。」
「那妳猜呢?」
我不發一語。
隔天早上七點零一分,我在博德堡的太平間試著開始調查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睡了三個小時,沒有吃早餐。進行軍事犯罪調查時,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鐵則,大部分都必須靠本能來隨機應變。但有一條確定的規則是:來到陸軍的太平間進行驗屍工作之前,絕對不能吃東西。
「這傢伙常被逮捕嗎?」
「交代說我們要把這件事寫成訓練出意外。他們會懂的,沒人受傷害、沒人犯錯,也不用調查。」
營舍裡面那扇門的哨兵讓我進去,我直接前往人事參謀的辦公室。當時是早上七點半,營舍裡已經燈火通明,到處有人忙來忙去——這透露出一種不尋常的味道。人事參謀坐在桌邊,他是個上尉,在特遣隊這個什麼都顛倒的世界裡,士官才是明星,軍官只能待在家裡做家事。
「他錯了。」
我說:「我的手下。還有一個我曾經向她徵詢意見的中校心戰講師,再加上一個病理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