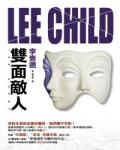18
「我猜是瓦索吧。」
賽門中校與我們說晚安後慢慢走開,桑瑪把椅子往後推,我看見身材嬌小的她在椅子裡動來動去。史溫往前坐,把手肘擺在桌上。
接著它們出現了,最前面一輛坦克從迷霧中穿出,很快向我們馳騁而來,有點顫抖,但大致還算平穩,引擎發出轟隆聲響,後面接著一台又一台坦克。它們排成一排縱隊,氣勢像來自地獄的「無敵艦隊」一樣驚人又壯觀。艾伯朗姆斯坦克就像鯊魚一樣,經過不斷演化,臻至完美。沒人會懷疑它具有「叢林之王」的地位,這地球上還沒有其他任何坦克可以損壞它,因為包覆著它的裝甲是由兩片軋鋼構成,中間的材質是貧鈾製成,裝甲密實,無法穿透。戰場上的子彈、火箭或者移動的裝置,只要撞上它都會彈回來,但它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它可以在非常遠的地方停住不動,看著敵人的子彈或飛彈因為推進力耗盡而在它面前掉下。接著它把炮管轉向,一秒鐘內就可以對攻擊它的敵人還以顏色,炮彈飛到一哩半以外。這是種無人能敵的優勢。
賽門說:「他是他們那個小團體的一分子,這是確定的。但你也知道那些將官是怎樣的角色,就算他們需要別人幫忙也不會承認。所以他們不重用他,他只是幫忙跑腿開車,但是當問題來時,他們會徵詢他的意見。」
他們的悍馬車從我跟桑瑪之間開走後,我們倆又在路中間站在一起。空氣裡彌漫著柴油與渦輪機廢氣的味道。履帶通過後,水泥地面出現一道道新的刮痕。
賽門說:「或者我們可以拿中東當例子。我們都知道伊拉克想奪回科威特,假如他們真的發動攻擊呢?長期來講,我們容易贏,因為大沙漠對坦克來講差不多等於歐洲的大草原,差別只在那裡的溫度較熱、風沙較大。我們的戰爭計畫應該會奏效,但我們的坦克真的能夠跑到那麼遠的地方嗎?我們只能讓步兵在那裡撐六個月,等坦克過來,但是誰說伊拉克人不會在兩星期內就用坦克輾斃他們?」
「什麼時候?」
「我也是。」
那位駕駛說:「馬歇爾不在這裡。」
為了搞清楚馬歇爾到底在什麼時間離開十二軍團,我們在三個辦公室間走來走去,最後來到瓦索將軍位於二樓的辦公室,他自己不在,跟我們講話的是個上尉,他似乎是個文書連隊的連長。他說:「馬歇爾少校在兩三洞洞搭乘民航機,從法蘭克福飛往杜勒斯機場。七小時後再從華盛頓機場飛到洛杉磯國際機場,旅行憑證是我簽發的。」
她說:「每個人都有事想隱瞞。」
他說:「我連屁股都快凍僵了,我只帶了太平洋區的制服跟裝備,三天後十二軍團才幫我找到一件冬天的制服。」
「他們本來覺得沒有風險,因為他們不想殺人,而且他們以為克拉瑪夫人不在家,而是在醫院。而且他們覺得史派瑞維爾與綠谷鎮的小竊案是不會上華府報紙版面的。」
「你是誰?」
桑瑪問我:「來過嗎?」
距起飛三十分鐘前運輸官來幫我們帶路,我們從飛機跑道上走向飛機,登上機腹。中段機艙有很多貨物,我們坐在旁邊裝有網子的摺椅上,背靠著機身內壁——整體而言,我還是比較喜歡法航的頭等艙,因為運輸隊沒有空姐,也不給免費咖啡。
她說:「那份議程跟昨天賽門中校講的事情,可說是一體兩面。賽門妄想步兵能變得更重要,裝甲部隊的優勢受挫,我想克拉瑪對這些也都一清二楚。二星中將可不是白混的,所以本來元旦要在爾汶堡召開的那場會議,就是要想出反制對策。我認為他們想反抗,他們不想放棄既得利益。」
「我真的不確定。」
我一點也不意外。史溫又矮又壯,他的身材幾乎就像個立方體。在軍需官的登記冊裡,也許只有他自己一人有這種尺寸。
我說:「去打包行李,準備三天份的東西。」
「他在班機起飛前三小時就從這裡離開了。」
他說:「很熟。」
我說:「他們殺了克拉瑪夫人,所以要逃。」
我點點頭。我想一月期間,法蘭克福應該是在七點破曉,所以我提醒自己,應該要在六點起床。
我們帶著行李去來訪軍官寢室,找到我們的房間。我的房間踉克拉瑪那間汽車旅館房間看來差不多,不過比較乾淨。裡面的格局跟一般美國汽車旅館一樣,當時可能是由某間連鎖旅館標下這個政府合約,然後他們把所有設備跟家具都空運過來,從洗手槽到毛巾架、馬桶等等都是。
我們在高空飛了將近八小時才開始逐漸下降,因為沒有對講機,不像民航機上機長會對旅吝發布即時訊息讓人安心。你只能從引擎聲的改變與機身往下傾斜來判斷,而且耳中會出現一種尖銳的感覺。我身邊到處有人站起來伸懶腰,桑瑪直挺挺地把背靠在一個裝彈藥的木板條箱上,像隻貓一樣摩擦著背部。她的狀況看起來很好——因為她的頭髮短到不會變亂,而且她有明亮的雙眼,充滿決心,好像她知道這趙旅程不是航向毀滅,就是光榮之旅。她決定服從我,不去想會是哪一種結果。
我邊搖頭邊走路,「我待過海德堡的步兵基地,待了很多次。」
我問他:「你們的來訪軍官寢室還有空房嗎?」
桑瑪瞥了我一眼,我聳聳肩。
史溫說:「沒聽過,我才來沒多久。」
「他們的反撲力量會很強大,因為他們的事業成敗就在此一擊。你要小心點。」
我問他:「所以未來會怎樣?」
桑瑪搖搖頭。
「如果他們的心臟真的那麼強,昨晚怎麼逃了?」
「確認了嗎?」
我說:「我也是。」
那傢伙打了通電話,確認後指著一道寬闊的樓梯,上二樓就可以找到他了。
我露出微笑。說這種話跟他自己是個步兵有關,這是面子問題。但其中也有幾分屬實。
「啊?」
她猶豫不決。
我說:「妳也是,不只是我。」
「攻擊是最佳的防守。」
賽門說:「好。我們就當是巴爾幹半島好了,假設在南斯拉夫,那裡一定是第一個開戰的地方,現在他們只是在等誰先開槍。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繼續等待,還是一片寧靜。
「我想是蘇聯T80坦克的油耗量,藉此算出他們的訓練模式。」
我說:「嗯。」
「我不確定。」
「什麼時候?」
「有問題嗎?」
我又點點頭。每年要花幾千億養的百萬大軍,要找出誰幫誰撐腰,嘿,這就是陸軍,你能怎樣呢?
「在附近嗎?」
我說:「我要去睡了。」
我和圖書說:「史溫的辦公室在六點十分打電話詢問馬歇爾在哪裡,五十分鐘後他就接獲來自爾汶堡的命令,又過一小時他就離開基地。」
那傢伙說:「柏林,他想弄些柏林圍牆的紀念品。」
「我們該找出是誰幫他撐腰,開始發送黑函。」
「晚上八點嗎?」
「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我問他:「你認識馬歇爾少校嗎?」
她離開後我打電話問我的中士,誰是這基地憲兵裡的第三號人物,我走後應該頂替我代理指揮官職缺的。稍後她跟我講了一個我認識的名字,是之前我在軍官俱樂部看過,那位手臂受傷的女上尉。我寫了張字條,向她解釋我必須離開三天,這段時間由她頂替我,然後拿起電話,打給喬伊。我說:「我要去德國一趟。」
「為什麼?」
他說:「兩年了。」聽到他的回答真讓我高興。因為我需要一些背景,而就像我不了解博德堡,史溫也不了解這裡。接著我才了解,賽門並不是恰巧來跟我們一起吃晚餐,一定是史溫想到我的需要,於是我還沒開口他就幫我做了這個安排。史溫就是這種人。
史溫說:「特調組的嗎?」
我說:「如果不去一趟,是不對的。但我不應該讓她覺得我比你關心她,那也不對。所以你也該去一趟。」
他說:「馬歇爾不在基地裡,他到鄉下進行夜間演練了,明天回來。」
他對我微笑,又聳聳肩,好像又跟我說了一次「你想怎樣呢?」然後他拿起話筒,我聽見他要他的中士找到馬歇爾,告訴他,如果方便的話,我想跟他見面。我們等待回電時,我四處看看,發現史溫的辦公室看起來也是暫借的,跟我在北卡那間一樣。兩間辦公室裡掛著同款電子鐘,沒有秒針,也不會發出滴答聲,已經六點十分了。
賽門又說一次:「好。假設我們先派八十二和一〇一空降師的人過去好了。一星期內我們就可以調三個輕武裝的營過去。但過去後呢?我們只能抵擋一陣而已,還是要等重裝部隊過去,這就是第一個問題。一輛艾伯朗姆斯坦克七十噸重,不能用空運的,一定要先用火車載,再用船運。而且最棒的是,你不能只是把坦克帶過去,坦克每多一噸,就要多載四噸燃料,還有其他裝備。這些吃油的怪獸每跑半哩,就要吃掉一加侖的油。而且還需要替換用的引擎,彈藥,還有大量維修人員。坦克部隊所需要的補給隊伍,可能長達一哩,所以移動坦克就像移動一座鐵山一樣。如果你希望坦克部隊可以多到扭轉戰局,最少需要六個月的準備工作,而且必須日以繼夜地工作。」
「我不確定。」
「這裡有事嗎?」
「議程的內容呢?」
在還沒看見十二軍團的艾伯朗姆斯坦克隊伍之前,遠遠就聽到它們的聲音了,那聲響穿越迷霧,直撲我們而來。我們聽見履帶轉動的聲音,以及渦輪機嘎嘎作響。每當齒輪帶動履帶上的金屬片,砰然一聲往前轉動時,我們都聽見吱嘎換檔的聲音,隱約從腳底感覺到震動。我們還聽到在坦克的重壓下,沙礫與石頭都被絞碎了。
「空降部隊根本撐不了六個月。」
「既然我要去德國,回程時當然要去巴黎一趟。你也知道,情況使然。」
桑瑪說:「我們在犯法。」
我說:「你自己可以看。」我穿著昨晚換上的戰鬥裝,衣領上有橡樹葉,衣服上印有「李奇」這個名字。
我們在法蘭克福機場裡位處偏僻的軍事禁區,大家搭著地勤人員的接駁巴士到民用航空站,接下來就各自到不同單位報到。有些人已經有專車在等著接他們,但我們沒有,我們跟一群老百姓一樣等著搭計程車。輪到我們的時候,我們給司機一張旅行優惠憑證,要他載我們到東邊的十二軍團基地。他非常高興能有這筆交易:他可以拿著憑證到任何美軍基地換錢,而且回程時他一定可以在十二軍團基地載到幾個想去城裡待一晚的美軍。絕對不會拿不到錢,也不用空車開回法蘭克福。他跟過去四十五年來的許多德國人一樣,都是靠美軍為生。他的計程車是輛賓士。
「昨晚吧。」
史溫說:「或者巴爾幹半島。等到蘇聯真正垮台,那地方是個已經煮了四十五年的壓力鍋,鍋蓋一掀開馬上出事。」
他說:「上去右轉。」
我說:「我覺得不是這樣。沒有人坐計程車去五金行偷東西,還入侵別人的房子。」
他說:「我們的新老闆嗎?我收到備忘錄了,沒見過面。但這裡有些傢伙認識他。他本來是搞軍事情報的,業務跟裝甲兵有關。」
我說:「夜班火車。如果只是去玩,誰會搭夜班火車?」
「基本上,他是個有計畫有策略的人。他會做長期盤算,克拉瑪將軍似乎很喜歡他,總是把他帶在身邊,任命他成為自己的情報官。」
我說:「我覺得很有道理。不過,他們兩人看起來都不像特別高大或強壯。」
賽門做了個表情,然後說:「應該會。他跟他們一樣,都是熱愛裝甲部隊的狂熱分子。但是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克拉瑪死的時機對他們來講真是不利。」
我說:「世界正在改變。」
縱隊裡一共有二十輛坦克,他們開進大門後,噪音與震動在我們身後消失,不久後,一輛偵查車從迷霧中穿出,開向我們——那是一輛執行「打帶跑」戰術的悍馬車,車上的配備是TOW2反坦克導彈發射器。裡面有兩個傢伙,我檔在它的路上,舉手把它擋下。我不認識馬歇爾,而且也只看過他一次,當時他開著那輛停在博德堡總部大樓外的水星尊爵,我看到他坐在昏暗的車內。儘管如此,我還是很確定這兩個傢伙都不是馬歇爾,因為我記得他很高大,而且皮膚黝黑,這兩個傢伙都很矮小,可說是較典型的裝甲兵,因為艾伯朗姆斯坦克裡面最欠缺的東西之一就是空間。
我聳聳肩。我希望喬伊在這裡,這種跟地緣政治學有關的問題他最在行。
「本來要參加,但計畫改了。」
她看著我,說:「他們在隱瞞些什麼?」
飛到高空時機身內壁變得很冷,所以我們都把手肘撐在膝上向前靠著。飛機裡吵到令人無法交談,我瞪著裝載在機上的坦克彈藥,直到視線開始模糊,我又睡著了。這種睡姿並不舒服,但身為陸軍的一員,必須學會在任何地方睡覺。我醒來大概十次,一路上大多睡睡醒醒,因為飛機引擎與螺旋槳氣流實在太吵。不過相對來講這趟旅程還算安穩,總算還能保有床上睡hetubook.com.com眠的六成效果。
「你的派令也是蓋伯簽發的嗎?」
我說:「這是桑瑪中尉。」
賽門說:「那還用說。而且他們都是我的人,我很擔心。輕武裝空降部隊如果遇到外國的裝甲兵,有可能不被屠殺嗎?這六個月會讓我非常非常焦慮。這還不是最糟的。等到重裝部隊終於抵達,下船後卻只跑了兩條街就被困住了。因為路不夠寬,橋不夠堅固,他們根本出不了港區。他們會被困在泥濘中,遠遠看著步兵被人宰殺。」
他說:「好,一路順風。」
桑瑪說:「動用空中武力,派攻擊直升機過去。」
我搖搖頭,說:「現在我們要去巴黎,我必須見我媽一面。」
我說:「我見過他了,不是什麼好東西。」
「為什麼不?」
我說:「要花更多錢。」
稍後飛機就往西迎風起飛了,接著我們用一百八十哩的慢速在華府上空飛著,然後加速往東飛行,我可以感覺到速度的變化。機上沒有窗戶,但我知道我們在城市上空,喬伊就在我下方某處沉睡著。
「你跟馬歇爾那種人講過這番話嗎?」
她不發一語。
有一陣子我們只聊一般性話題。我們拿薪水與津貼的事發發牢騷,也聊我們都認識的人,還有巴拿馬的「正義之師」行動。賽門中校說他前兩天去了一趟柏林,帶了一小塊柏林圍牆的水泥碎片回來。他說打算把東西保存在一根塑膠管裡面,像傳家之寶一樣代代相傳。
「我同意,而且他們應該就在此地此刻反咬我們,這裡是他們的地盤。我真的搞不清楚。」
「口頭的。」
「他們的參謀?絕不可能。」
我問他:「來很久了嗎?」
她把手放在桌上,手心向下,吸了口氣。「其中一部分被我看出來了。」
上面講的都不是。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聲音是坦克進入柏油路時履帶發出的尖銳聲響以及嘩啦噹吠的巨響。這種聲音在在華沙、鹿特丹、史達林洛勒以及柏林都出現過,然後出現在布達佩斯,布拉格、漢城與西貢等地。這是種很殘暴的聲音,讓人害怕,而且它代表壓倒性的武力優勢,具有一種孤傲、不人性而冷漠的特質。坦克用這種聲音告訴世人:它是無人能擋的,所有人在它面前都顯得脆弱無力。接下來坦克一邊的履帶停止,另一邊繼續轉動,此刻它轉而向你推進,一邊咆哮尖叫。這是二十世紀真正的聲音。
我說:「給我們兩間房間,過一夜。」
「他們可能直接從飯店大廳搭計程車或租台禮車,而且我們絕對追查不到,因為除夕夜是整年生意最忙碌的一天。」
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聲音是什麼?這問題的答案可能見仁見智。有人說是飛機引擎緩慢的嗡鳴聲——想像一下一九四〇年代一架戰鬥機在蔚藍天空中爬升發出的聲音。或者是一架噴射機從頭上低空快速呼嘯掠過,撼動地面。也可能是直升機發出唔噗、唔噗、唔噗的聲響。其他還有滿載的七四七班機從地面轟隆轟隆起飛,以及炸彈落在城市裡的猛烈轟炸聲。這些聲音都有資格成為二十世紀特有的噪音,是先前歷史上「前所未聽」的。有些狂熱的樂觀主義者可能會說是披頭四的歌聲,——在台下聽眾的尖叫聲中,四個人耶、耶、耶的合唱聲漸漸漸消逝。我自己會投這種聲音一 票,但實際上歌聲與尖叫聲卻不是二十世紀特有的,因為自從有人類以來,音樂與慾望也伴隨著出現,它們不是一年後才有的。
我刮了鬍子後又沖澡,穿上乾淨的戰鬥裝,距離跟史溫見面還有五分鐘時去敲桑瑪的房門。打開門後發現她看來也是乾淨又清爽,從外面看進去,發現她的房間跟我的也一樣,不過裡面聞起來已經有女性的氣味,空氣裡彌漫著某種淡香水的味道。
「有人會說,因為我們花了大筆經費才贏了這場戰爭。」 賽門點頭說:「說得沒錯。但接下來會怎樣?」
我說:「我必須跟他談談。」
我說:「真大膽,不是嗎?居然坐計程車去做這種事。」
他搖頭說:「暫時被派到別處去了。」
上尉說:「沒有,他坐火車去的。」
他的電話響起,他聽了一分鐘後把話筒放下。
我說:「我要找馬歇爾少校。」
我問他:「這基地裡毒品很多嗎?」
接著我們聽到部隊回來的聲音。
他說:「你想來點嗎?」
到安德魯空軍基地的路上我都在睡,抵達時午夜已經過很久了。我們把車停在專用停車場,用兩張旅行憑證換了兩個運輸大隊C130運輸機上的位置,凌晨三點要飛往法蘭克福。我們在一個有日光燈的大廳等飛機,裡面有塑膠椅墊長凳,還有滿滿的候機旅客。軍隊調動是最常見的事,所以不管白天或晚上,任何時刻都有人要趕往某處。這種候機大廳從來不是交談的地方,那天也不例外,我們只是渾身僵硬地坐在那裡,又累又不舒服。
進去後我發現桌子後面坐著一個叫史溫的傢伙。我跟他挺熟的,上次我們見面是三個月前在菲律賓,當時他剛調到那裡,本來要派駐一年。
那條路穿越門口,轉向後往東延伸,接著偏北進入一片霧中,朝著蘇俄方向繼續下去。這是條又寬又直的大路,路面由強化水泥鋪成,因為坦克履帶的摩擦,所以街邊石上面到處是刻痕,常有楔形水泥石塊從上面掉下,因為坦克是非常難駕馭的。
我說:「我同意,但這樣是不夠的。國防部馬上就會不斷收到這種狗屁文件,堆起來有一個人高,裡面有贊成的意見、有反對的意見,還有什麼如果啦、但是啦、然而啦,大家看了都無聊死了。但在那份議程裡面有個截然不同的東西,這讓他們拚了老命也要把議程拿回來。到底是什麼?」
「誰會接掌他的指揮權?」
史溫從桌子另一邊伸出手來跟桑瑪握手。
桑瑪說:「整年裡面就這天最難確定不在場證明。」
「這太冒險了。華府的計程車司機可能跟大家一樣都會看報,而且因為塞車時間多,看的報紙可能更多。如果司機看到綠谷鎮兇案的報導,他會想起那兩個乘客。」
「根據經驗法則。要追就要追那個被他們支開的,因為他們覺得他最容易出錯。」
我說:「幸會。」接著我跟史溫點點頭,好像在跟他道謝。我們用結霜的大杯子飲用冰冷的美國啤酒,喝完才去用餐室。史溫先訂了位,服務人員帶我們在角落一張桌子坐下。我坐在一個讓我可以立刻看到整個房間的座位,我沒看到任何認識的人,瓦索與和圖書庫莫都不在。
我說:「選擇在妳,不管妳加入或退出,我都不逼妳。」
破曉之際,我已經跟桑瑪一起站在十二軍團基地的東路大門,當時是早上六點五十,手裡各拿著一杯咖啡。地上已經結凍了,四處一片霧濛濛的。當時天色灰暗,景色一片粉綠。這裡的地勢很低,最多只有波浪似的起伏,跟很多歐洲地區都一樣,完全沒有讓人驚歎的感覺。到處都是整齊的矮樹叢,冬天時整個大地都在休眠,寒冷的空氣中散發出一種植物的味道,四下一片寂靜。
「為什麼?」
「因為英國國防部臨時通知他要開會。」
「那現在由他指揮一一〇特調組?」
「瓦索將軍也副署了他的旅行憑證嗎?」
史溫說:「派空降部隊過去。」
「我不知道。」
「庫莫上校呢?」
第十二軍團的基地原本是納粹時代最典型的軍事設施。某位納粹的工業鉅子在原野裡蓋了個上千畝的工廠,那已經是一九三〇年代的舊事了。它的特色是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辦公大樓,後方有一排排的鐵皮屋,綿延數百公尺。這些鐵皮屋曾因轟炸而數度化為碎片,又被重建,而辦公大樓則只有部分受損。一九四五年,有些疲憊不堪的美國裝甲部隊在此駐紮,為了賺取食物,法蘭克福許多戴著頭巾、身穿褪色洋裝的瘦弱婦女來到這裡,用鏟子與小推車把碎石弄成一堆一堆。接下來美軍工兵部隊把辦公大樓修好,派推土機把碎石清掉,然後五角大廈不斷撒鈔票重建這地方。到了一九五三年,這裡已經是個模範基地了,到處矗立著磚造建築,刷上閃亮的白漆,基地周圍還有堅固的圍籬。到處都是旗杆、崗哨與警衛室,還有許多食堂,以及診所和福利社各一。基地裡遍布營舍、工作站與倉庫。最重要的是,這一千畝的平地上,到了一九五三年時已經停滿了美軍坦克。它們排得井然有序,全都朝東停放,隨時可以呼嘯而出,在東西德邊界的「富達平原」 (the Fulda Gap )上與敵人決戰。
我說:「有可能。也許我們該查查計程車。」
「勝利背後隱藏的是苦果,一切都將改變,你該聽聽這些傢伙的論調。他們很悲觀。」
我說:「我知道,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點點頭。回想克拉克警探在幾天前說的:我派手下沿街訪查,但沒有任何發現。當天有些車子進進出出。
我點點頭,「我知道。很怪吧?」
我說:「現狀無法持續下去了,有人這樣跟我講。」
郊區街道又整齊又乾淨,樸素的商店上方都是些公寓,櫥窗裡陳列了許多閃閃發亮的商品。路標都是白底黑字,用的是種古老字體,很難看懂。路上到處都有較小的美軍基地路標,沒隔多久就會看到一個,我們沿著十二軍團的路標往前進,距它愈來愈近。我們離開建築物群聚的地區,穿越兩、三公里的農田,感覺起來就像壕溝,或者一塊隔離的區域。我們眼前東邊的天空已經暗了下來。
「妳來告訴我。」
菜單一點也不特別,裡面的菜色是世上任何一個軍官俱樂部都看得到的。軍官俱樂部不是為了向你介紹當地菜餚而存在的,它是為了讓你有家鄉的感覺,所以裡面的一切都代表陸軍對於美國文化的詮釋。我們可以選擇魚或牛排,魚可能來自歐洲,但牛排一定是從大西洋對岸空運過來的。一定是家鄉有牧場的政客向國防部施壓,完成了這筆令人滿意的交易。
桑瑪跟我在我住處外的人行道上會合,我們把行李拿到雪佛蘭車上,我們都穿著戰鬥裝,因為如果我們運氣好,可以在安德魯空軍基地搭乘夜間運輸機。要搭夜間的民航機,時間已經來不及了,而且我們不想再等一夜,搭乘隔天最早的班機。我們上車後在門口簽名,離開基地,開車的當然還是桑瑪。她用力加速,然後車速稍減,一路用很平順的節奏開車,時速只比一般車輛多十哩。
他聳聳肩,那姿勢就像是說:嘿,這就是陸軍。你想怎樣呢?
桑瑪說:「還有瓦索就去了倫敦,庫莫則是匆匆搭上去柏林的火車。」
「我沒概念。而且我也不在乎,未來是步兵的天下。」
我說:「不遠。」
大家都不發一語。
上尉點點頭,「是,他也簽了名。」
我們上樓後右轉走進一道長廊,兩邊都有辦公室,辦公室的門都是硬木門板,上面裝有條紋窗戶。我們找到要去的那間,進去後發現外面的辦公室有位士官,這辦公室跟我在博德堡的那間沒什麼兩樣:壁漆、地板、家具、溫度與氣味都一樣。連咖啡機也是陸軍配發的,裡面的咖啡也相同。這位士官跟我以前共事過的許多士官一樣溫和、有效率而且冷靜,看起來他隨時都準備好可以自己搞定這辦公室裡的大小事,而且搞不好已經有過這種經驗。他坐在桌子後面,當我們進門時抬頭看我們,花了點時間了解我們的身分與來意。
我們抵達法蘭克福時,已是三十七年後的事了,當時天色暗到根本看不到什麼,但我知道基本上沒什麼是會改變的——唯一不同的是坦克的機種。幫我們贏得二次世界大戰的M4雪曼坦克車早就被換掉了,只在大門擺了兩部保養得非常好的樣本,肩並肩停在一起,像是精神象徵。兩輛坦克都一樣,一半已經登上一個經過造景設計的水泥斜坡,高舉炮管,尾部向下,就像它們還在奔馳一般,正在向上挺進。旁邊打的燈光頗具戲劇效果,車身的綠漆光澤亮麗,兩邊都有閃亮的白色星星,比原來的模樣更好看。他們後面有條長長的車道,兩邊的街邊石漆成白色,還有用泛光燈照射的辦公大樓,現在是基地總部。總部後面是坦克的車庫,裝甲師的主力MlA1艾伯朗姆斯坦克肩並肩停在一起,這些數以百計的坦克,光是一輛的造價就要四百萬美金。
我說:「我跟你一樣。」
桑瑪說:「還有,他們昨晚為什麼要逃?他們一定早就把克拉瑪那份議程,還有所有影本都毀掉了。他們可以睜眼說瞎話,先把你騙過去,甚至可以給你一份假的議程,直接告訴你這就是議程,你自己看看。」
「你在兩天後搭乘夜間班機。我會跟你在戴高樂國際機場會合,我們一起去看她。」
「他怎麼辦到的?」
她點頭說:「我還是覺得瓦索與庫莫殺了她。克拉瑪一死,發球權就交到他們手上,他知道自己有責任出面把所有會洩密的文件處理掉,所以克拉瑪夫人是間接受害者。」
駕駛是個上尉,www.hetubook.com.com坐在他身邊的也是個上尉。他們都穿著防火坦克裝,頭戴全罩式保暖帽以及有內建式對講機的鋼盔。那位乘客袖子的口袋上插滿了筆,兩邊大腿上都綁著寫字板,裡面都是打分數的紀錄。
我說:「但是她很厲害。」
「先追哪一個?」
「顯然是有攻有守。他們必須抨擊把部隊整合起來的構想,嘲笑輕型裝甲車,吹噓自己的專業有多了不起。」
他說:「完全正確。就像海軍一樣。當那些大型戰艦被航空母艦取代時,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及另一個時代的開始。艾伯朗姆坦克就等於大型戰艦,它們曾經舉足輕重,但已經過時了。它們能夠走的路,只有那些我們為坦克量身訂做的道路,方向也都是早就決定好的。」
「除了我跟我的猴子。」
「他離開的時候。」
甜點是蘋果派,接下來我們喝了咖啡,咖啡挺好喝的。我們從未來又跳回現實,開始聊些不關痛癢的話題。服務人員在我們身邊不發一語地走來走去——軍官俱樂部都是差不多的,只不過這個跟我前些晚上去的相隔四千哩遠。
「他們對未來有何想法?」
「所以他也是圈內人?我聽說克拉瑪、瓦索與庫莫被大家稱為鐵三角,但沒提到馬歇爾。」
「說出來會嚇死你。」
威拉絕對不可能核准我出國,所以我去了一趟憲兵指揮官的辦公室,從辦事員書桌上拿了一疊旅行優惠憑證,把它們帶回我的辦公室,然後在指揮官簽名處簽上我自己的名字,然後用很像蓋伯上校的筆跡在授權者的簽名處簽上里昂.蓋伯。
「現在克拉瑪死了,他是不是會跟著一起往上爬?或許他可以接庫莫的遺缺?」
我說:「但因為是長途車程,要花很多錢,司機也會因此記住。」
「什麼時候?」
「書面的嗎?」
她說:「現在呢?」
「據說是。」
我們從計程車下車,越過人行道,走向大門警衛室。我出示特調組的徽章後,他們就放行了。這枚徽章可以讓我們通過任何美軍設下的檢查站,唯一的例外是五角大廈內部的警衛室。我們拿著行李,沿著車道走下去。
那位上尉點頭說:「八點整。」
賽門說:「希望如此。飛機跟直升機是很炫,但它們沒辦法自己打贏戰爭。歷史上沒這回事,以後也不會有。只有步兵能克敵制勝。」
「這我也不確定。」
賽門說:「不夠機動。下一場戰爭會在哪裡發生?」
最前頭那輛坦克從我們眼前通過,它長二十六呎、寬十一呎、重七十噸。它的引擎聲像打雷一樣,重量撼動地面,履帶在地面滑動時會發出吱嘎聲響,嘩啦噹啷。接著是第二輛、第三輛、第四輛、第五輛。噪音震耳欲聾,坦克的炮管時而上下跳動,時而左右搖動,空氣中彌漫著坦克排放的廢氣。
賽門說:「什麼世界?基本上這是克拉瑪的世界,從各方面來講都是。他是西點軍校五十二年班的,而且很多基地像這裡一樣,都是五十三年班的人在當家作主。過去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裡,他們可以說是世界的中心。這地方做了多少軍事建設?多到你難以想像。你知道誰在這個國家付出最多嗎?」
我安坐在椅子裡,看著路面路肩,還有沿路的商場集散地以及車流,我們往北開三十哩,經過克拉瑪投宿的那家汽車旅館,然後上了交流道,朝東開往九十五號公路,往北走後我們經過休息,一哩後經過克拉瑪的手提箱被棄置的地方。接著我闔上雙眼。
我說:「閒聊而已。」
史溫點頭說:「這裡的人說德國有些土耳其外勞可以幫人弄一點,我確定有個賣安非他命的傢伙也兼賣海洛因。」
我說:「這是披頭四的歌,他們的歌聲是二十世紀的聲音。」
「他什麼時候離開的?」
我說:「你的憲兵指揮官在嗎?」
「那他在哪裡?」
「顯然有人幫他撐腰。」
她說:「真的是這樣,他必須像以前的戰艦艦長一樣為自己打算。」
我說:「太棒了。」
我說:「走吧。」
「跟馬歇爾少校一起去機場的。」
史溫說:「跟我一起吃晚餐。我不習慣跟這些裝甲兵一起,剛好沒伴。一小時後在軍官俱樂部見面?」
悍馬車就在我面前停下,我繞到駕駛座窗邊,桑瑪則是輕鬆地站在乘客座窗邊。駕駛把他的窗戶搖下,瞪著我。
因為我住的來訪軍官寢室格局實在太常見,關上門後不到一分鐘,我就忘了自己身在何方。我把制服掛在衣櫃裡,洗澡後鑽進被窩。那被單的洗潔精味道一聞就知道是各地陸軍統一使用的。我想到在巴黎的我媽和在華府的喬伊。媽大概已經睡了,而不管喬伊的工作是什麼,應該還在工作。
「他去倫敦了。」
我說:「這就像庫斯克的坦克大戰,我們不能回頭了。」
「司機不會看到的。瓦索或庫莫其中之一或者他們倆可以走進那條巷子裡,五分鐘後把鐵鍬藏在大衣下走出來。去克拉瑪夫人她家也一樣,可以叫計程車在路上等他們,司機根本沒看到他們做了什麼。」
「誰?」
我說:「倫敦?」
那傢伙說:「什麼單位的?」
「馬歇爾,我想先抓他。」
我們全都再度坐下,降落前緊抓椅子旁的網子,輪子落地後,輪胎發出摩擦巨響,煞車_把機身拉住,上面放著貨物的托盤往前滑動,但是被帶子固定住,引擎關掉後飛機又滑動了好一陣子才停下來。機尾的活動舷梯放下後我們從後面看到薄暮的昏暗天色。當時是德國的下午五點,比美東時間早六小時,比世界標準時間(Zulu time )還要早一小時。我很餓,因為從前一天在史派瑞維爾吃了那個漢堡後就沒進食了。桑瑪和我站起身拿了行李就開始排隊下機,跟其他人一起從舷梯下去,到了飛機跑道上,發現天氣很冷,跟北卡差不多。
我問他:「你遇過一個叫威拉的傢伙嗎?」
我說:「難道你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到這裡的?」
我說:「我必須跟一個叫馬歇爾的傢伙見面。他是十二軍團的少校參謀。」
「爾汶堡有什麼緊急任務?」
「他有情報背景嗎?」
桑瑪說:「它們是機動的,所有坦克都一樣。」
我們很容易就找到了軍官俱樂部,這棟建築一樓有兩個側廳,它在其中一個裡面,占整個側廳的一半。裡面空間很大,天花板很高,灰泥牆面上還有裝飾雕紋。裡面有個大廳,有酒吧、還有用餐室,史溫在酒吧裡。他跟一個穿著軍禮服的中校在一起,軍禮服外套上有戰鬥步兵的徽章www.hetubook.com.com。在一個裝甲兵的基地裡能看到這種人是挺奇怪的。他的名牌上寫著:賽門。他自我介紹,我覺得他會跟我們一起吃晚餐。他說他是這裡的步兵聯絡人,裝甲兵也派了個人到海德堡的步兵基地去,做跟他一樣的事。
我說:「也許不是。關鍵在馬歇爾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如果是在史溫打電話以後,那一定有鬼。」
桑瑪跟我去軍官俱樂部吃早餐,坐的還是昨晚那張角落的桌子。我們靠牆並肩坐在一起,兩人都可以看到整個用餐室。
我說:「也許吧。但我還是覺得不太可能。妳可以算算從華府開車到那裡的時間,還要花十分鐘找到偷鐵鍬的那家五金行,他們只剩十分鐘可以決定。而且他們沒有車,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不是裝甲兵,也不是步兵。這個戰場是陸軍工兵部隊建造出來的。以前的雪曼坦克車有三十八噸重、九呎寬。現在我們已經升級到M1A1艾伯朗姆斯坦克,重量七十噸、十一呎寬。這四十年來,陸軍走過的每個地方,工兵部隊都曾留下痕跡,他們在西德境內鋪路造橋,拓寬的路數以百哩。我的天,路跟橋都是他們建的。如果你想讓一輛輛七十噸坦克車馳騁前往東邊的戰場,你最好確定那些路跟橋都撐得住。」
「有問題的是別人,我需要馬歇爾幫我查出一件案子是誰幹的。你認識他嗎?」
我點點頭,往後退開。
他說:「我想你是來找少校的。」 我點點頭,他拿起話筒,打電話到裡面那間辦公室。
「他們倆都比克拉瑪夫人要高要壯。而且你可以想像,在逼不得已的狀況下,他們激動之餘會做出什麼,所以鑑識結果會有點不準確。而且我們也不知道綠谷鎮的辦案人員到底有多厲害。他們可能派個家庭醫師來當驗屍官,這種人真的懂嗎?」
「為什麼?」
他頓了一下,說:「是這樣沒錯。」
我說:「我同意。」
這是趟橫越郊區的半小時路程,這裡的郊區有西德常見的景象,到處都是一大片遠在五〇年代就蓋好的淡蜂蜜色建築物,新社區蜿蜒聚集著,形成一道東西向的不規則曲線,這些區域都是把轟炸的殘骸剷平後重蓋的。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跟德國一樣在一場戰役中輸得那麼慘,我跟很多人一樣都看過那些一九四五年拍的照片:「慘敗」還不足以形容當時的情景,「世界末日」應該比較接近一點。全國各地變成廢墟一片,從建築物上到處都可看到證據——就連建築物下方也是。每次電話公司裝設線路時,總會挖出頭顱、骨骸、茶杯、彈殼以及生鏽的反坦克飛彈。每次建築物的地基在用汽鏟機開挖前,總有個教士在旁邊為亡靈祈福。我出生在柏林,跟一群美國人一起生活,居住地方圓數哩內都是毀滅後又重建的。我們以往總是說:是他們先惹我們的。
她有一陣子沒開口。
「這會列入紀錄嗎?」
桑瑪說:「這趟白來了。」
「那是幾點?」
「那我們要追他們嗎?」
我說:「這些旅行優惠憑證要到一、兩個月後才會被發現有問題,到時候不是威拉已經走人,就是我們捲舖蓋,我們有什麼損失呢?」
門前有寬闊的石板台階,這棟大樓看來就像美國某個小州的議會大樓,保持得乾乾淨淨。我們踏上台階進門,一進門就有個坐在桌前的士兵。他不是憲兵,只是個辦行政的十二軍團小兵,我們把識別證給他看。
我說:「他是計算油耗量的。」
我說:「難道他是跟瓦索、馬歇爾一起去機場的?」
他說:「我會先打電話過去,只要照著指標往前走就好。」
他說:「馬歇爾去加州了,去爾汶堡出緊急任務。」
「誰下的令?」
「瓦索將軍。」
不管我問十二軍團的人什麼問題,他們似乎總給我千篇一律的答案:「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我說:「中東?也許是伊朗或伊拉克。兩伊戰爭結束了,他們總得再找事做。」
我對自己說早上六點,然後閉上雙眼。
史溫告訴我:「馬歇爾黎明時會回來,他在進基地的第一列縱隊裡,應該坐在後面的偵查車裡。」
賽門說:「這些都要花掉數以十億計的經費。當然,他們知道哪些路跟橋是重要的。他們知道部隊要從哪裡開拔,要前往哪裡。他們跟戰爭領袖談過了,他們看過地圖後就開始用水泥與鋼筋幹活。只要我們有需要,他們會幫忙建造中繼站,還有堅固的燃料站、臨時彈藥庫、維修站,在部隊經過的預定路線上,會有數以百計的設施。所以說我們在這裡已經根深蒂固,簡直可以說挖個洞住在這裡。李奇,這整個國家就等於是冷戰的戰場。」
「沒有正式訓練,但他應該曾經輪調去做類似的工作。」
她說:「這真是沒道理,因為他們總不能逃一輩子,而且他們也知道遲早他們必須扭轉情勢,反咬我們一口。」
他說:「直接進去吧。」
史溫說:「沒什麼動靜。有個直升機部隊的傢伙去海德堡逛街,結果被撞死了。當然,還有克拉瑪的事,那倒是件大事。」
「範圍太大。」
她說:「除夕夜華府的計程車與禮車在三個州之間穿梭來回,大家去的地點五花八門,所以是有可能的。」
他說:「報告,還有。」
我說:「爾汶堡出了什麼狀況?」
「有人說他本來要參加夜間訓練。」
我露出淺淺的微笑,然後對他說:「馬歇爾什麼時候接到命令?」
賽門說:「就跟一九四一年的海軍一樣。一夜之間,戰艦變成歷史,航空母鑑成為新寵。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整合,我們必須了解陸軍的輕武器部隊太脆弱,重武器部隊卻又太緩慢。所以應該要摒棄輕兵種與重兵種之間的差別,我們必須組成有裝甲交通工具的快速反應部隊,但是交通工具必須在二十噸以下,而且要小到可以裝進C130運輸機的機腹裡。我們必須更快抵達戰場,用更聰明的方式作戰,不要再妄想跟敵人進行坦克大決戰。」接著換他露出微笑,「基本上我們該讓步兵當家做主。」
我問他:「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我說:「我在找海洛因,不過不是我要的。」
我說:「他們必須放棄的還真多。」
「七點鐘。」
「大概的時間就好。」
「心臟太強了。」
他指著走廊後面,那邊還有幾扇門可以走進這棟大樓。我看看手錶:剛好中午,不過手錶上顯示的還是美東時間。現在西德已是傍晚六點,天色已經變暗。我說:「我必須跟你們的憲兵執行官見面,他還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