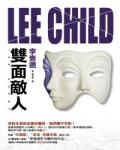22
「在這句話之前。」
我示意桑瑪完成其餘逮捕程序,因為根據《軍法統一法典》,必須跟他們聲明非常多事項,有許多建議與警告必須告知。桑瑪講得比我流利多了,聲音清晰,姿態專業,瓦索與庫莫兩人都沒反應,既不出言咆哮,也沒有託詞,也沒大發雷霆,以示清白。他們只是聽到一個問題就點一次頭,最後還沒被叫起立就自己站了起來。
她瞪著我說:「你能證明嗎?」
桑瑪說:「這案子的根據很薄弱,根本可以說很難成立。這些證據連間接證據都談不上,根本只是臆測之詞。」
我說:「布魯貝克的案子。」
我說:「那是卡邦的血。馬歇爾殺了他之後躲在後車廂裡。刀子找到了嗎?」
被關的可能是你。
他點頭說:「暗中盯著。」
我搖頭說:「我知道案發經過,行兇時間、方式、地點與動機都知道。但我卻沒辦法證明任何一件事,所以要靠他們的自白。」
法蘭茲說:「他們在五號就把車丟在那裡了。」
法蘭茲說:「墊子下有塊兵籍號碼牌,好像是鍊子斷了,其中一塊掉了下來。」
「我不知道。」
「然後呢?」
她的態度開始退卻。
「那當然。所以我們需要他們的自白。」
我說:「修女不就是要拯救世人嗎?」
「馬歇爾三十一歲了,從未結婚。」
「很多東西。有另外一個人的血,不過數量很少,本來應該在某人的夾克袖子或刀刃上,是經過摩擦後留下的。」
我說:「他在,這是妳想出來的。當時我們離開基地,正要去問克拉克警探有關鐵鍬的事,妳已經跟我說了。記得嗎?當時威拉打電話追蹤我,妳建議我一件事。」
我說:「瓦索將軍、庫莫上校,你們倆因為違反《軍法統一法典》而被逮捕了,罪名是與其他人共謀殺人。」
法蘭茲說:「沒有,不過後車廂裡到處是馬歇爾的指紋。」
「罪名呢?」
「好啦。」
「那我們先去吃早餐吧。」
她想了一下,搖搖頭,「那布魯貝克又是怎麼一回事?」
「能有多離譜?」
我們沿著走道慢慢往下前進,找到我們的位子,一個是靠窗的座位,另一個位於中間,走道上已經坐著一位老修女。我希望她有重聽的毛病,才不會聽到我們的話。她移動身軀,讓我們進去,我要桑瑪坐她旁邊,我坐窗邊。我扣上安全帶,沉默了一會兒,看看窗外的機場景致。泛光燈下一群人正在忙碌著,然後機身脫離登機門,開始滑行。跑道上沒有其他班機要起飛,不用排隊,所以我們兩分鐘內就飛了起來。
桑瑪又說了一次:「那布魯貝克又是怎麼回事?」
法蘭茲說:「他們找到那輛水星尊爵了。」
爾汶堡與十二軍基地的來訪軍官寢室就像是出自同一汽車旅館承包商的手筆,他們在一片沙地上蓋了一排排一模一樣的房舍,室內的一角是大家共用的設備,例如視聽室、桌球桌與交誼廳等等。法蘭茲帶我們從一道門走進去,然後就退到旁邊去。我們看到瓦索與庫莫正面對面坐在兩張皮革安樂椅上。當時我才想到我只跟他們見過一次面,就是他們來我博德堡辦公室裡找我那一次。儘管我最近花了那麼多心思在他們身上,看到他們的時間相形之下真是不成比例。
法蘭茲問我:「馬上要辦正事嗎?」
我說:「就是馬歇爾回德國述職之前。」
「馬歇爾?他連人都不在場。」
但是她搞砸了——她等了太久,修女打開包裝,開始用餐。
「和*圖*書我說,不要。」
桑瑪沉默了很久,她瞪著外面的夜空。
「這件事還是很離譜,我要說的每件事都是。」
我說:「還有呢?」
對於在飛機上只吃到半飽的人而言,美國的陸軍軍官俱樂部可以說是繼續用餐的好地方。這裡的自助餐檯好像有一哩長,菜單跟德國一樣,但是橘子汁與水果拼盤看起來比較道地,因為這裡是加州。我吃下可以餵飽一個步兵連的東西,桑瑪吃得比我更多,法蘭茲已經吃過了。我喝咖啡喝到肚子撐,然後雙手往前一推,把椅子推開桌邊,深深吸了口氣。
我向一個裝甲兵打聽了方向,開著法蘭茲的悍馬車去逮捕馬歇爾。他目前的任務是偵查,目前位置在一個廢棄炮靶附近的小屋裡。根據描述,那個炮靶是一輛廢棄不用的謝里丹坦克,車身應該已經嚴重破損。那一間小屋的狀況則比較好,就在那輛老舊坦克的附近。他叫我循著蓋好的車道往下開,才能避開尚未爆炸的炮彈以及沙漠裡的烏龜。如果我輾過炮彈,會被炸死。如果我輾過烏龜,會被內政部罵死。
我說:「他們可說是生手。哥倫比亞市的法醫一定會立刻查出屍斑以及排氣管在他身上造成的灼傷。他們很笨,但是運氣超好,因為法醫沒有立刻告知我們這件事。而且他們把布魯貝克的車丟在北邊,真是白癡。」
她說:「不要。」
我說:「那是一定的。他在裡面待了好幾個小時。」
「接下來瓦索、庫莫與馬歇爾開始到處尋找手提箱。相對於我們,他們的優勢在於他們知道該找的是個男人,不是女人。馬歇爾在二日飛回德國,翻遍克拉瑪的辦公室跟寢室。他找到有關卡邦的東西,也許是一本日記、一封信、一張照片,也可能是電話簿裡的一個名字或號碼。他在三日飛回來,他們計畫好後打電話給卡邦,威脅他,安排好隔夜跟他交換東西,用信件、照片或其他東西跟他交換手提箱。卡邦接受了這筆交易,而且他很樂意,因為他不想曝光,反正他已經把議程透露給布魯貝克了。他沒有損失,只有好處。也許他以前也有過這種經驗,而且不止一次,因為這可憐的傢伙在陸軍裡待了十六年。但這次他沒有成功,因為在交易時,他被馬歇爾幹掉了。」
我點點頭,一語不發。
我獨自離開主要營舍,當時剛好是早上九點半。我不想等桑瑪,瓦索與庫莫兩人的逮捕程序就夠她忙的了。我感覺我們好像走到了一趟旅程的盡頭,我只想趕快把這件事了結。我借了把手槍,但這決定還是不夠周密。
接著我收起笑臉,把臉別開。我想到在這一九九〇年的一月初,世界各地不斷有人丟了性命,卡邦、布魯貝克、克拉瑪夫人,當然還包括李奇夫人。
她嘆了一口氣,對我說:「好,等等。」
我搖頭說:「不是,在早餐來之前。」
我說:「卡邦的?」
「他們一定又累又緊張,壓力又大,畢竟開車開了那麼久。他們從阿靈頓公墓下來,後來又要把車開到史密斯菲爾丟掉,然後再去哥倫比亞市棄屍,最後直接北上杜勒斯機場。十八小時無法停歇的路程,這也難怪他們會犯錯。但如果你沒有跟威拉的命令唱反調,他們會就這樣逃過一劫。」
「他跟馬歇爾在一起。」
我屏住呼吸。
我說:「這是禮儀問題。他是個上校,如果要跟一位將軍和另一個上校講話,他會把瓦索安排在前座,庫莫坐在右後方,講話
m•hetubook.com.com時轉身就可以看到他們倆。馬歇爾不是他在意的人,所以也可以不用看到他。他只是個少校,誰需要他?」「妳建議我躲在後車廂裡,出門時就不會留下紀錄。桑瑪,馬歇爾就是這樣。開車的是庫莫,瓦索坐在乘客座上,而馬歇爾在後車廂。他們就是這樣通過大門的,然後他們把車遠遠停在軍官俱樂部另一邊。車尾朝後停,因為庫莫在下車前先把後車廂的開關按下。馬歇爾把後車廂車蓋拉下來,但他們還是需要掩護。所以瓦索與庫莫進去軍官俱樂部,開始編造鐵證般的不在場證明。同時馬歇爾在車裡等了幾乎兩小時,一直拉著後車蓋,直到四下無人他才出來把車開走。所以第一班巡邏的人記得看到車子,但第二班的人卻不記得,因為車子本來在那裡,後來被開走了。所以馬歇爾去某個指定的地點接卡邦,他們一起開車到樹林裡。卡邦拿著手提箱,馬歇爾打開後車廂,給了他一個信封或什麼的,他轉身到月光下查看。因為這是他們說好的交易,即使像卡邦這種那麼小心的特遣隊員也會這麼做,因為這跟他的飯碗有關。站在他後面的馬歇爾拿出鐵鍬來打他,不只是因為手提箱。反正他都已經拿到手提箱了,這筆交易是成功的,卡邦在事後也不能說什麼。馬歇爾會攻擊他,部分原因是因為生他的氣,嫉妒他跟克拉瑪在一起,所以殺了他。他拿回信封,拿走手提箱,把東西都丟進後車廂。接下來的部分我們都知道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然後他來的時候早就準備好那些誤導辦案方向的道具。他開車回營區,在路上把鐵鍬丟掉。他把車停在原來的車位,回到後車廂裡。瓦索與庫莫從軍官俱樂部出來後,就把車開走了。」
我們到華盛頓機場時,車子的汽油幾乎耗盡。我們把車擺在長期停車場,因為沒有接駁車,我們走了大約一哩路回到航廈。那是個無人的深夜,我們特別把一個辦事員從後面辦公室拖出來,我把最後兩張旅行憑證交給他,他幫我們訂了晨間第一班飛往洛杉磯國際機場的班機。我們要等很久才能上飛機。
他說:「有消息要告訴你。」
「你有派人盯他們嗎?」
「他們不會招的。」
「妳有辦法用其他方式解釋所有的事嗎?」
「事實並非如此,那裡幾乎是最不可能的地方。克拉瑪過去五年幾乎沒在那裡生活,他的幕僚一定知道,因為他們常跟他一起出差。然而他們還是很快就決定東西在那裡了,為什麼?」
「草莓,盒子上用來撕開封膜的凸出部分有馬歇爾的指紋,似乎他還吃了甜點。」
桑瑪說:「抱歉。」
天花板上的擴音器傳來聲音,宣布我們的班機已經可以登機,我們拿起行李,慢慢走進排隊的人群裡。外面天色還是一片漆黑,我算一算乘客人數,希望班機沒有滿座,所以會有些多餘的早餐,我餓得很。但看來狀況不妙,班機很滿,我猜對於住在華府的人,洛杉磯的天氣使它成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地方,隨便也可以找個理由去那裡開會。
桑瑪說:「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到了洛杉磯我才把眼睛睜開。飛機著陸後,輪胎觸地的巨響與摩擦聲把我吵醒。接下來飛機的反推力被啟動,又發出巨響,我在座位上往前滑動,直到被安全帶拉住。外面射進清晨的曙光,這裡黎明的天色似乎都是一片棕褐色。機長告訴我們加州現在是七點。過去兩天以來我們一直都hetubook•com•com搭乘飛機往西飛行,平均下來,本來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可是因為時差,我們的一天卻要二十八小時才過得完。我睡了一下,不覺得累,但還是很餓。
我們慢慢走下飛機,走到提領行李的地方,司機都是在那裡接人的。我四處看看,發現法蘭茲沒有派人過來,而是親自跑了一趟。看到他讓我很高興,感覺起來他會好好幫助我們。
「一定是預謀,他們已經計畫好了,他們開到遠遠的地方棄屍,馬歇爾在德國過夜時準備了海洛因跟裝滿子彈的槍。所以我們畢竟猜到兇手是同一人,只是搞錯對象。兇手殺了卡邦後直接坐車出了基地大門,然後又馬不停蹄地去殺了布魯貝克。」
我說:「好,幹活去。」
我說:「沒錯。他騙他們,說他跟老婆在一起,藉此掩飾他跟卡邦在一起的事實。但他為什麼有必要告訴他們呢?」
「什麼事?」
「不,在這之前。妳說的上一件事。」
我們回到法蘭茲的辦公室,他打電話給手下,他們說馬歇爾已經到靶場去了,但是瓦索與庫莫則是端坐在來訪軍官寢室營舍的康樂室裡面。法蘭茲開他的悍馬車載我們過去,下車後我們站在人行道上。那天陽光普照,溫暖的空氣中布滿灰塵。我可以聞到沙漠裡那些小型多刺植物的味道,彷彿也可以看到它們一點一滴地成長著。
他們倆抬頭看我。
他用力踩下柴油渦輪引擎,把車開離街邊石。爾汶堡就在巴斯托市北邊三十幾哩外的地方,因為要穿越晨間的車流,他載我們過去可能要花一小時的時間。我看到桑瑪看著法蘭茲開車的樣子,從眼中可看出她正在評估他的技術,如果換她來開,大概只要三十五分鐘就到了。
「你怎麼知道坐在他後面的是馬歇爾?」
我把他介紹給桑瑪。他們握手後他拿起她的行李,我想部分原因在於他這個人很客氣,但也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可以比較快坐上他的悍馬車。他把車停在紅線區,但警察站得遠遠的,通常他們對黑綠相間的迷彩悍馬車都會有這種反應。我們上車時我讓桑瑪坐在前面,這是個貼心的舉動,同時也因為我想在後座把身體伸展開來。飛機的座位實在太窄了。
「你要錄口供之前就得想清楚,因為根據實在太薄弱,被關的可能是你。你會因為騷擾的罪名被起訴。」
我說:「誰知道?未來會創造出奇怪的整合部隊,布魯貝克一定大受歡迎,因為他打的戰役本來就很奇怪。所以也許瓦索與庫莫謊稱要跟他結盟。無論如何,她們在四日深夜約好要見面,那一定是個布魯貝克知道的地點,他曾開車經過很多次,介於他打球的地方與博德堡之間。而且他一定覺得很安全,所以才會讓馬歇爾坐在他後面。」
法蘭茲說:「一個,在後車廂裡。」
桑瑪沉默了一會兒:「接下來呢?」
「克拉瑪夫人死了,這可不是我猜的。」
「他們是預謀殺人,或者是意外?」
「這都是你猜的。」
法蘭茲朝著方向盤點點頭,他說:「大門的進出紀錄是這樣顯示的。他則是搭運輸機回德國。為了加快鑑識速度,我們的人把車拖給聯邦調查局,還特別透過關係找人幫忙。調查局一開始不願意,後來進行了一整晚,興沖沖的要趕快完成工作。因為似乎跟他們的一個案子有關。」
「然後他們一直開車,又急躁又興奮,但當時他們已經知道克拉瑪夫人被馬歇爾殺掉了,所以他們也很緊張、很擔心。他們不知道馬歇爾身和圖書上有沒有血跡斑斑,所以不能隨便找個地方讓他出來。第一個安全的地方是往北開一小時的休息區,他們再度把車停在偏僻的地方,讓馬歇爾出來。馬歇爾把手提箱給他們,他們繼續往下開,花了一點時間把手提箱徹底找過一遍後,才把它丟出窗外。」
我說:「可惡。」
我們真可以算絕處逢生——也許在飛機上有得吃。我們拿著行李走到一扇二十呎寬窗戶旁的候機座椅,窗外只看得到一片漆黑。那些座位是有塑膠墊的長凳,為了不讓人在上面睡覺,每兩呎就設有把手。
「我說這是個根據很薄弱的案子。」
我點點頭,花一分鐘想這件事,然後閉上眼睛。
我看著她:「妳剛剛說什麼?」
最後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到爾汶堡,我總算見識到洛杉磯的高速公路有多塞。這個基地跟一般基地沒什麼兩樣,它是座忙碌而龐大的基地,坐落於莫哈維沙漠中。有一個以上的裝甲部隊會輪流駐紮在這裡,而且每當有其他部隊要來基地進行對抗演習時,這些部隊就要扮演地主隊的角色。每年春季,基地在訓練時的氣氛就是不一樣:因為天氣好,在陽光裡每個人樂於把昂貴的大型機器當作大型玩具來操練。
桑瑪說:「我們沒錢。」
我聽到耳邊傳來了動靜,有位空姐推著早餐出來了。她拿了一份給那位修女,桑瑪跟我各一份。早餐少得可憐:只有冷的果汁、熱火腿跟起司三明治,如此而已。我想等一下還會有咖啡,希望如此。三十秒內所有的東西都被我掃進肚子裡,桑瑪只比我慢一點點,但是那位修女根本沒碰餐盤。東西一直擺在她面前,我用手臂推一推桑瑪。
「克拉瑪沒有情婦,他是個同性戀。」
我說:「我餓了,先吃東西。」
我說:「兇手真是外行。還有呢?」
「因為那顯然是該去嘗試的第一個地方。」
「哪一種人?」
我有可能犯下騷擾他的罪。
我說:「他有開,但沒吃。」
「大部分都是一般證物。那輛車很髒亂,有很多頭髮與纖維,還有速食的包裝、汽水罐,類似的東西。」
他說:「那就已經是人類跨出的一大步了。」
「因為在面對某人的時候,他一定要給個說法。」
我說:「布魯貝克的部分我不確定。他跟這些案子有何關係?是他們打電話給他,還是他打給他們?除夕的午夜過了三十分鐘後,他就知道那份議程的內容了。像他那種先發制人的傢伙,或許他會先出手施壓。也有可能是瓦索與庫莫設想到最糟糕的狀況,他們認為像卡邦這種資深軍官,一定會先打電話給指揮官。所以我不確定誰先打給誰,也有可能他們互相聯絡、互相威脅,或許瓦索與庫莫提出雙方的合作方案,對大家都有好處。」
我說:「我覺得有些微的影響,我想克拉瑪夫人有跟馬歇爾講到話,她一定是在德國基地時就認識他了,也可能知道他跟她丈夫之間的關係。也許她還知道劈腿的事,可能她很生氣,還拿這件事來奚落馬歇爾。也許馬歇爾在盛怒之下,痛下毒手。可能就是因為這樣,他沒有馬上告訴瓦索與庫莫,因為她不只是因竊盜案而無辜受害,也是因為激烈爭論。所以我說,克拉瑪夫人不只是因為手提箱而被殺,我想也是因為她奚落了一個醋勁大發而且情緒失控的傢伙。」
我說:「連續殺人。受害者是克拉瑪夫人、卡邦與布魯貝克。」
我說:「一定要,帶著他們一路走到拘禁室,不要坐車。讓大家看著,他們是陸軍和-圖-書的恥辱。」
我說:「我知道,這點是不能證明什麼,現階段要證明什麼的確很難。」
但是他們倆都沒反應,兩人都不發一語,一副完全放棄的樣子。他們看起來很合作,好像知道這案子終於結束,不可避免的事正在發生。他們就像從一開始就預知這個時刻一定會來臨。我吐了口氣。人們對於壞消息的反應通常有許多不同階段:難過、悲傷、否定。但是這兩個傢伙顯然已經跳過這些階段,直接跳到最後一種反應:也就是,硬著頭皮,準備接受一切。
我微笑說:「我們本來都是用猜的,有了這些,也只算是些旁證。」
他們是長官。
她說:「這件事有何影響?」
「好,我們從克拉瑪夫人開始。馬歇爾為何去綠谷鎮?」
桑瑪說:「他們用兩個東西來誤導方向,一個是海洛因,另一個是把他開到南邊棄屍,不是北邊。」
他們都穿著那種改良過後,上面有人們所謂「巧克力條紋」的沙漠迷彩裝,兩件都是全新的。他們倆不管是穿沙漠迷彩裝或者叢林迷彩裝,就是沒有軍人該有的模樣,活像兩個扶輪社社員。瓦索的特徵還是禿頭,庫莫也還戴著眼鏡。
她又說了一次:「不要。」
「還有優格的盒子?」
「其他部分都是。」
她說:「這些都是推論。」
桑瑪問我:「要上手銬?」
她說:「現在就說吧。」
她說:「拜託,不可能。」
我說:「逮捕三個人。瓦索、庫莫與馬歇爾。」
我看到她好像在腦袋裡把講過的話倒帶似的,然後說:「我說,但如果你沒有跟威拉的命令唱反調,他們會就這樣逃過一劫。」
「那你把卡邦與布魯貝克的事說給我聽。」
「草莓或藍莓口味?」
「這很有可能嗎?」
法蘭茲說:「裡面還有個空信封,寄到駐紮在德國的十二軍團,收件人是克拉瑪將軍。蓋了一年前郵戳的航空郵件,沒有寄件人的地址。像是那種專門用來寄照片的信封,但裡面空無一物。」
他說:「這些算是好消息嗎?」
我點頭說:「克拉瑪是個劈腿的傢伙,馬歇爾是他主要的情侶,他們倆有固定關係。馬歇爾不是情報官,但克拉瑪還是任命他,為的就是想把他帶在身邊,他們是一對。但克拉瑪這傢伙用情不專,他在某處認識了卡邦,然後開始偶爾跟他約會。所以除夕夜那天他告訴馬歇爾,說他要跟老婆見面,馬歇爾信以為真,他就像富豪的情婦一樣。這就是為什麼馬歇爾要去綠谷鎮,他心裡料定克拉瑪一定是去了那裡,他以為他是世上唯一能確定這件事的人,於是他對瓦索與庫莫說出克拉瑪的行蹤,但是克拉瑪騙他。就像一般情侶一樣,有時也會騙對方。」
我說:「桑瑪,我們是陸軍。難道妳以為這是刺繡俱樂部嗎?」
我不發一語,他從後照鏡看著我。
我說:「我也遇過這種狀況,有辦法讓他們招的。」
「假設有個跟情婦在一起的富豪。如果他有一晚不能跟她在一起,就一定要給她一個說法。如果他告訴她,說他必須在老婆那邊待一晚,純粹為了露個臉,她就不能多說什麼。也許她不喜歡,但也要忍下來,因為這種事的確偶爾會發生。婚外情就是這樣。」
「因為克拉瑪跟他們說,他要回去那裡?」
我吸了口氣。
「還會有誰的?」
他點頭說:「後車廂的墊子上有布魯貝克的血跡跟腦漿。有人用紙巾擦過了,但是沒處理乾淨。」
「那又怎樣?」
我點點頭。
我說:「問她要不要吃。」
「我說,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