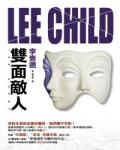23
「瓦索與庫莫有說什麼嗎?」
還是沒有爆炸。
但我知道他們不會停止射擊,因為它們看不到我們。因為煙塵四處彌漫,而且艾伯朗姆斯坦克的密閉式結構,視野本來就不好。坐在裡面往外看,就像拿著一個雜貨店購物袋,把底部截斷,透過底部的方形洞口往外看。我停下來揮手把塵土撥開,一邊咳嗽一邊往前看。我的悍馬車就在眼前了。
開了一哩後我把速度放慢,再過一哩後,我把車停下。馬歇爾還活著,但全身流血,陷入昏迷中。我那槍打得很準,他的身上有個被九毫米子彈穿透,一片血肉模糊的傷口,子彈穿過肩胛骨,而且小屋崩塌時的破瓦殘礫把他割得到處是傷。他的血跟塵土混在一起,好像紫紅色的糨糊。我把他安頓在座位上,用安全帶固定好,拿出急救箱後把繃帶貼在他肩頭兩側,幫他打了一針嗎啡。我按照戰場上的規則,用油性鉛筆在他額頭上寫了一個M字,代表已經打過嗎啡,這樣醫院裡的醫務兵才不會幫他過量施打。
我說:「不對勁。」
它平平整整地停在那邊。
鐵門外有一片地面因為是用來停車的,所以被鋪平成一條路。在建築術語裡面這種叫做「隨心所欲的小徑」。沒有一輛坦克往北邊朝我的方向開來,他們大多往西或往東走,一邊會有早上的陰影,一邊會有下午的陰影。所以我一直站在空地上,跟鐵門保持十碼距離。接下來我就一直站著不動:這是個好據點,它面對著小屋,我寧願站在那裡也不想直接衝進去,被人殺個措手不及。我可以在那裡等一整天,絕對沒問題。當時是一月,中午的太陽不會傷害我,我可以等到馬歇爾投降,或者餓死。可以確定的是,我最近吃的東西一定比他多。而且如果他決定跑出來開槍,我可以先射他,這一點也沒問題。
我可以聽見坦克正在逼近,距離不會超出八、九百碼。我可以聽見履帶運轉時的尖銳聲響以及嘩啦噹啷的巨響,它們迅速移動著。就像在野戰手冊裡面講的一樣,它們會散開來,顫動旋轉,馳騁在沙塵中。它們會形成一個機動的半圓形。炮管朝內,形狀就像是輪幅。
之前我跟他說,如果要自殺,我很樂意幫忙。但是他選擇讓坦克幫他這個忙。他看到我後就猜到我是誰,就像瓦索與庫莫每天都呆坐著,等待這件事的結局到來。終於,坐在悍馬車裡,穿越沙漠而來的我,就是要來幫他了結的。他想過後,做了決定,透過無線電對講機下令。
他要自殺。
人質談判專家稱這種問題為「壓力問題」,問這種問題的目的是要造成一種負面的心理影響,但是在法律上來講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他開槍打死我,他得在李文沃斯堡被關四百年。如果他不開槍,也得關個三百年。實際上並沒有差別,任何神智正常的人都不會理我。
他有武器嗎?
我說:「妳去就好了,我沒辦法去。」
「為什麼?」
我又聽到同樣的通訊內容:「再說一次?」然後是馬歇爾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也許是說「確認。」
我等待著。
我又叫他:「馬歇爾!」
坦克已經很靠近我。當它們輾過傾斜不平的地面,向上爬升時,我聽見引擎高高低低的運轉聲,履帶撞擊著側邊的車身。當它們的炮管轉動時,我聽見車上的液壓結構吱嘎作響。
「哪裡?」
他沒有回應,但是我聽到隱隱傳來一陣又低又短促的無線電通話雜訊。小屋屋頂沒有天線,所以他一定是帶著一具野戰無線電對講機。
我只跟他見過一面,而且不曾面對面看過他。當時是元旦,他在博德堡總部大樓外面,人坐在那輛水星尊爵的車裡,因為車窗上貼著綠色隔熱紙,裡面顯得非常暗。當時我估計他是個皮膚黝黑的大個子,這點從他的檔案資料獲得了確認。他現在看起來還是一樣:高大、魁梧、肌膚是橄欖色,一頭濃密的黑髮剪得很短。他穿著沙漠迷彩裝,弓著身體從牆上洞口看我。
我直接載他去基地的醫院,從護理站打電話給法蘭茲,要他派衛兵來看守。我等他們抵達後,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可以確保馬歇爾能被送進軍事法庭,他們要升遷或獎章都沒問題,而且要他們在他醒來後就立刻向他宣讀他有哪些權利,特別要留心他可能會自殺。然後我把戒護的事交給他們,開車回到法蘭茲的辦公室。我的戰鬥服上到處是破洞,上面因為沾滿塵土而變硬,而且我的頭髮、手和臉也好不到哪裡去,因為法蘭
和_圖_書茲一看到我就笑了出來。
我瞄準鐵門中間,扣下扳機,子彈射了出去。槍口發出火花,砰一聲把子彈推出去,鏗鏘一聲巨響後,子彈在十碼外的鐵門上留下一個小坑洞。
他有武器。
「我的悍馬車呢?」
一小時後我還是維持四十哩車速,小屋還是沒有蹤影,不過靶場還有很大一部分沒走完。無庸置疑的,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用地之一。也許蘇聯有地方比我們更大,但我會感到很驚訝。也許威拉可以把答案告訴我。我面帶微笑,繼續開車,越過一道山脊後發現下面有片平原,前方地平線上的一個小點,可能就是那間小屋。西邊五哩外有片揚起的沙塵,可能有坦克車正在移動。
我露出微笑。
她說:「明天我們要去華府跟軍事檢察官見面。」
我想到可以確認這點的方法。
我又大聲叫他:「馬歇爾!」
他要把自己的悍馬車毀掉,然後搶走我的。
我掙扎著起來,穿越殘破的屋樑與水泥碎塊往前爬,把扭曲的屋頂鐵片往旁邊丟:我覺得自己就像剷雪機或推土機,往前輾過去後把破瓦殘礫往左右兩邊推成一堆一堆。室內塵土實在太多,我只看得見陽光直撲我而來,眼前是一片光亮,身後則一片黑暗。我繼續往前推進。
「他們說需要自白書。」
他沒有回應。
我起身跪著,然後蹲伏在車子引擎蓋的後面。這個時候其實我比之前還要安全——這輛大車整個往車的右邊傾斜,這個角度的車身不僅可以掩護我整個人,連一大片沙漠地面也被擋住。我緊靠著前擋泥板,用重達六百磅的引擎來擋住霰彈槍。我聞得到柴油味,因為一條油管被打裂了,燃料迅速漏出來。現在好了,不只輪胎被掀掉,連油箱也空了。而且我不可能脫下襯衫用它沾上燃料,點火後丟進小屋內,因為我沒火柴。而且柴油不像汽油一樣可燃,它只是一種滑滑的液體,必須先經過蒸發,加壓到一定程度後才會爆炸。這就是為什麼悍馬車被設計時就是用柴油引擎:因為安全考量。
然後我在新鮮的空氣裡走一會兒,漫無目的地在車道上走來走去。我咳嗽、吐口水,儘可能把身上的塵土拍掉。水泥碎塊在我身上留下瘀傷,我全身痠痛,身後兩哩不斷傳來坦克開火的聲音,我猜他們在聽到停火的命令前是不會停下的,但就算炮彈全部打光,他們也不會收到命令的。
馬歇爾把他們的練習目標換掉了。
我大聲叫:「放棄吧,馬歇爾!你還想惹多少麻煩?」
他不想活了,連我也要一起拖下水。
我叫得更大聲了:「我是憲兵,所有人員立刻從屋裡出來。」
法蘭茲借給我五十元,給了我兩張空白的旅行憑證。儘管蓋伯仍在千哩之外的韓國,我簽名後又用他的名字在上面副署。然後法蘭茲載我們回洛杉磯國際機場,他開的是幕僚用轎車,因為他的悍馬車上到處是馬歇爾的血。公路車流很少,我們很快就到了,進去後我用兩張旅行憑證換了下一班往華府班機的兩個座位。我把行李託運,這次我不想親手拿。我們在下午三點起飛,待在加州的時間剛好八小時整。
然後我起身蹲著,直視那間小屋。
他真的不理我,他的神智很正常,所以他不理我,而是用綺色佳霰彈槍還擊,如果是我,我也會這麼做。
「你自己在裡面?」
我想了一下,說:「我們必須回博德堡一趟。現在就走。」
「你還好嗎?」
「考古學家一百年後才會發現的地方。」
她搖頭說:「他們死也不開口,軍法局會派人來,今晚帶他們搭機到華府。已經指派律師給他們了。」
我躲到他那輛悍馬車的車蓋後面,把槍擺在溫熱的車身上。迷彩烤漆的表面凹凸不平,我覺得好像有沙粒混在裡面。我現在站的角度有點往下傾斜,於是我必須往上瞄才能打中小屋。我又開了一槍,打中上方窗框的內側。
我頓了一下。也許他沒有,因為MAG10霰彈槍有三發子彈,但他只開了一槍。可能他在等我離開掩護,然後調整位置,興奮地露出微笑,把我轟掉。我沒有多餘的彈藥可以用,用掉四發後還剩十一發。
我找到那把霰彈槍,槍管已經被壓毀,我把它丟掉,繼續往前推進。我找到躺在地板上不動的馬歇爾,拉著他的衣領,把他弄成坐姿,繼續一路把他拉到前面牆邊。我把背部靠牆,貼著牆面往上滑動,直到我碰到窗洞。我把他拉起來,塞進窗框,丟出屋外,然後也鑽www.hetubook.com•com出去。我用手撐起身子,跪著抓起他的衣領,繼續拖著他走。屋外的塵埃已經落定,我看到大概三百碼外的左右兩邊都有坦克,為數眾多,烈日的光線直接打在它們的金屬車身上。我們被坦克包圍住,它們維持怠速不動,圍成一個完美的圈圈,炮管平擺著,瞄準著我們這個方向。我又聽見砰……嗚嗯的聲響,看見一根炮管閃耀著光芒,後座力把整台坦克往後推。我看見炮彈從我們上空飛過,那劃破天際的聲音聽來就像脖子發出嘎啦嘎啦的聲響。已變成斷垣殘壁的小屋再度被擊中,我背後又揚起更多塵土與水泥碎片,我趴在地上不動,被困在這塊三不管地帶裡。
我等著。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不在乎,我不想催他。我想到一個好主意:我沿著悍馬車歪斜的一邊匍匐前進,停在後保險桿旁。我透過它往南看著我自己的悍馬車,往北我可以看到小屋。我的車跟小屋之間有二十五碼的距離,就像一塊三不管地帶。馬歇爾必須跨越這塊空地的二十五碼距離才能拿到我的車,但也把自己送進我的火網內。他有可能往後跑,邊跑邊開槍。但他的武器就算裝滿也只有三發,如果要這樣跑,他只能每八碼開一槍。如果他一開始就卯起來亂射,剩下的路程就完全沒有掩護。不管是哪種方式,我可以確定他都討不了便宜。因為我有十一發派拉貝倫子彈和一把精確的手槍,開槍時我可以把手腕擺在鋼製的保險桿上。
無線電通話的內容就是在講這件事。馬歇爾命令他們停止在西邊五哩外的活動,朝著他前進,然後朝著他自己的位置開炮。他們不敢相信,還說「再說一次?」「再說一次?」馬歇爾回覆他們:「確認。」
我對自己說:「馬歇爾,你要呼叫誰?裝甲部隊嗎?」
「辦不到。」
我又聽到了無線電的短促雜訊:了解,通話完畢。這句話說得又快又隨興,就像鋼琴的顫音。
我拿了行李,找了間來訪軍官寢室沖了個澡,然後把口袋裡的東西都擺進一件新的戰鬥服裡,把破掉的衣服扔掉,我想我的軍需官也會覺得那套衣服不能再穿了。我在床上坐了一會兒,只是發呆,然後又走回法蘭茲那裡。桑瑪回來了,看起來興沖沖的,手上拿了個很多頁的檔案夾。
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我迅速離開車道,試著走到小屋東邊。我又看到了馬歇爾,他移動到另一個小洞後面,眼神從屋裡投射到我身上。
沒有人回應我,也沒人出來,我還是可以從洞口看到馬歇爾,他也看得到我。我猜他只有一個人,如果有人跟他在一起,那個人會走出來,沒有理由怕我。
我沒回答。
我站起身用跑的完成最後十呎路程,先把馬歇爾拉到乘客座那邊,開門把他丟進前座,然後我從他身上爬過,把自己塞進駕駛座裡。我按下紅色發動鈕,啟動引擎後,打檔並用力踩下油門,因為車身猛力往前衝,車門自動關起。然後我把車燈全部打開,腳擺在地板上,讓車子全力衝刺。桑瑪一定會為我驕傲,我朝著一排排坦克衝過去,距它們剩兩百碼,一百碼,選定一個突破點後我從兩輛帶頭的戰鬥坦克中間穿過,時速超過八十哩。
接著我心裡想:裝甲部隊。一支裝甲兵團。我轉身看著西邊的塵土,突然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我孤身一人跟一個可以被證明有罪的兇手在這片荒漠裡,他在一間小屋裡,我在室外。我的搭檔是個九十磅的女人,現在人在五十哩外。他的好兄弟卻在前方可見的地平線上,開著七十噸重的坦克。
他們在對我發射練習彈。
坦克斷斷續續射出一發發的炮彈,沒有爆炸,但是一陣陣慘烈而粗暴的金屬噪音可能更糟。空中不斷出現咻咻咻的聲響,而當炮彈的動能耗盡,掉在地上時發出了砰砰砰的重擊聲。金屬與金屬之間的低沉碰撞聲,聽來令人膽戰心驚,就像古代巨人用寶劍對決時鏗鏗鏘鏘一樣。謝里丹坦克的大塊殘骸四處飛散,掉落地面後發出巨響,顫抖滑動著。空氣中彌漫著塵土,我嗆個不停。馬歇爾還在小屋裡,我蹲低拿好貝瑞塔手槍,瞄準那塊空地,等待著。我的手不敢動,兩眼直視空無一物的空間,專心一志。我不太懂,馬歇爾一定知道他不能繼續等,因為他下令坦克集中射擊,所以我們才會被艾伯朗姆斯坦克攻擊。我的悍馬車隨時都有可能中彈,他唯一逃生的機會馬上就要在他眼前破滅。悍馬m.hetubook.com.com車會被擊翻到空中,倒頭栽下。用平均律算算就知道了。又或許小屋會先被擊中,在他身邊坍塌。不管是何者,都是即將要發生的事,一定沒錯。他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但是我需要掩護嗎?
走到一半我又停下來開槍。在這種狀況之下,誰管什麼承諾呢?但我往高處瞄,打算往窗框的內側射擊,如此一來子彈要先往天花板或牆壁飛,彈射後才會打中他,大部分的力道都已經被抵銷掉,他的傷也不會很重。派拉貝倫子彈的威力是很強大,但畢竟它不會變魔術。
她說:「我們的案子成立了,軍法局說這次逮捕是合法的。」
他沒有回話,一點聲音都沒有。我繼續繞著小屋活動,走到北邊。北邊的牆面上沒有洞,只有一扇關著的鐵門。我想門上應該沒鎖,因為裡面沒有東西可以偷。我可以走過去把它打開。他有武器嗎?我猜,按照標準程序他是不會拿武器的。因為他是個偵查員,哪會遇到什麼敵人。但我覺得像馬歇爾那麼聰明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是有備而來。
我蹲低身體,迅速往西邊移動。如果他有槍,他就會開槍打我,但是不會打中。不管什麼時候,如果要我挑跟誰對決,我一定會挑一個乖乖坐辦公室擬定戰略計畫的傢伙。但話說回來,看他幹掉卡邦與布魯貝克的表現,卻又不像一個廢物。所以我把移動範圍加大,讓我有機會躲在他的車或者那輛謝里丹坦克後面。
絕對不要相信一把你沒親自試射過的武器。
為了掩護自己的逃亡,他把訓練的靶換掉。
我看到窗邊有動靜。
沉默了好一陣子後,他也對我大叫。
我不發一語。
「太順利了。」
我說:「桑瑪在哪裡?」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了。
我說:「沒有馬歇爾那輛那麼慘。」
我等到回音消退。
我一直沿著車道開,直到距離小屋三十碼外才在它南邊停下。我打開車門,走進熾熱的車外。我猜外面溫度只有攝氏二十度左右,但是去過北卡、法蘭克福與巴黎等地方後,這裡給我的感覺就像沙烏地阿拉伯一樣熱。
還是沒回話。
我往回爬,看著我的悍馬車。但如果我衝向它,無疑的馬歇爾會從屋內開槍打我。那片二十五碼的空地對我來講是很棒的攻擊目標,對他來講也是。
「妳把案情對他們講了嗎?」
接下來,謝里丹坦克在我眼前四分五裂。
我又聽見小屋裡傳來短促的無線電雜訊。
「什麼?」
我又叫他:「馬歇爾!你這是拒捕,所以我要靠過來,我要朝著窗孔開槍了。或許你會被擊中而死,子彈反彈也會打傷你。如果你不希望這樣,只要舉手走出來就好。」
我沒有打中,換他對我大叫。
我沿著道路繼續開,時速還是四十,車子經過之處也揚起一片沙塵。吹進車窗裡的空氣是熱的,那片平原也許有三哩寬,隨著我愈來愈近,地平線上的那一點變成微粒,而且愈來愈大。一哩後我可以看到前方兩個物體的形狀:那輛廢棄坦克在左邊,那個用來偵查的小屋在右邊。再過一哩後,物體變成三個,中間多了一輛馬歇爾的悍馬車。他把車停在小屋西邊,車子被籠罩在晨間的小屋陰影裡。那輛悍馬車跟我在德國十二軍團基地看到的那一輛一樣,上面也加裝了用來執行「打帶跑」戰術的反坦克導彈發射器。那間簡單的方形小屋是用煤渣磚蓋成的,牆上開了幾個大洞充當窗戶,但是沒裝上玻璃。那是一輛老舊的M551型的輕型鋁裝甲坦克,一開始的設計就是把它當成偵查車。它的體重只有艾伯朗姆斯坦克的四分之一,而且它就是賽門中校那種人心目中會在未來扮演重要角色的那種坦克。它曾經跟美軍的空降部隊一起經歷過許多戰役,性能還不錯,但是這輛看起來差不多已經快解體了。為了讓它看來比較像蘇聯前一代的坦克,還特地在坦克上面加裝一層夾板做成的護板。既然這款坦克尚未除役,當然沒必要訓練我們自己的人攻擊它。
接下來的幾枚炮彈因為是從近處發射,砰……嗚嗯,砰……嗚嗯,中間完全沒間斷。我把門拉開後衝進去,馬歇爾就站在我面前。他的臉朝南,視線受限於窗外的強光。我瞄準他左肩的肩胛骨,扣下扳機,緊接著一顆炮彈把屋頂給打掉。小屋裡瞬間彌漫著飛揚的塵土,碎裂的屋樑、瓦片往我身上砸來,無數水泥碎塊讓我感到一陣陣刺痛。我跪在地上,然後整個人趴在地上不能動,看不到馬歇爾。我掙扎起身跪hetubook.com•com著,揮手擋住破瓦殘礫。塵土往上飛揚,呈不完整的螺旋狀往上捲,我可以看到晴朗的藍天。我的周遭到處是坦克履帶轉動的聲音,接著我又聽到砰……嗚嗯的聲音,小屋前面的一角在一瞬間被轟塌了,前一秒那片堅固的水泥牆面還在,下一秒卻灰飛煙滅,緊接著是一片灰色的塵土迎面而來,速度就像聲音一樣快。一陣夾雜著塵土的強風往我這裡吹,我又倒了下去。
爾汶堡之所以會蓋在莫哈維沙漠中,主要是它很像中東地區廣袤無垠的沙漠,而且如果略去氣溫與沙土不論的話,它的地勢就跟東歐的大草原一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因為在我已經看不見基地的主要營舍很久之後,大概才只走了預定路程的十分之一而已。我身邊是一片空盪盪的平地,悍馬車在裡面就像一根針一樣渺小。當時是一月份,所以看不見熱光,但溫度還是很高。關於悍馬車裡「空調」的使用方式,我們有一種非正式的說法叫做二四〇。於是我把兩扇窗戶打開,用四十哩的時速行駛,感到一陣陣微風吹來。因為悍馬車的車身很大,所以時速四十哩就會感覺很快,但是在荒漠裡面,卻覺得好像完全沒有移動。
我聽到空中嗡嗡嗡飛來一顆像福斯汽車一樣大的炮彈,轉身時剛好看到那輛老舊坦克被炸成碎塊,好像被火車撞過似的。它往上彈了一呎高,然後車身上圍的夾板整個碎裂爆開,炮塔整個脫離後在空中慢慢翻轉,然後轟隆一聲掉在距離我十呎的沙地上。
我聽見炮管砰的一聲巨響,炮彈嗚一聲飛過來,我起身朝另一邊奔跑。然後又是砰……嗚嗯一聲,第一發炮彈擊中謝里丹坦克,把它砸翻過去,第二發炮彈擊中馬歇爾的悍馬車,將它完全瓦解。我躲在小屋北邊的角落,緊靠著牆面底部,貼著煤渣磚,感覺金屬發出一陣陣嘰哩嘎啦的響聲,那輛老舊謝里丹坦克最後解體時,傳來尖銳刺耳的聲音。
我挺身站起,把臉上的塵土抹掉,走到鐵門前,看到剛剛被我打出來的那個大洞。我知道馬歇爾此刻或者是在南邊的窗戶旁尋找正在奔跑的我,抑或是站在西邊的窗戶查看機器殘骸下是否有我的屍首。我知道他是個很高的右撇子,我心裡開始模擬一個目標,左手放在門把上等待著。
唯一的問題在於煤渣磚牆上的那些洞,它們看來跟一般的窗戶一樣大小,足以讓一個人爬過去,即使像馬歇爾一樣身材高大的人也不例外。他可以從西邊牆面爬出來,跑過去開他的悍馬車,或者從南邊牆面爬出來,開我的。軍車沒有鑰匙,而是在車上有很大的紅色啟動鈕,所以在緊急的狀況中,可以衝進車裡,立刻走人。而且我無法同時顧及兩個牆面。如果我要掩護自己,就不可能做到這點。
我站在我的悍馬車旁邊,他不發一語地看著我。
我看到馬歇爾從牆上一個洞裡看著我。
看起來完好無缺。
我對他大叫:「馬歇爾!如果你想自殺,我可以幫你忙!」
我還是用二四〇的方式進行車內空調,開到一半時馬歇爾醒了,我看到他的下巴抬起,瞥視前方,然後向左往我這邊看。嗎啡的藥效正在發作,他的右手也廢了,但我還是很小心。如果他用左手抓住方向盤,我們可能會衝出車道,不管是輾過未爆彈或烏龜,我們都會吃不了兜著走。所以我舉起右手,反手對著他的眉心給了結結實實的一拳,他立刻又昏了過去。這叫做手動式麻醉法。回到基地的一路上他都昏迷不醒。
他離開了我的視線,往後退進一片漆黑的屋內。我把借來的那把槍從口袋拿出來:那是一把新領來的貝瑞塔M9型手槍。我的腦海裡傳來一句訓練時該謹記的座右銘:絕對不要相信一把你沒親自試射過的武器。所以我把一發子彈推進槍膛裡,那聲音在一片寂靜的沙漠裡傳了開來。我看到西邊的塵土飛揚,那一陣塵土可能愈變愈大,因為它離我愈來愈近了。我把貝瑞塔手槍的保險栓調整到「可發射」的狀態。
我大叫:「少校,從屋裡出來!」
我聽見北邊與西邊斷斷續續傳來轟隆、轟隆,又低又沉悶的聲響。兩根炮管密集發射,它們的距離愈來愈近。空中傳來咻咻聲,其中一顆炮彈飛得較遠,另一顆的彈道較平坦,擊中了謝里丹坦克的側邊,射穿它的鋁製外殼又從另一邊穿出,就好像點三八子彈射穿汽水罐一樣。如果賽門中校在場,我想他對未來的規劃可能要重新盤算了。
他說:「我在裝子彈。」
接著hetubook•com•com另一輛坦克又開火,後座力把它往後震。這輛七十噸重的坦克震動力道大到把自己的前半部也掀起來,跳到半空中。它的炮彈在我們上頭發出巨響,我又開始移動,把馬歇爾拖在身後爬行,像在游泳似的穿越塵土。我不知道他對著無線電講了些什麼,下了哪些命令,一定是叫它們往外移動,也許叫他們不要管是不是會打到悍馬車。也許這可以解釋他們為何會說「再說一次?」也許他說這兩輛悍馬車也是可以攻擊的目標,所以他們覺得難以置信。
我又對他大叫:「少校,出來!你知道我為何而來。」他又退回陰暗的室內。我繼續大叫:「你的行為是拒捕!」
他不是拿手槍,我看到一根大口徑的黑色霰彈槍槍管伸出來對著我,槍管就跟雨水管一樣粗。我猜那是一把綺色佳MAG10:一把好槍,我想如果你要的是把霰彈槍,它可以說是極品。而且因為它對鋼板較薄的車子具有破壞力,所以它的綽號叫做「擋路煞」。我往後退,用悍馬車的車頭擋住自己,儘可能把身體藏起來。
他說:「正在用電傳機通知軍法局,跟他們講電話。」
馬歇爾大叫:「現在,我要裝子彈了。」
理論上我就是在等待這個時刻。使用長槍很費事,所以在他可以再度開槍之前,就是我攻擊的最佳時機。我應該立刻從掩護我的車子後面衝出來,瞄準後給他致命的一擊。所以在十號霰彈槍子彈的壓制之下,我的動作慢了半秒。我沒有被擊中,密集的霰彈往下噴出,把悍馬車的車胎打爆,我感覺到車子的一角往下陷了十吋,到處都是煙霧以及塵土。半秒後我發現槍管已經不見,我又往窗框的上方發射,因為我希望流彈能垂直往下飛,貫穿他的腦袋。
我等待著。
他在跟誰講話,而他又下了什麼命令?
炮彈沒有爆炸。我看著那塊開放的空間,馬歇爾還在小屋裡。接著我感覺到頭上被陰影籠罩,一顆炮彈又用慢動作飛過來,就像長程火炮給人的那種錯覺一樣。它以一個完美的弧度飛越我,又過了五十碼後掉落在沙漠地面上。它揚起一大片沙塵,最後自己陷進沙地裡。
我說:「你的貝瑞塔手槍被我搞丟了。」
他還是沒有回應。我已經開了三槍,還剩十二發子彈。他如果夠聰明,會躺在地板上,任我怎樣射擊也不動。所有子彈的彈道都在他上方通過,因為我的位置在他的下方,也因為那些窗框。我可以試著往天花板和遠處的牆面開槍,但這不是在打撞球,沒辦法計算彈射角度。彈著點不可預測,也不可靠。
他說:「抓個坐辦公桌的傢伙有那麼困難嗎?」
他們有幾輛坦克?我有多久時間?如果他們在這區域裡部署了二十輛坦克,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擊中一個人形目標,這顯然是幾分鐘內就會發生的事。從平均律來計算就知道了。如果被一顆五吋寬長一呎多的子彈打到,一點也不好玩,就算是擦傷,我也會死得很難看。我用來當掩護的悍馬車如果被五十磅的鐵塊擊中,它會裂開變成一片片跟藍波刀刀刃一樣大小、一樣銳利的鐵片。不需要炸藥,光是炮彈的動能就可以辦到,就好像一顆手榴彈在我身邊爆炸一樣。
馬歇爾又開槍了。我看到黑色槍管在窗邊移動,另一次爆炸聲後悍馬車的後面那一個角落也往下陷十吋。我趴在地上,斜視著車子,心想:他要把車胎都打掉。悍馬車的設計是,就算爆胎,車子還是能動。但是如果根本沒有輪胎,就走不動了。十號霰彈槍不只會把輪胎打爆,而是把整圈輪胎掀掉。它會把輪胎從鋼圈上扯下來,二十呎的範圍內到處都是輪胎皮屑。
我隱約聽見遠遠傳來渦輪引擎嘰哩嘎啦的聲音,扣鍊齒輪、中間齒輪與履帶滾輪等轉動時的金屬摩擦聲。坦克朝我開過來時,引擎傳來低沉的呼嘯聲。接著是炮管隱約傳來轟隆一聲,沉默一陣後空中傳來嗡嗡聲響,然後謝里丹坦克3T被擊中,車身再度解體破碎。練習彈的大小與體重就跟實彈一樣,推進火藥也是填滿,只有彈頭部分沒有裝進炸藥,打出來純粹只是鐵塊而已。效果其實就像手槍子彈一樣,只不過它長一呎多、寬五吋。
接著我又聽見屋內傳來無線電的聲音。那是一通很短的通訊,我只能隱約聽見,但是因為雜訊太大聲,我聽不清楚任何一個字,但是從節奏與抑揚頓挫聽起來,應該是類似「再說一次?」之類的問題。如果下令不夠清楚,就會聽見對方問這種問題。
我大聲叫他:「馬歇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