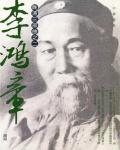第七章 身邊的刺客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軍競賽的關鍵時期,北洋水師的建設卻鬆懈下來。由於北洋海軍看起來成軍,以渤海灣為重點的防禦體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慶典、光緒皇帝大婚典禮、黃河河工等巨額開支,清政府的財政異常拮据。一八九一年,戶部決定暫停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兩年,將預算挪用於建頤和園。這一決策,使清國海軍的發展停頓了下來,也使日本海軍後來居上。
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還在上下奔波,想通過外交途徑來避免戰爭。李鴻章希望爭得西方各國的同情,給日本施壓。當俄國沒有遵守替中國調停的約定後,李鴻章就轉而請求美國和英國出面調停。紐約方面向日本提出雙方談判的照會後,日本堅決地拒絕了。倫敦方面事先未曾料到事態發展如此之快,一時也找不到適當的對策,左右為難。經過商議,英國出面提出了一項溫和的、雙方都不得罪的建議:呼籲中、日雙方同時撤軍,並在朝鮮京城周圍建立一個中立地帶。日本又拒絕了英國的建議,那是因為他們對於當時的國際形勢成竹於胸。希望徹底落空了的李鴻章,同時又延誤了清國在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直到和平解決的希望徹底破滅,李鴻章才不得不下令向朝鮮增援。
在德國,日本使節團似乎找尋到了自己國家發展的模式。剛剛完成國家統一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歡迎日本使團的宴會上實話實說:如今世界各國,雖然都說要以禮儀相交,但那畢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裡實際上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這段帶有囂張氣焰的大實話讓日本人茅塞頓開。他們不僅認同了俾斯麥的強權政治說,也醉心於德國的發展模式,那就是由國家來主導工業化的進程,以國家的力量來推動本國各方面的進步。同時,他們也在內心當中認可了一種方向,那就是軍國主義的擴張國策。
在此之後,日本與清朝洋務運動採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業化。顯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動也更迅捷。當清朝的士大夫階層慷慨陳詞地爭論購買西方「奇技淫巧」的機器會傷害民生,修鐵路會損傷地脈的時候,明治政府已開始大規模地引進外國專家、技術和設備了。僅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五年間,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國專家人數就達到了二千四百九十七人,這個數字遠遠超過清國。明治政府給予外國專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過本國的高級官員。就這樣,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遠遠超過了清國,如果說清國的現代化像一艘碩大的貨輪喘著粗氣在淺灘中航行的話,那麼,日本的改良則像一艘迅速的軍艦一樣早已進入深水區。經過廿多年的努力,到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已迅速成為令世界刮目的新興國家。
國門大開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與改革。武士們以王政復古的名義推翻了在日本歷史上持續六百年的幕府,扶持剛剛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一八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這是一個推動國家變革,開啟變法圖強大幕的總綱領。從此,日本進入明治時代,決意向西方學習,對日本實行全面改革。一八七一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團從橫濱港出發,前往歐美各國考察,代表團中包括四十九名明治高官,這個數字幾乎是當時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為了支撐這次龐大的出行,成立剛剛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當年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二。這支龐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團共考察了歐美十二個國家,共花了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在此之後,寫下了長達百卷的考察報告。這個團隊規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員級別之高,出訪時間之長,在日本和*圖*書乃至亞洲國家與西方世界的交往歷史上,都可以稱得上前所未有的。
日本窮兵黷武之際,在清廷內部,統治者正忙於權力鬥爭,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老戲正在上演。
從溯源的角度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比清國的洋務運動要整整晚八個年頭。當清國在八年之後仍是羞羞澀澀地推行洋務運動的時候,彼岸的日本一開始,就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把這場快速蛻變定位為脫胎換骨。
一八九四年,朝鮮爆發「東學黨叛亂」事件。當朝鮮國王請求清國出兵幫助鎮壓時,李鴻章聽信了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只是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一五〇〇人赴朝。與此同時,日本卻派出八〇〇〇人的精銳之師趕赴朝鮮。雙方的力量懸殊太大,清軍一下子陷入了尷尬的地步。李鴻章這時候才猛醒過來,意識到事件的危急,他一方面緊急召見英、俄使節,想請兩國出面斡旋避免戰爭,另外一方面,火速增派軍隊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但李鴻章偏偏就被甲午戰爭撞上了,可以說,甲午戰爭撞碎了李鴻章的強國夢,將他的努力付之東流,也使他的整個人生乾坤顛倒,墜入深淵。
為了迎合西方文明,顯示日本的開化,明治政府耗資十八萬日元,費時三年,在東京修起了一座洋樓——「鹿鳴館」,作為接待外國客人的迎賓館。從一定意義上說,「鹿鳴館」像一個晴雨表一樣,向日本國民傳達著一種信號。明治政府的達官貴人和外國官員經常在這裡大擺酒宴,舉辦各種西式晚會。在這裡,首相伊籐博文更像一個政治明星一樣,經常在這裡舉行大規模的化裝舞會,鬧得滿城風雨。不僅如此,為了向民眾傳達徹底西化的信號,並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籐還經常往教堂裡跑,以示對於西方宗教的熱愛。伊籐做這一切,就是向社會傳達著一種新的信息,那就是日本國準備「革面洗心」了。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我們不妨假設一回。如果命運女神真正垂青東方這塊土地的話,也許,李鴻章就能成功了。
新年剛過,李鴻章就直接預見了戰爭的不祥之兆。家門口的塘是最知深淺的了,對於李鴻章來說,北洋水師到底處於什麼樣的狀況,戰鬥力怎樣,李鴻章當然清晰不過。一八九四年五月,李鴻章再一次檢閱了北洋海軍,之後,憂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國以舟師縱橫海上,船式日新月異。臣鴻章此次在煙台、大連灣,親詣英、法、俄各鐵艦詳加察看,規制均極精堅,而英猶勝。即日本蕞爾小邦,亦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北洋海軍開辦以來,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大小二十餘艦勤加訓練,竊慮後難為繼。」李鴻章奏折中的擔心終於言中了,朝廷剛剛收到李鴻章的奏折,這邊,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李鴻章不想打,但清國另外一些人卻一心想打這場戰爭。這當中的重要代表是以光緒皇帝為首的「帝黨」,主要是光緒與他的老師戶部尚書翁同龢。原因很簡單,日本不是大英國大法蘭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和地大物博的中國打仗的話,正好給了中國一個出出這些年受西洋人窩囊氣的機會。光緒是為了心中的激奮,也是為了大清國的自尊。至於翁同龢,除了愛國熱情以及書生意氣之外,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那就是作為李鴻章的對頭,他才不願意看著李鴻章拚命地武裝自己的部隊,積極爭取俸祿卻不打仗。在翁同龢看來,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現在,無論怎麼樣,都應該來看看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到底是騾子還是馬了。中國歷史上的戰與和就是這樣充滿著非理性。戰與和,在表面的堂皇下面,總是和*圖*書有潛流與陰謀,在更多情況下,它是政治勢力的干預,而不是真正的需要。於是,屢屢出現這樣一種局面:戰則失機,和則失策;從時間與地點上,戰與和往往南轅北轍,在不該戰的時候戰,在不該和的時候和。一個在錯誤的時機下所誕生的正確決定,最終也無可奈何地變成錯誤。
行進在陌生的西方列國之中,這支日本政府團就像一塊乾燥的海綿一樣,拚命地吸收著發達國家的營養。西方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各國的政治、經濟以及教育的結構和方式,都使他們著魔。這支日本代表團的工作重點就是調查和研究資本主義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討將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節團到達美國後,由伊籐博文起草的工作要點中有這樣一句話,集中體現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初衷:「我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業,盡皆超絕東洋。由之,移開明之風於我國,特使我國國民起速進步至同等化域。」
一八八九年,光緒年屆十九,並已完婚。按照清朝慣例,光緒既然成人,慈禧就不便繼續「訓政」,於是,慈禧宣佈「撤簾歸政」,由光緒帝「親政」。「親政」和「訓政」的不同之處在於,光緒可處理日常事務,逢重大事件,再請慈禧懿旨。但這樣的「度」是很難把握的,在具體過程中,時有一些微妙的摩擦。慈禧哪裡肯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力呢?由於慈禧肆意干涉光緒的日常工作,與光緒接近的朝臣憤憤不平,光緒也鬱鬱不樂,不甘心於傀儡地位。於是,朝廷的大臣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兩派,一派是在光緒周圍逐漸形成的並無正式組織的小集團;另一派大臣則團聚在慈禧周圍,唯慈禧馬首是瞻。時人稱前者為「帝黨」,後者為「后黨」。「帝黨」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氏先後為同治、光緒老師,曾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和軍機大臣,他的主張是「尊王攘夷」。在「帝黨」中,除翁同龢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清流」人士,並無實權,他們好空談,於事無補。在這場明爭暗鬥中,直隸總督李鴻章自然是雙方爭奪的目標,但李鴻章豈是一個隨便可以爭奪的人,李鴻章雖然讚賞「帝黨」革新內政的主張,但他又不滿帝黨在「抵禦外侮」中一味不顧實力的主戰態度。在李鴻章看來,這種意氣用事的主戰,明顯是目光短淺。而對於「后黨」,李鴻章對於他們嚴重滯後的思維方式,拖拉而不思進取的效率又深感不滿。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謂如日中天,他不僅擔任直隸總督,而且還兼任北洋水師的總管。他擁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親信爪牙。並且,李鴻章還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當時清國的外交,與總理衙門「分庭抗禮」形成「兩個外交部」,形成當時清國政壇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中國駐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總理衙門,也送給李鴻章。李鴻章可以不經咨照總理衙門而直接向駐外公使發出指示。可以說,李鴻章的政治影響力、朝廷的寵信程度等,在當時的漢族大臣中,可以說無出其右。當然,更重要的,是李鴻章所倡導並身體力行的洋務運動,也初見成效,並在各方面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動力。
經過近代化的工業浪潮,日本像一頭吃飽了食物的狼一樣,變得茁壯強大起來。第一時間裡,俾斯麥強權政治的話語便如錄音機一樣在他們腦海裡回放了。日本首先把目標對準了不遠處身患病症的清國,在新興的日本國看來,這個病入膏肓的東方大國已不可救藥,與其讓西方列強慢慢蠶食,還不如先下手為強,吃了這個獵物來壯大自己。貪婪的島國開始覬覦著,
和-圖-書尋找著攻擊的時機。依舊迷糊的清朝仍惺忪著眼,對身邊的這個小國不屑一顧。清朝的傲慢越發激發了這個小國的自尊,清朝的懈怠,更加劇了日本的進攻慾望。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這個散落在太平洋的島嶼之國與中國一衣帶水,在歷史與文化上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地理環境對於民族性格的影響來說,這個一直被汪洋包圍著的民族在內心深處一直埋藏著島嶼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識,他們一直有著尋找歸宿的靠岸心態。這種天生的陸地意識和求生感,決定了居住在島嶼上的人們必然要向外擴張,並為此進行瘋狂的努力;也決定了他們具有高度的警覺和攻擊性,他們能迅速察覺恐懼的存在,然後,一旦意識到危險時,便會如野獸般一躍而起,先下手為強展開攻擊。
但李鴻章還是意識到自己身邊潛在的危險了。北洋水師基本建設完畢後,李鴻章為了展示清國水師的威力,給日本以武力震撼,先後兩次派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定遠」、「鎮遠」等艦抵日進行訪問。第一次訪問是一八八六年七月,北洋水師剛剛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鴻章的要求帶領六艘軍艦訪問日本。當清國的軍艦到達日本長崎港後,日本國民近瞻龍旗飄揚、威風凜凜的巨艦,深受刺|激,驚歎、羨慕、憤懣等複雜情緒一齊湧上心頭。清國軍艦在日本休整期間,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國民——由於北洋水師組建不久,士兵紀律鬆弛,水師官軍還在日本釀成與當地警察的大規模械鬥事件,雙方各有死傷。事態在李鴻章的直接干預下沒有進一步擴大,「定遠」、「鎮遠」艦回國後,李鴻章下令北洋水師進行大規模整風。一八九一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遠」、「鎮遠」等六艘軍艦訪問日本,這一次,經過幾年的整頓,北洋水師的軍容軍紀有了很大改變,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當時這樣描述道:登上軍艦,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艦上的情景:以前來的時候,甲板上放著關羽像,亂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難聞之極。甲板上散亂著吃剩的食物,水兵語言不整,不絕於耳。而今,不整齊的現象已蕩然無存;關羽的像已撤去,燒香的味道也無影無蹤,軍紀大為改觀。水兵的體格也一望而知其強壯武勇……
一八九四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壽之年,陰曆十月初十,是慈禧的生日。慈禧一心想舉辦盛大的生日慶典來為這個暮氣沉沉的王朝「沖沖喜」,讓列強領受天朝的威風。時間剛跨入新年,正月初一,慈禧就來了個「殊恩特沛」,把一班大臣都加官晉爵一番,以示普天同慶——李鴻章賞戴三眼花翎,兒子李經邁,被任命為員外郎……同時,慈禧指派首席軍機大臣世鐸「總辦萬壽慶典」。既然「老佛爺」想大操大辦自己的生日,舉國上下都跟著大動干戈,清廷更是忙碌起來,原先只是想把頤和園修繕一下,沒想到一動工才發現,工程越來越大,預算一再突破。戶部沒有辦法,最後不得不挪用原先準備給北洋水師更新武器彈藥的六百萬兩白銀;李鴻章也不甘示弱,也挪用了以興辦水師為名從各地徵集的錢款利息一百多萬兩送給慈禧以解燃眉之急。這樣的行為,用翁同龢的話來說,就是「用灤陽換萬壽山,用渤海換昆明湖」,這算是李鴻章對慈禧前年在自己七十大壽時贈送厚禮的「投桃報李」了。
在此之前,日本就為日本兵伐朝鮮的「師出有名」埋下了套子——這樣的苦果是李鴻章親自釀成的。那一年,日本首相伊籐博文親赴天津,與李鴻章簽署《天津條約》。當時,年輕的伊籐謙遜低調,而李中堂則倨傲自大,一派頤指氣使。在日本的爭取之下,《條約》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李鴻和圖書章向朝鮮派兵時通知了日方,而日本派出大批虎狼之師時,並沒同李鴻章打一聲招呼。
說這話是有理由的。如果歷史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一直平平緩緩發展,沒有出現大|波瀾的話,那麼李鴻章「始作俑」的洋務運動必然會成氣候,而且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經濟和近代化的進程。這樣的進程發展到一定規模,又會帶動相關領域,譬如政治、文化、社會、教育、民風等各方面的發展。這樣,洋務運動所體現的,就不僅僅是它技術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會以一種示範的作用來帶動整個社會,由洋務運動散開廣泛的力量,慢慢推動民間和上層的改變。於是,當民間和市場形成一定氣候的時候,那種加速度的效應必將來臨,那時,韜光養晦的李鴻章也許會迎來一飛沖天的時候。
一八七四年利用「琉球事件」侵台未得手後,日本痛感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將無法使自己在遠東處於領導地位。正因如此,日本舉國開始發展海軍,他們向英國訂購了「扶桑」、「金剛」、「比睿」三艘軍艦,也建立了自己的艦隊。一八八二年,朝鮮發生「壬午事變」,中日兩國皆派軍艦前往干預,當時日本海軍剛剛建立,在實力上,不如吳長慶所率領的北洋軍艦,心存忌憚,沒有發生直接的交鋒。李鴻章加速北洋水師的建設時,日本更是感到膽寒,他們轉移了戰略目標,把第一敵人從俄國變成了清國。不久,日本更是發憤圖強,政府決定從一八八三年起,將釀造業、煙酒業的稅收二千四百萬日元作為海陸軍經費,連續八年建造軍艦。一八八四年,朝鮮發生「甲申事變」,北洋海軍再次赴朝進行干涉,更加深了日本的反華情緒,只是因為日本軍方認為對華作戰的準備尚未完成,宣戰計劃未被採納。
丁汝昌在旗艦「定遠」號上招待了前來觀光的日本議員。後來,參觀過中國戰艦的日本法制局長官尾崎三良寫道:「巨炮四門,直徑一尺,為我國所未有。清朝將領皆懂英語。同行觀者在回京火車上談論,謂中國畢竟已成大國,竟已裝備如此優勢之艦隊。反觀我國,僅有三四艘三四千噸巡洋艦,無法與彼相比。皆捲舌而驚恐不安。」
黑船的到來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動。不久,佩裡再一次率領艦隊來日本。一八五四年三月,日本幕府幾乎全部接受佩裡提出的要求,簽署了日本與美利堅合眾國的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兩處港口,向美國人提供淡水、糧食和煤炭;親善條約還規定了最惠國條款,承認美國在下田駐領事的權利。隨後幾年,俄國、荷蘭等國也相繼同日本締結了親善條約。日本鎖國的大門徹底被西方列強打開。
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當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准將率四艘海軍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港通商時,日本沒有進行抵抗。他們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實力相差太大了,抵抗無疑就是送死。而且,日本已從中國鴉片戰爭中吸取了教訓。幾天後,日本允許美國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員浦賀奉行以總督的名義接受了佩裡遞交的以藍色天鵝絨包著的國書。
清國北洋水師的飛速發展以及兩次來訪給日本以強大的壓力。在這樣的情形下,建設一支足以對抗北洋水師的海軍,成為了日本的最高使命。日本明治天皇發佈詔敕,要不惜一切代價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日本國民紛紛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即捐銀六十萬兩。正是在這樣的動力下,日本完成了海軍的擴展計劃,其中包括專為對付北洋海軍「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購買的「巖島」、「松島」、「橋立」三艘海防艦,向英國訂造了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吉野」號等。到了甲午戰爭之前,日本https://m.hetubook•com•com的海軍急速擴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艦的行駛速度均超過了北洋水師。
李鴻章實在不想打這一場戰爭,這當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李鴻章明白,年底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慈禧興致勃勃地想興辦一次盛大的慶典,迷信的西太后不想被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來攪局,想討一個吉祥。二是清國國力羸弱,國民經濟也在剛剛恢復之中。對日戰爭,從李鴻章掌握的情況來看,絲毫沒有必勝的把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失敗的可能性大大超過了勝利的可能性。李鴻章想把戰局再推後幾年,在他看來,這一場戰鬥純屬無把握之戰,他不願在這樣的戰鬥中,過早地消耗自己的實力。三是李鴻章深知,如果要開戰,充當主力的,也只會是自己的淮軍和北洋水師,那些政敵們只會「坐山觀虎鬥」,李鴻章可不願意自己的部隊過早消耗。
但歷史顯然沒有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和願望的方向發展,命運狠狠地將一個爛柿子擲向了李鴻章。陰差陽錯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遠的島國日本,在最關鍵的時候捅了清國致命的一刀。
一八八二年中法戰爭瀕臨爆發之際,日本就派間諜對中國沿海進行了偵察,並提交了一本厚厚的《攻取中國以何處為難何處為易》的報告書,對中國的「山川險要,土俗人情,無不詳載」。一八九三年,負責日軍情報工作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陸軍中將還親自化名進入了朝鮮和中國境內,實地考察了預定戰區的情況,並組織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清國的一切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對清國的總兵力和作戰能力可以說瞭如指掌;對朝鮮、中國東北及渤海灣預定戰區都繪製出極其詳盡的軍用地圖,甚至每一座山丘、每一條道路、每一口水井都標識得清清楚楚。
日本這一切都是在悄無聲息的情形下進行的,清國從沒意識到自己的身邊潛伏著這樣一個血腥刺客。從歷史上看,即使這個島國上的居民不斷騷擾中國的海域時,中國也從沒有正眼看待他們,把他們當作真正的對手。雖然這個島嶼上的居民一直一廂情願地自認他們與這片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大陸從沒加以承認。在大陸人的眼中,這片叫作扶桑的天盡頭的地方,生活的只是浪人與和尚,另外也盛產一些小偷。他們看起來謙遜而恭敬,但盡愛幹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們偷走的不僅僅是物質,而且也偷走中國的文化,甚至文字。從中國歷史上對於他們的稱謂就可以看出,「倭寇」,這樣的名詞明顯地流露出蔑視的味道。當年,一幫倭寇在東南沿海一帶不斷地騷擾,讓統治者覺得很是心煩。即使如此,也並沒有把這些來自島國的強盜當作真正的對頭,何況,在這支曾經給東南沿海造成危害的散兵游勇中,領頭的,還是自己國土的逃亡商人。把他們稱為「倭寇」,只是想激起民憤。所以,即使是在清國陷入歐洲列強的危難之後,清國的上上下下對這個為虎作倀的島國也沒有正眼相對。
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衝擊的,不僅是幅員遼闊的中國。它給島國日本帶來的,同樣有巨大的衝擊波。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給日本造成的衝擊要遠遠大於中國。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日本引起的震盪是舉國性的。對於島國日本來說,幾千年來,一直都以不遠的中國為榜樣,中國一直是日本的老師,也是世界的中心,但這樣一個強大無比的國家,竟然輕而易舉地被西方打敗。這樣的感覺,就像一個孩童心中力大無窮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個外來人輕易擊倒——轟然倒塌聲中,那種恐慌和失落肯定是致命而徹底的。
夏天是太平洋季風來臨的時候,中日甲午戰爭,同樣以不可逆轉的風雨之勢撲面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