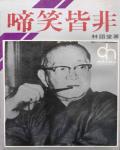卷一 局勢
證今篇第五
格立格爵士是前非洲肯亞總督,並在英國政府歷任要職。像凡爾賽和會所揭發的戰爭期中祕密條約已經開始密訂了。這回大戰的性質日益顯露出來了。老狗教不出新把戲,教也無用。當代政治家的頭腦永不會學新意義的戰爭與和平。威爾遜十四條件之廢棄不用,以此也。大西洋憲章之主義原則,現已致疑,以後將復捐棄,也以此也。
啊,自由二字,何等動人!撞起自由的鐘!但是你要傾愛自由,須教自由之神先脫下印度女人的沙利服,而穿上歐洲的女裝。有英國的自由神,使你想起英國的郊野茅屋,炊煙芳草,落日湖邊,也有印度的自由神,騎著大象在萬山深林中遊行。人類的肉眼看不出真相,不知這位我們所愛的神女,也不裹大英國旗,也不|穿印度袈裟,只圍一條透明蟬翼羽紗,無形無色,只用慧心靈眼才看得見。
這種態度有點難懂。有些美國人對於美國十三洲脫離英國獨立與印度脫離英國獨立,作兩種看法。配恩(Tom Paine)〔美國獨立戰爭中文字最動人的作者〕的話便奉為民主要典,同樣的話出於甘地尼赫魯口中,便是異端邪說。我不是美國人,不能這樣分作兩種看法。由我看來,華盛頓跟甘地尼赫魯一樣的「排英」,一樣的固執己見。可見得雙眼眼鏡委實不便。我也知道邱吉爾在紐約威名大振,甚洽民情,原可以圓滑些,附和群眾,稱頌在英國危傾時我所欽佩的英雄。但我偏要帶雙眼眼鏡,或者只靠一雙天然眼。
這篇社論結論有精警語:
(此篇專言印度問題,原名「邱吉爾與波里克里斯」,反證古今證明今日帝國與自由的衝突仍未解決,且因此大戰宗旨中途改變,暗伏第三次大戰的殺機)
如果英國政府的動機,是要對一手無寸鐵的屬國豎立威信,這目的確已達到。如果其意在收拾人心,作為日後英印合作的張本,那機會便永遠錯過了。武力征服叛變,無論有無武裝的叛變,也可以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英國武力制人,威信復立之後,還是不許黨中與黨外的領袖有機會聚頭,商討一個政治解決,雖然一九四二年十月間未入獄的領袖有這樣明確的要求。這種冥頑不靈的政策便無可原諒。英人所說「印度人自己不肯團結」這句話我就不懂。各人分禁獄中,似不是交換意見的理想環境。就是印度和尚〔yogi有仙術〕也做不來,而且甘地不是有仙術的印度和尚。「文思突破囹圄」還是文人一句說話,不適宜於拉查哥巴拉查利亞,或薩勃廬,或尼赫魯〔可以調解諸人〕。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邱首相在英下議院討論大英帝國殖民地之將來,說道:「本政府深信無疑,大英殖民地之將來統治,須繼續為大英國一己的責任。」這是清楚確定無疑昭告我們,邱吉爾立定主張,要保守印度,緬甸,馬來半島,星洲,香港,斯里蘭卡島的版圖。這樣一來,也須讓其他帝國各保存其殖民地,才算合理。由此觀之,將來自成白種人在亞洲的帝國捲土重來的局面。所以個人認邱吉爾為將來和會上的梅特涅,不是錯見。〔按:拿破崙散後,維也納和平會議,由梅特涅親王領導,恢復各國貴族皇室,協同摧殘所有革命勢力,而造成以後五十年間歐洲反動勢力的大集合。〕
假如此刻,有人對印度人說,美國種族宗教複雜,有天主教徒,耶穌教徒,猶太人,又有新政策主義者,反對新政策主義者,又有民主黨,共和黨,共產黨,社會黨,東北省人,東南省人,內革羅人,又有浸禮會,美以美會,安息日會,聖公會,摩門教(多妻教),而且猶太人,義大利人,希臘人,愛爾蘭人在遮西城同住在一條街坊,而且美國有二百五十左右教門,印度人也只好搖頭作罷,不再去理辯那錯綜迷離的紛局。但是在印度,印度人同回教徒也比鄰而居,而且如美國的義大利人同愛爾蘭人相安無事,也許更易相處。不但此也,對於一件事他們全國一致——就是要印度自由,除非是兩件事——要印度自由,和深恨英國。南斯拉夫國不是一樣嗎?也有天主教,猶太人,克羅忒族,色皮亞族,但是合之於我有利,我們就毫不遲疑把這些異族合併。老實說,假如印度沒有回教,英人也須捏造個回教出來。宗教這東西是上帝恩賜大英帝國的寶物,大英帝國和一神論不能兩立。多神論正有好處哩。
第一種主張也許似理想國烏托邦,但是他正是美國〔在國內〕的道理推廣及於世界。美國現在對付局部的現有問題,還是本著這道理做去,還是承認波羅的海俄國邊境的小國國土的完整。那第二種主張,不似烏托邦,而是著重「現實」,以武力抗衡原則及強權政治為基礎。」hetubook.com.com
假如我們以為邱吉爾忘記亞洲,便是錯了;他永不忘亞洲——是殖民區。也許我們所要清理的不是大英帝國,而是世界人類半自由半奴隸的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問題是,我們這戰爭是否為爭些主義原則,使戰爭不再實現,求一比較公道和好的世界。但這些問題都不便討論——不管大英帝國的清理或是荷蘭帝國、法蘭西帝國、日本帝國的清理。大家不要談吧。先打勝仗,仗打完了,梅特涅親王總在那邊,大家才開始爭吵攘奪。然後再過三四十年,大家再來幹一下。
要尋究歷史,不能鑽在已經檢查過的日報紙堆中,去追尋那些天天討論的很熱鬧的小枝節。要尋究歷史,應研究主持國政者的心理,去探討本源。印度人說克利浦斯爵士赴印開始談判之時,曾經答應他們組織「內閣」,而克爵士的隨員一樣熱烈的否認他曾經應允給他們組閣的真權實柄〔按:此指美記者Ouis Fisner與某英人在紐約國民週刊之爭辯〕。在這種情形之下,旁人若以為由此能明真相,便是發痴,只有由另一方法下手,先研究主持該事之人(這現代波里克里斯)的心理,才能明白克爵士赴印使命之真相。誰讀完了以下邱吉爾於一九三〇、三一年所說對於印度基本態度的話,而尚不明白克爵士何以失敗,便是低能兒。要明白這印度問題的經過,須先明白我們的波里克里斯〔雅典王,說見上章〕。一九三〇年正月,邱吉爾說:「早晚你們必須打倒甘地和印度國民大會黨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主張。」——這些主張恰巧是大西洋憲章用來適用於印度的原則。在西門爵士使團在印度接洽談判之時及其後,反對與印度開談判,認為有傷帝國及其政府人物之尊嚴,喊得最響的人便是邱吉爾,一九三一年三月他說:「我們討論這些問題,只抬高一些永遠不能與我們同意的匹夫的身價,一方面損失印度大英政府之尊嚴和權威。」一九三一年二月,他說:「把這〔治印度的〕責任移交極勉強極有限少數的印度政客黨人,便是倒行逆施,便是一種無恥的行為,便是懦怯,棄職而逃,喪盡廉恥的行為。這便是使大不列顛含垢蒙羞,在世界歷史上永遠汙及大英帝國代天宣德澤及萬民的令名。」原文照錄如下:
所以我們不必去推敲印度問題之枝節。雙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把人類自由的中心問題撇開,可以辯得你惝恍迷離,莫知所適。一個人要做一件事,總會拿出理由來,一個大國定了一種政策,總會採取名正言順的手段。有時你同人家爭辯,就已承認對方的理由有爭辯之價值。
美國的立場,光明正大。這戰爭的宗旨是為爭世界各國各民族的自由。大西洋憲章存意是要「普遍」適用於各地各民族。美國的民眾是贊同羅斯福的。美國的立場,是光明正大的。自由之旗未曾降下半竿。
沙復克利昔居伊海之濱兮,其為時已甚遠,
曾聞長浪之呼嘯兮,慨苦海之潮汐,
余居渺遠之北海兮,亦聞音而有感。
大道若溟洋兮,曩泛濫於兩極,
儼彩憧之舒卷兮,若雲旗之奪目,
悲余生之不遇兮,聞長波之太息,
聲宛宛以淒涕兮,浪奄奄而退汐,
奇晚風之悲鳴兮,漸汩沒乎尾閭。
嗟唯余與汝兮,瞻蒼茫之暮色,
嘆長夜之漫漫兮,心倉皇而失策,
若兩軍之喪明兮,羌渾沌而夜擊。
曾聞長浪之呼嘯兮,慨苦海之潮汐,
余居渺遠之北海兮,亦聞音而有感。
大道若溟洋兮,曩泛濫於兩極,
儼彩憧之舒卷兮,若雲旗之奪目,
悲余生之不遇兮,聞長波之太息,
聲宛宛以淒涕兮,浪奄奄而退汐,
奇晚風之悲鳴兮,漸汩沒乎尾閭。
嗟唯余與汝兮,瞻蒼茫之暮色,
嘆長夜之漫漫兮,心倉皇而失策,
若兩軍之喪明兮,羌渾沌而夜擊。
這一場印度問題的經過,只是指明我們未曾認清帝國與自由衝突的問題,只是指明我們精神上還未覺悟,相信「局勢有把握」時,猜疑畏忌痛恨仇惡都不足重輕。這所謂有把握的講法,就是說暴動可用武裝軍隊彈壓,而正與希特勒想法相同。我們可以斷定,戰後的印度局勢將更有「把握」,而印度不配獨立的理由還要依然存在。東西政治哲學若有不同,便是關於武力淫|威暫時成功後的久遠用處。亞洲人乖巧一點,認為為圖長久計,顧到民情要緊,眾怒不可犯,武力不足恃,且要人心和平,然後天下可以太平。
過了恰恰半載,甘地聲明他要絕食,不是抗議他私人的冤屈,而是抗議他民族的受冤屈。他明知是向頑石乞憐,但他只好如此,派他有罪也好,無罪也好,他總不改初衷。甘地固然頑強,總督也是剛決。甘地已經快要死了,而此後英印合作之夢將擊個粉碎了。印度政府即刊布一部七十六頁的白皮書,聲稱黨人有引起暴動的言行,據說,印度政府的職責是維持治安,而黨人正圖擾動抶序。「橫豎我們武力強迫所得的人力物力,比不用強調方法相同。況且局面已有把握。而且我們是為自由而戰。」
但是那兩位共同起草大西洋憲章的朋友,尚有公事未了,自從羅斯福說明該憲章的適用範圍至此已有一年多和*圖*書,而邱吉爾尚不肯與羅斯福同聲說這憲章是普遍適用於「各地各民族」。他不肯確定憲章的範圍,或是聲明一下,說美國的解釋是不誤的。他不肯適用這憲章於印度;他說這些主張條件「一點不限制〝bid not quality in any way〞關於印度、緬甸及大英帝國其他部分立憲發展的歷次聲明」。換言之,大西洋憲章的真諦妙道,人人都須實行,只有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可以特別寬免。況且應該注意,他自己相關的「歷次聲明」是如下:一九三〇年十月,他說:「我從不擬想在我們看得到的時期中,給印度與加拿大相同的憲法權利與政制。」一九三一年正月,他說:「除了在大戰期間印度代表列席開會的純粹場面儀式上的意義(purely ceremonial sense)以外,誰也不曾設想,在我們能合理或有用去推料的期間中,關於印度的原則與政策會實行起來。」〔按:現時華府「聯合國家會議」諸國列席,正合「場面儀式上的意義」〕
夫印度問題,不僅是印度的問題,乃人類自由的問題,所以已經演出一種矛盾的局面,在這自由戰爭中,印度的自由戰士因犯為自由而戰的罪名而坐監牢。除了英人而外,對此都會發怔一下。
近來我冤枉得了一個排英的罪名,至少有一些紐約婦女認為排英,因為我曾真心替印度自由呼籲。這呼籲印度自由與排英有什麼關係,我始終看不出,而我的紐約女友也說不出來。我的態度很明顯;我不是排英,我是排斥冥頑,不管那一國,我國也在內。我不僅反對邱吉爾的守舊黨的印度政策——我痛惡而深絕之。邱吉爾是英國人,我也知道,但於我,他的國籍與問題無關;不管這政策出於英法中日任何國之手,我都要痛惡而深絕之。我會明白分辨英國守舊黨人與開明黨人之不同,也會辨別邱吉爾與肯德堡大主教之不同。
To transfer that responsibility to this highly artificial and restricted oligrachy of Indian politicians would be a retrograde act. It would be a shameful act. It would be an act of cowardice desertion and dishonor. It would bring upon Great Britain a moral shame which would challenge forev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valiant and benignant for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所謂佛法業緣一說之是非,就是看你認為此事之餘波就此結束,或是認為餘波會蕩漾下去,與其他潮流併合。
這段抄文頗有大英帝國詩人吉卜寧腔調(Kiplingesque),邱吉爾和吉卜寧同時在南非戰爭中充當記者,吉卜寧對於他邦「不識聖教的下級異族」(〝the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意見,邱氏也贊同。嗚呼,使邱氏生於十六世紀尚不失為一位英雄好漢,使生於十七、十八世紀,也足以守先待後;十九世紀,他便是一位賢臣名相,於二十世紀,他只是唱吉卜寧調的違背時潮的史跡。他主張堅決,立志不移,言詞伶俐,在那幾句話中,不但可以解釋克爵士赴印之失敗,並可解釋整個印度政策之現在與將來。古代希臘波里克里斯王在國勢正盛之時說話,也不會比他莊嚴,皮匠克利翁(Cleon)不會比他愛國,賣麻繩的優克雷底斯(Eucrates)不會比他堅決,連賣油燈的海波波拉司(Hyperbolus)也不會對雅典市民發出更悅耳媚眾的腔調〔按:諸人皆波里克里斯死後主持雅典政府人物〕。我書至此,不禁想起亞諸的詩句幾行:
現在這帝國與自由衝突的問題,正引起同盟的分裂。戰爭一時未了結,我們須暫把這問題按下,至少不使妨礙我們共同作戰的努力,雖然我們在亞洲作戰的策略,也憑我們願見戰後怎樣一個亞洲而定。但是每個關心時務的作家都有職責,須告訴國民事局的真相。並於必要時加以警告,無論如何,不得蒙蔽事實以欺大眾。同盟分裂的根
和圖書芽已在,既然無法抹殺,只好把他揭曉,期弭禍患於未萌。因為戰爭或者不足使我們分裂,和平卻可使我們分崩離析。夫欲和平必須集體安全,必然而無疑,欲求集體安全,必得美國合作,又必然而無疑。然而美國或進而合作,或退而孤立,全憑一事而定,就是下次和平的性質。安琪兒爵士〔在美的英國作者,見第一章〕高調提倡集體安全,反對美國孤立。但他卻茫然不知這樣高調闊論,遇見一個激起美國人民悔恨的和平條約,便全然失效。高談闊論,勸美合作,雖是要緊,更要緊的是謀一個和平條約,值得美國的合作。美國人士也不必你來苦口婆心勸告。由心理上觀察,此刻的美國人預備放棄孤立態度比歐洲某國人預備放棄強權及帝國主義還要爽快。兩者都得同時放棄;不然,歐洲請美國幫忙合作之時,只是請美國合作幫忙歐洲的帝國主義。
我不得不忠言奉告,美國國際上的合作,只看是否有美國民眾所能贊同的公平和議辦法一事為轉移,倘使帝國主義的條約復見,必激起美國憤而孤立,那時仰首嗟嘆,也無補於事了。安琪兒爵士忘記美國的孤立態度歷史上是怎樣發生的。孤立態度之發生,由於凡爾賽條約激起反感厭憎,由於「了結一切戰爭的戰爭」一轉變成爭奪分贓的戰爭,理想幻滅,民心失望。再來一個凡爾賽,美國國民又要慨嘆上了歐洲搗鬼政治家的當,又要悔恨惆悵,退而獨善其身。在嚴重的犧牲之後,眼見理想消滅,而嗒然若喪,抽身而退,乃人之常情,而美國人民也不能免俗。因為世界保安隊要美國加入的話,就是要美國共同捍護那和平條約所訂定的國際秩序,而這國際秩序須教美國民眾誠心相信是值得護的。假定說,這國際秩序只是恢復歐洲列強的亞洲殖民地,那世界保安隊的職責便是要用武力來維護那殖民地制度,而所以擔保這制度者,乃美國人民的生命與金錢。可是,美國和中國一樣,自身一個殖民地也沒有。你教美國人不要為幾條大義公理而戰,美國人便覺得殺身而不能成仁,師出無名,而死不以其道了。
自從英國未經印度人同意替印度對德宣戰之中,中間經過兩年半,印度黨人力主鎮靜,而英國方面不肯稍讓一步,改善局勢。等到日本人打入緬甸,印度聲嘶力竭的呼籲自由,才臨時抱佛腳,派遣爵士赴印。印度人要求實權防衛國境;英人卻不肯交還實權。克爵士一行的實惠,只是由英人正式祝福「回回國」的主張(Pakistan)〔此為第一次承認〕,留為將來印度分裂之禍機。爵士回國,印人要求重開談刊,都不見效。須知印度之爭,卻是在美國分輸贏;英人在美國宣傳勝利了,所以認為十分滿意。印度黨人及民眾日益激昂,懷恨英人日深,而民氣日趨消沉。然而英人仍是兀然不動。你要叫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到了重開談判的希望失敗了,甘地事前通知印度總督,說要開始和平不合作運動。英人不肯受人威脅。甘地要求見總督,而總督擺出撫臺的威風不許他見。就此逮捕黨人入獄,這逮捕後來依英人法庭判定,認為違法。這沒有武裝的「叛變」平服了。局面有「把握」了。美國報紙表示意見,說英人剿變之後,必繼以撫綏,重開談判。然而英人卻「強硬」到底。
今日所見局面,可以看兩個不可稍缺的要點。將來美國對於國際合作最後決定的態度,大抵要憑戰後和議之性質而定。同時,這戰後和議的性質之形成,也要看我們〔美國〕有無表示,仗打完後,肯積極參加世界的政局。
讀史固然要耗費金錢精力,修氏一部希臘內戰史在現代叢書買來九角半,但不肯去精讀這部書,也許結果現代世界的耗費損失還要大。因為今日帝國和自由衝突的問題,還未解決,置之不理。因此我不能不談起印度問題。
英美兩國政府都已對法聲明,法國帝國可以完全恢復,並已對西班牙葡萄牙聲明,絕不割削他們兩個帝國的國境。且我們應當假定,聯合國中之兩位有殖民地的國,荷蘭與比利時,如有同樣的請求時,也必照樣的允許。那麼是否惟有大英帝國應該解散?
誰也明白,美國肯定一個解放菲律賓的年限,使菲律賓人相信美國的誠意。同樣的,解放印度定一年限,也可以使印度人相信英國的誠意。那末,為什麼期限未立,是誰反對呢?揮鐵格的書我們不能逃避歷史(〝We Cannot Escape History〞一九四三年出版),告訴我們一段啟人聰明的軼事。「閣員中有一些人決定要用冷不防手段迫他(邱氏)即刻進行。據那回席中人之一出來告訴人家,『愛慕利〔守舊黨員現充倫敦政府的印度部長〕正在說,打敗希特勒之後,我們應定個給印度聯邦地位的期限。話剛說完,其他政府要人正要附和,還未開口,忽聞邱吉爾吼的一聲,正像和_圖_書獅子中擊一般。霎時間房中空氣頓然肅清,宛如真有一隻獅子步入室內。從此這題目就沒有人再提起了。』」(第二四三頁)
英國這種作風,由一種假定看來才可以明白,而這假定卻是事實。這就是說同盟國武備充實之時,亞洲人什麼觀感好壞,都可不理。老實說,一九四二年整個作戰策略,都是基於一種心理習慣,說印度人,中國人,俄國人反感如何,儘可置諸度外。為什麼呢,因為英美將來有大量充實的空軍。
美國報館編輯,遇著兩位英國人如邱首相與肯德堡大主教意見恰恰相反之時,認為應該雙方加以贊同,將這大戰宗旨做個人情,以免越禮。我絕不肯把大戰宗旨送我的至親密友做人情,甚至或是送給上帝。要是某地的局部問題,我可退讓。要是鄰邦的內部政策,我也可退讓。甚至問題是先運什麼入中國——先運軍火或是先運可口可樂給駐華的美國空軍,我還可以退讓。但是到人類自由關頭,我絕不肯讓步,因為大義所在,不容苟且,而我深知我們今日在帝國與自由之間不得不擇一而從,不容易敷衍過去。因為邱吉爾明目張膽護持帝國主義,我可以推知他小時希臘歷史不曾用過功。這還小事,關係重大的是,因為一人壟斷全戰爭及和平的宗旨政策,使這大戰的性質,目標與宗旨中途改變,然而這大戰的勝利卻須賴中蘇英美各國人的頭顱共同換來。這關係綦重,就是英國的真友,也不當因送人情裝啞吧,噤若寒蟬起來。
今日這回大戰所爭只有一端——就是帝國與自由之衝突。有兩位世界領袖站在對方的兩極——一邊是蔣介石,認為「但知愛國,猶未可也」即須兼愛天下,〔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紐約論壇報所登「中國戰後的宗旨」一篇,引第一次大戰時克維爾護士Edith Cavell語。〕另一邊是邱吉爾,認為但知愛國已足。凡深思的人都得在二者之中擇一而從。現代歐洲強權政治的標準和亞洲傳統倫理的標準正相背而馳。二千二百年前,孟子說的好。「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我相信大西洋憲章,足為世界長治久安的穩固基礎,恰如威爾遜的十四條件,如果不在和議時臨時捐棄,也足以奠定和平的基礎。然而就是大西洋憲章那些主張,此刻已被憲章發動人之一斥為「神話」〔邱吉爾三月十八日演說首段〕,而關於怎樣去實行這些主張,他已經認為此刻討論含「危險性」。
因這緣故,我們今日不知大西洋憲章何時適用何時不適用,莫名其妙。依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日紐約時報社論,這一討論,便會引起大英邱首相所認為「危險」的爭端。但是依這篇社論:
俗語說:有備無患。世界如果需要美國戰時及戰後國際上的合作,須肯出一個代價,而那代價就是人類自由及平等公道的原則,一點不許還價。據我私人觀察,此刻美人完全願意負戰時及戰後國際合作上極大的犧牲,如果有法使美國人相信這代價是值得的。因此,凡是一見凡爾賽式和約復現的朕兆,就令我心慌。如果某一國不肯收拾往事,忘記前鑑,只顧收拾本利,乘勝打劫,集體安全便不可收拾(雙方關語):〝There will be no collective security if some notion wants only to collect and fails to recollect.〞因此,我談到一九四三年三月號「英國」月刊(Britain,紐約英國宣傳部發刊)所摘載格立格爵士(Sir Edward Grigg)在倫敦星期日時報的一段話,就竦然而懼:
慚愧的很,我對印度人爭取自由或法國人暗中組織爭取自由,看不出什麼分別,印度政府刊布白皮書,指明印度黨人的言論引起地方騷擾及破壞產業。東印度兩條鐵路被炸壞了,這白皮書大書而特書。如果巴黎通利爾及巴黎通里昂兩條鐵路被破壞,美國報界不知將如何褒揚這些解放人類的自由戰士!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一段佳話,證明精神不死,永不會為暴力淫|威所制服。印度有兩條鐵路炸壞,我也引以為憾,因為這有妨礙共同作戰的努力。但是你要教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同盟國分心作戰,便不能共同勝利,無論男女,人人早晚須靜心一想,各定主張,到底這回是為自由而戰,或是為帝國而戰。二者之間,無法通融,二者之外,別無良策。我們須在羅斯福與邱吉爾之間,擇一而從,因為取此必捨彼。羅邱也者,兩種道理而已。
爭端卻已引起,而從這爭論中,可以看出兩種將來國際組織的粗略規模。一種是基於大西洋憲章的嚴確解釋,期望一種世界,無論大小國,大家平等相處,並為集體安全及相互利益,藉一種國際的機構在政治及經濟上同心合作。另一種是比較縮限於歐洲,期望一個由英俄二國共同保管的歐洲,而其他較小的國因疆界之遠近,或傾於英,或傾於俄。〔按:即三月二十一日邱氏重要演講所宣布〕……和-圖-書
但是那話是一九三一年說的。大西洋憲章是一九四一年夏簽定。那時美國還未加入戰爭。不確定憲章適用範圍,倒有好處。因為倘使那時邱氏像他現在這樣清楚說法,也許美國不會加入帝國之戰。但是一九四二,四三年這兩年中同盟國仗打得好,勝利已望得到,英國愈強愈自信,而美國也已加入戰爭,欲罷不能了。當時他不肯清楚聲明的現在卻聲明的很乾脆,毫不含糊。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工黨議員馬可文(J. Mc Govern)質問邱首相,他關於大英帝國的聲明的意思是否說,「德國於戰後須交還佔領的土地,而英國不必。」邱氏答道,「這樣比擬實屬侮辱」(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紐約論壇報登載聯美社電)。他又提防人家誤會,以為他誤解大西洋憲章將適用於英國屬地與德國屬地相同,所以不憚辭費藉勃烈根(Brendan Bracken)(英國宣傳部長)轉達他的真意,昭告全世界。如果有誰「要走自招大禍的錯著,要毀滅或交出我們可觀的遺產,我想帝國尚有硬骨架,可以抵抗這種的意思……我們非捍衛我們的權利不可」,他對勃烈根聲明:「我們既是聯合國家的基本會員之一,絕不對我們的百姓說,我們可以讓世界任何國欺負。聯合國家的責任須大家聯合到底。」
但印度問題枝節雖不談,印度自由代表世界全人類自由的問題,我要談,且非談不可。因我不帶獨眼眼鏡,又不和亞司斗夫人同意,所以我視印度的自由也正如視挪威、希臘、波蘭的自由。不,管我如何同情蘇聯而痛惡納粹,德國或俄國要消滅希臘、波蘭的自由,我都要同樣反對。
所以現在大家糊裏糊塗,莫知適從,就為這個緣故。帝國與自由衝突的難關我們不可躲避,也躲避不得,雖然邱首相專講「先打勝仗」,在戰局未轉以前盡量躲避。至少他的宗旨認得清楚,說得坦白,而羅斯福不知如何是好,和他直爭也不是,不和他爭也不是。羅斯福對這帝國與自由的問題一天不表示態度,避免和他的好友拌嘴,世界人民就一天對大戰宗旨糊裏糊塗,莫名其妙。大家應該認清這員「老將」,不管他帶不帶圓頂帽;易地而居之,要是生在維也納〔梅特涅親王,主持維也納和會〕他便留個小髭。不要汲汲記住他是英國人,或是,如紐約時報所稱(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一週大事記」),「這二十多年來,他是守舊黨員之中堅」,或是如卡令德(Harold Callender)在同期所說,他是「吉卜寧詩人浪漫時代的帝國主義信徒」。今日的世界無所用乎吉卜寧時代的帝國主義者,也無需乎梅特涅。
所以此刻現在,英人正在為自由而戰,同時也正在為自由而戰的印度人。印度人也正在為自由而戰,希望獲得自由可以幫助英人在這場自由戰爭中去為自由而戰。這樣一篇糊塗賬,越弄越糊塗,假使在印度的英人也用過頭腦的話,必然中風不語。可是這也毋須過慮。在印度不會去談到「四種自由」,或是聽人提起。提起有點難為情罷?先打勝仗,再用頭腦!只有英人強健的頭腦,才會超脫一切逆情悖理的難關,而據我看來,這難關不難度過。你只須聽印度總督報告囚殺的成績一副得意忘形的神色,就可斷然無疑。「至一九四二年八月為止,殺死九百四十名,擊傷一千六百三十名,逮捕六萬零二百二十九名,判決有罪二萬六千名,囚禁未付審一萬八千名,」新共和週刊有一篇通訊說:「總督報告,正像芝加哥大屠場報告殺豬一樣。」且須記住這每隻豬都是一位自由戰士,不怯淫|威,鞭打縲絏都不怕,抑豬玀終究是豬玀耶?
其實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把世界人類作戰的宗旨做人情,送給他的至親密友,或是上帝。歷史上不論何時代,自由與反動的勢力都在角鬥,爭佔上風。各人應該運用他的聰明智力去分辨認識這兩種勢力,而站在自由與革命家一旁,毫無袒護的和反動的健將挑戰。有些美國編輯想要討好雙方。但那位老將明站那邊,視死如歸,誓不肯經管清理大英帝國。諸位美國編輯,千萬不可小覷這員老將。那老人家閱事不少,伎倆很高。凡是遇著口談仁義頭頭是道的人,你要小心。當著這員老將聲明他「要保守原有地盤」(〝We mean to hold our own〞)包括原屬印度人無疑的國土,而且教中美俄人不妨替大英帝國作戰,這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口唸「亞孟」?要是這回戰爭是英德兩國的私鬥,這話也沒什麼不該,誰打贏,誰保守他的地盤,那些屬國只當他們的賭品。如果屬國不高興的話,那是另一件事,另開一回戰,由屬國與勝利國去解決。但這次大戰又不是兩國的私戰,還牽連到多少旁人。英國首相聲明他存意將大英轄境一直管治下去之時,中國人馬上想到香港,印度人想到印度,荷蘭人想到爪哇國,而美國人就想到自由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