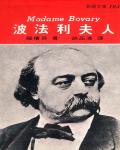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一部
8
大家又繼續談了幾分鐘的話。道別以後,倒不如說道了日安以後,城堡主人便就寢了。
雙人花步舞已經開始了。人都來了,互相擁擠著。她坐在門口的一張小長凳上。
但是她在打冷顫。她脫了衣服,蜷縮在被子裡,靠著熟睡的沙勒。
早晨三點的時候,壓軸舞開始了。艾瑪不會跳華爾滋。大家都跳華爾滋,包括昂德維利耶小姐和侯爵夫人。剩下的只有城堡裡的主人們,大約有十二個。
他們聽見拿絲達西在哭。他有點喜歡那可憐的女人。從前,當他在鰥居時期感到無聊的時候,她夜裡常常陪他。她是他第一個病人,也是他在那地區最先認識的人。
「妳滾!」艾瑪說,「妳開什麼玩笑,我叫妳滾。」
那位先生俯身。當他把手伸出去的時候,艾瑪看見那少婦的手把一點白色的東西摺成三角形放在他帽子裡。那男士拾起了扇子,恭恭敬敬地交給那位女士,她點了頭表示謝意,又開始聞著她的花束的香味。
城堡是義大利式的現代建築,有兩個伸向前的翼,三個臺階,座落在一大片草地的末端。在疏疏落落的高樹之間的牧場上有幾隻母牛正吃著草。同時,一簇簇、一團團的灌木:石南、山梅、繡球、叢集在一條蜿蜓的沙路上。一條河在橋下流著。透過霧層,你能看見牧場上星散著一棟棟的茅頂屋。牧場的兩邊有兩個傾斜度不大的山腰。牧場後面,矗立著車房和馬廄,形成兩條平行線。那些車房和馬棚都是拆掉了的舊城堡的殘餘。
沙勒默然不語,踱著方步等艾瑪穿衣服。
「別碰我,」她說,「你會弄皺我的衣服。」
艾瑪默默地看著車輪轉動。沙勒坐在長凳的邊上,張開著雙臂駕車。小馬在車轅中跳躍,對牠來說,那車轅是太大了些。軟軟的韁繩擊拍著馬的臀部,並且浸在臀部冒出的汗水裡。捆在馬車背後的盒子撞著車箱,發出有規律的響聲。
「裡面還有兩支雪茄,」他說,「吃過晚飯再抽。」
雙人花步舞跳完以後,舞池空出來了,有一群群的男士們站著談天,傭人們端來了大大的托盤。坐成一排的女士們揮動著畫扇,花束半掩著她們臉上的微笑。扇柄上金孔裡的流蘇在半開的手中旋轉著,白手套的尖端上顯出指甲的形狀,手套也緊緊地裹著手腕。花邊飾,鑽石別針,花紋像獎章的手鐲在上衣上顫動,在胸前發亮,在赤|裸的臂膀上鏗鏘有聲。前面有覆額瀏海,後面梳成髻子的頭髮上飾著琉璃草、茉莉花、石榴花、麥穗或者是矢車菊,有冠冕形的、有串簇形的、有枝枒形的。那些皺著眉的母親們裹著紅色頭巾安詳地坐著。艾瑪的舞伴牽著她的手指,她就位的時候心有點跳,但是,不久就不再緊張了。隨著樂隊的節拍,她搖盪,向前滑,脖子輕輕地動。有時,其他的樂器都停止演奏和_圖_書,只有小提琴獨奏。當她聽見小提琴優美的旋律時,唇邊不禁浮起了微笑。旁邊的桌氈上有金幣傾注出來的聲音;然後一切又繼續下去,小喇叭吹出嘹亮的聲音,舞步又按著節拍踏著,裙子鼓起來,摩擦著,手牽手又分開,如同一雙眼睛在你面前低下又凝視你。
吃午飯的時候有很多人。午飯時間只費了十分鐘。沒有飯後酒,醫生覺得很奇怪。然後,昂德維利耶小姐拾起了麵包屑,裝在一個籃子裡,拿去餵池裡的天鵝。大家去溫室裡散步,那兒有奇怪的、長滿了毛的植物,那些植物是放在懸著的花盆裡面,一層又一層,呈金字塔形。那些花盆像太滿的蛇窩,窩邊上有長長的、交錯的彩帶垂下來。另一端的橘林隱密地通向城堡的厨房。侯爵為了要取悅波法利夫人,特地帶她去看馬廐。形狀像籃子的食盤上面,有一塊一塊的瓷板,上面寫著馬的名字。有人走近的時候,每匹馬都在食槽裡激動,一面咂著舌頭。馬具房的地板亮得耀眼,像客廳裡的地板。馬具房的中央有兩根旋轉柱,上面堆著鞍轡。馬勒、馬鞭、馬鐙、馬嚼鐵則靠牆放著。
在她附近,一位女士讓自己的扇子掉在地下。一位男士正好走過。
有幾個男人(約十五個),年齡介乎二十五歲和四十歲之間,分散在舞者之間或站在門口聊天。不論他們是什麼樣的年齡,穿著是什麼樣子,長相是什麼,一望而知都是世家子弟,與眾不同。
波法利夫人注意到有幾位貴婦人不曾脫下手套,但是拿起玻璃杯的時候卻不會沾濕手套。
艾瑪在肩上披了一條圍巾,開了窗,雙手支頤。
「再回到自己家真好。」
他站在她背後透過鏡子看她,而她的影像在兩支晃動的蠟燭之間。她的黑眼睛顯得更黑了。雙鬢邊的兩片頭髮各自在耳邊凸起,發出藍色的光華,髮髻上一朵玫瑰在晃動的莖上顫抖,花瓣的尖端有人造露珠。她穿著一件淺鬱金粉色的衣裙,飾以三朵有綠葉的淡紅玫瑰。
第二天那個日子好長!她在小花園裡散步,在同樣的園徑上走來走去,在花床前面停下,在靠牆的樹群面前停下,在石膏牧師面前停下,驚訝地望著她原就很熟悉的東西。對她來說,舞會已經顯得多麼遙遠!究竟是誰把前天早晨和今天晚上隔得這麼遠?佛比薩之旅在她生活中形成了一個窟窿,一如暴風雨在一夜之間在山上形成大大的裂縫。然而,她認了。她虔誠地把她美麗的衣服和緞子鞋塞在衣櫃裡,鞋底已經在光滑的、打了蠟的地板上變黄了。她的心也和鞋子一樣:一旦觸及了富貴,上面便沾著一點永不磨滅的東西。
他把拾來的東西放在口袋裡,而且用鞭子抽著小馬。
對艾瑪來說,追懷那次舞會也是一項工作。每逢星期二來到,她一醒來就對自
和*圖*書己說:「哎!已經是八天以前的事了……已經是十五天以前的事了……三個星期以前,我在城堡裡!」漸漸地,那些人的面孔在她記憶中混成一團,她忘記了舞曲,也不再看得清楚那些傭人的制服,那些房間;若干細節消失了,但是卻把遺憾留給她。他放下了雪茄,跑到水龍頭下面喝一大口冷水。艾瑪抓起了那雪茄盒子,猛然地往衣櫥深處扔。
舞池裡的空氣很沉悶,燈光也暗淡。大家都往彈子房裡擠。一個傭人爬上了一張椅子,打破了兩塊玻璃。碎玻璃的聲音使波法利夫人轉過頭,看見花園裡有鄉下人用臉貼著玻璃窗向裡面望。那時,她想起了貝赫多農莊。她又看見了那農莊,泥濘的沼澤,穿著襯衫站在蘋果樹下的爸爸,也看見了她自己,像從前一樣,在乳品儲藏室裡用手指弄掉土罐的牛奶上面的皮。而目前的生活使她眼花撩亂,直到此刻,一向都是很清晰的過去的生活全然消失了,也懷疑她是不是曾生活過那段日子。她在舞會中,四周有的只是陰影,覆蓋著一切。於是,她用左手拿住一份裝在紅貝殼裡的櫻桃酒冰淇淋,把調羹舉向齒間,一面閉上眼睛。
「你也抽菸?」她問。
沙勒走上前去吻她的肩膀。
過廳很高,地上鋪著大理石板,腳步聲和說話聲在其中迴盪,就像在教堂裡一樣。迎面是一座筆直的樓梯,左邊是一條朝向花園的遊廊,那遊廊通向彈子房。一進門,你就能聽見象牙球撞擊的聲音。當艾瑪穿過彈子間走進客廳的時候,她看見一些面孔嚴肅的男士,下頷貼著高高的領帶結,全都掛著勳章,一面靜靜地笑,一面推動他們的球棍。牆上深色的木飾配著大大的金框子。框子的底部有黑色字母拼成的名字。她唸著那些名字。一個是「日昂.昂端.昂德維利耶.伊威朋維勒——佛比薩的伯爵,佛黑內的男爵,一五八七年十月死於古特哈之役」。另一個名字是「日昂.昂端.昂利.格伊.昂德維利耶.德拉佛比薩——法國海軍上將,聖米歇勒級騎士,一六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於烏格珊瓦斯特之役受傷,一六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死於佛比薩」。然後,她幾乎看不清其他的名字,因為投射在彈子檯綠氈上的燈光在屋子裡形成了一片浮動的陰影。燈光把畫幅照成棕色,順著油漆的裂紋碎成細條,那些大幅大幅的有金框子的畫面上有些部份比較明亮。在某些部份,你能看見一個蒼白的頭額,一雙望著你的眼睛,一些披散在紅燕尾服肩上的假髮,或是豐|滿的足脛上部的扣襪帶的鈕釦。
「鞋底間的皮帶會妨礙我跳舞。」他說。
有人斟了冰過的香檳酒。當嘴感覺到酒的冷度的時候,艾瑪全身都發抖了。她從沒有看過石榴,也沒有吃過波蘿。連那兒的砂糖也比別處的白。
和圖書「是呀!」
「妳真的要打發她走?」
他終於問了:
然而,有一個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子爵的、會跳華爾滋的人又來請波法利夫人。他的背心領口開得很大,剪裁也非常緊身。他向波法利夫人保證說他會帶,而且她也會跟。
但是當沙勒向韁繩瞧最後一眼的時候,他看見地下有點什麼東西,在他的馬腿之間。他拾起了一個雪茄盒子,四邊鑲著絲綢,中央繡著徽章,像馬車門一樣。
到家的時候,晚飯還沒有準備好。夫人生氣了。而且拿絲達西回話時的態度很傲慢。
然後,他們在厨房裡取暖,等臥房收拾好。沙勒開始抽菸。他嘟著嘴抽,每分鐘吐一口痰,每吐一口就又吸一口。
夜很黑,且下著幾點雨。她吸了一口冷風,冷風使她的眼皮感到清涼。舞會中的音樂仍然在她耳邊繚繞,她努力使自己清醒,為了使她對即將放棄的奢華生活的幻覺能夠延長一些時候。
距離艾瑪三步的地方,一位穿藍色燕尾服的騎士在和一位肌膚潔白的少婦談義大利。她戴著一串珍珠項鍊。他們誇耀聖比耶教堂的大柱,誇耀迪佛里城和維蘇威火山,誇耀卡斯達拉馬勒和卡辛林蔭道,誇耀日恩納的玫瑰,以及月下的戈利色劇院的廢墟。艾瑪用另一隻耳朵聽另一種談話,其中充滿著她不懂的字句。大家包圍著一個年紀很輕的男人,上星期他擊敗了兩匹名馬:阿哈蓓勒小姐和羅牧魯斯,在英國跳一道溝又贏了兩千路易。一位男士在抱怨他的千里馬變肥了,另一位則抱怨印錯了他的馬的名字。
大家望著他們。他們走過去又回來,她的上身不動,低著下頷,而他老是保持同樣的姿態,腰部向後彎,肘子呈圓形,嘴向前傾斜。她知道如何跳華爾滋,那個女人!他們繼續跳了很久,令大家感到厭倦。
然後,女士們上樓,去臥室裡打扮自己,準備出席舞會。艾瑪也細心化妝,像一個初次登臺的女伶,她依照理髮師的叮嚀梳她的頭髮,穿上攤在床上的細呢衣裙。沙勒覺得自己的褲腰太緊。
當他們到了廸布維勒鎭的山岡上時,突然有幾個騎士從他們面前笑著經過,口裡含著雪茄。艾瑪相信他們之中有那個子爵。她回轉頭,只看見一些人頭依著奔馳之快慢或高或低。
進餐廳的時候,艾瑪覺得自己被熱空氣裹著。那是花香和美麗的檯布味道的混合物,也是肉和香菌氣息的混合物。燭臺的鈴形銀罩上有長長的焰,蒙著一層霧的水晶杯盤反映著蒼白的燭光;整張長桌上都鋪上了和圖書花束,自一端至另一端。餐巾摺成了主教帽子的形狀,放在寬邊的碟子裡,兩個褶縫之間放著一個橢圓形的小麵包。龍蝦的紅爪子露在盤子外面,時果籃裡鋪著青苔,青苔上堆著很大的水果。鵪鶉的毛沒有拔去,胃著熱氣。總管穿著絲|襪、短褲,打著白領帶,上身穿著有襟飾的襯衫,嚴肅得像一位法官。盤子裡的菜都是切好了的。總管端著盤子,在客人的肩膀之間上菜。他只要用調羹撥一下就能把你所選的那一塊送給你。鑄有小銅柵的大瓷爐上,一個頭巾披到下頷的女人雕像正靜止地望著高朋滿座的大廳。
沙勒扶著樓梯的欄杆把自己拖下樓,膝頭彎到身體裡去了。他一連在桌子面前站了五小時,看人家玩紙牌,卻一竅不通。因此,當他脫下了靴子的時候,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舒坦於懷。
「跳舞?」她問。
他們的衣服剪裁得比別人好,料子也更細柔。他們的鬈髮垂在鬢邊,亮晶晶的,抹著更細膩的髮膏。他們的膚色是富家子的膚色,白色的,因為有許多陪襯而顯得更白:白瓷器,緞子的光澤,美好的家具的油漆,因保持健康而作的審慎的節食:精緻的食物。在低低的領帶上面,他們的脖子靈活地旋轉著,他們的長腮鬍子垂在翻領上。他們用繡著一個大字母的手帕擦嘴唇,手帕上幽香四溢。變老的人顯得年輕,而年輕人的臉上又有點什麼成熟的柬西。他們漠然的目光裡浮著一種逐日的熱情得到滿足後的平靜。他們溫文的舉止中卻流露出操縱「種」馬,結交不良婦女以及統治半難半易的事物所必需的特殊的粗暴。在做那些事情的時候,他們使出精力,虛榮心也令他們覺得好玩。
晚飯的時候有洋蔥湯,酸模配小牛肉。坐在艾瑪面前的沙勒沾沾自喜地搓著手說:
晚餐桌上有大量的西班牙酒,萊茵河酒,蝦子濃湯,杏仁濃湯,特哈法勒卡式的布丁,各種被肉凍包圍著的肉類,肉凍在盤子裡震動。晚餐以後,馬車又開始一輛一輛的離去。掀開車子的紗簾時可以看見車燈的光滑入陰影中。長板凳空了,有些賭博的人還呆在那裡,樂師們用喝過清涼飲料的舌頭舐涼指尖。沙勒半睡半醒地靠著一扇門坐著。
然而,在桌子的另一端,有一個老人弓著腰吃飯,他是女客桌上唯一的男人,盤子裡堆滿了菜,餐巾繫在脖子上,像個小孩。他吃完的時候,口角流下一滴一滴的湯汁。他眼中充滿著血絲,頭上有一條小假辮子,被一條黑緞帶繫著。那是侯爵的岳父——拉威迪耶老公爵,阿多阿伯爵昔日的寵臣。在佛德依狩獵時期,在貢佛朗侯爵家裡,有人說他曾經是瑪莉.昂端內特皇后的情人,介乎郭阿尼和羅三兩位先生之間。他曾經過著喧嘩淫逸的生活,比武、打賭、誘拐女人,把家產敗光了,使全家人害怕。他椅子背後站著一個傭人,每逢他用手指著一盤菜,那傭人就在他耳邊大聲說出那道菜的名字。他說話結結巴巴,嘴唇下垂。艾瑪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老是望向那老人,他像是一個既不尋常又莊嚴的東西。他曾在宮廷裡住過而且在皇后們的床上睡過!和圖書
天已破曉。好長一段時間,她都在望著城堡的窗子,一面猜測哪幾間是她前夕所注意到的人的臥室。她想知道他們的生活,步入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融混在一起。
侯爵打開了客廳的門,其中一位女士(侯爵夫人)站起,走向艾瑪,請她坐在她身邊,在一張雙人椅上,開始友善地和她談話,好像很久以前就認識她似的。侯爵夫人大約有四十來歲,肩膀很美,她的鼻子像鷹鉤,拖長著聲音說話。那天晚上,她在深棕色的頭髮上披了一條花邊頭巾,頭巾垂在背上,呈三角形。她旁邊有一位金髮少女,坐在一張高背椅上。男士們全都在禮服的鈕釦洞上佩著一朵花,站在壁爐旁和女士們談話。
又走了四分之一里。必須停下來用繩子接上那斷了的韁繩。
「你瘋了!人家會笑你。你呆在座位上別動。而且醫生跳舞顯得失態。」她又加了一句。
「是的,誰能阻止我?」她回答。
當她再打開眼睛的時候,客廳中央坐著一位女士,三位男士跪在她面前。她選擇了子爵做舞伴,小提琴又開始鳴奏了。
「有時也抽,當機會來到的時候。」
沙勒的馬車停在中央的臺階前面,傭人們出來了;侯爵走上前來,用手臂挽住醫生的太太,把她帶到過廳裡。
「你會把自己弄出病來。」她輕蔑地說。
然後沙勒請了一個傭人為他裝備馬車。馬車已經到了臺階前,包裹也都塞進去了。波法利夫婦向侯爵夫婦道了謝,再動身回多斯特。
傳來了一陣小提琴的旋律和號角聲。她下樓了,只差沒有跑。
七點鐘的時候,開飯了。男客比較多,坐在大廳第一桌,女士們坐第二桌,在飯廳裡,和侯爵及夫人在一起。
開始的時候,他們慢慢的跳,然後跳得快些。他們轉,四周的一切也跟著轉:燈、家具、板壁上的飾物、地板,像唱片繞著唱盤轉。跳到門邊的時候,艾瑪的裙擺掛住了舞伴的長褲;他們的腿交錯著,他低下頭看她,她仰起頭看他,她彷彿癱瘓了,停了一會兒,然後又繼續跳。子爵用更快速的動作拖她,消失在廻廊的一端,在那兒,她喘著氣,幾乎要暈倒。有一會兒的功夫,她把頭靠在他胸口上。然後,他們還是轉,只是慢些,他把她帶回原來的地方。她往後仰,靠在牆上,把手擋住眼睛。
那女士說,請為我拾起長沙發椅後面那把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