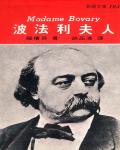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一部
9
現在,她一點也不管家事。她婆婆在四旬齋的時候曾經到多斯特住幾天,對她那種改變非常驚訝。是的,她從前在各方面都很細心,如今她一連好幾天都不換衣服,穿著灰棉布襪子,家裡也只點蠟燭。她一再說應該省錢,因為他們並不富有,又說她很滿足、很幸福,說她很喜歡多斯特城。她還說了許多新的道理使得婆婆啞口無言。而且,艾瑪似乎不再願意聽從她的規勸。有一次,當婆婆說主人應該注意傭人的宗敎生活時,艾瑪報以怒目,報以冷笑,那好心的老婦人從此不再提起那回事。
於是,她呆在那兒把火箝燒紅,一面看下雨。
大家正從敎堂裡出來。女人穿著打過蠟的木屐,農人穿著新工裝,光著頭的孩子們在大人面前跳躍,大家都回到自己家裡。也有五六個男人,老是同樣的那幾個,呆在旅店約大門口玩瓶塞遊戱,直到夜間。
她穿著一件全然敞開的睡袍,襟口露出裡面的一件有三粒金色鈕釦的、打褶的襯衫。她的腰帶是一根有流蘇的粗索子,石榴紅的便鞋上有一大簇寬緞帶,攤在脚背上。她為自己買了一張吸墨紙,一紮信紙,一個筆架,一些信封,雖然她沒有通信的對象。她拂去書架上、鏡子上的灰塵,照照鏡子,拿起一本書,然後又把書留在膝上,一面在字裡行間幻想起來。她想旅行或是回到修道院裡去住。她既想死,也想住在巴黎。
她凝視那盒子打開,甚至聞盒子襯底的味道,混和著馬鞭草和菸草的味道。那是誰的菸盒?……子爵的。也許是他的情婦送給他的。一定是在紅木繃子上繡的,繃子是可愛的小家具,平日藏起來不給人看,沉思的繡花女在繃子上面渡過不少的時辰,讓柔軟的鬈髮垂下來。愛的嘆息,曾經從針孔之間穿過,每一針都在刺繡上把一個希望,一個記憶固定,那些交錯的絲線只是同一的、無言之愛的持續。然後,有一天早晨,子爵把那盒子帶走了。當那個盒子放在壁爐的大平板上時,放在花瓶和朋巴都夫人時代的座鐘之間時,他們談些什麼?她在多斯特。而子爵此刻在巴黎。巴黎是什麼樣子?多麼偉大的名字。為了消遣,她再三用低低的聲音叫出那個名字。那名字在她耳邊發出聲音,像敎堂裡的鐘聲。那名字在她眼前發光,一直照到她髮膏瓶子的標籤上。
常常,當沙勒出去以後,她就去衣櫥裡把那個綠綢雪茄盒從衣服的褶疊裡拿出來,是她把那盒子放在那兒的。
此外,她覺得他越來越令她生氣。隨著年齡增長,他變得肥胖了。吃甜品的時候,他用刀切空酒瓶的塞子,吃完飯以後,用舌頭舐著牙齒,喝湯的時候每一口都有聲音。由於他在開始變胖,他原就很小的眼睛被臃腫的顴骨擠得往上翹。
因為她不斷地抱怨多斯特城,沙勒以為她得病的原因是由於當地的影響。因為有了這種想法,而且想定了,他認真地想換個地方行醫。
三月裡,當他們離開多斯特的時候,波法利夫人懷孕了。
春天又到來了,風和日暖。梨樹開花的時候,她反https://m.hetubook•com.com而感到窒息。
她為自己買了一張巴黎地圖,用手指在地圖上遊覽京城。她走上林蔭大道,在一條又一條街之間的轉彎處停下,在代表房屋的白色方塊前面停住。最後,她的眼睛倦了,閉上眼皮。在黑暗中,她看見煤氣燈在隨風搖曳。同時,馬車的踏脚板喧嘩地停在劇院廻廊面前。她訂了兩份雜誌,一份是名叫部「花籃」的婦女雜誌,一份則是「沙龍中的男仙」。她一字不漏地讀有關下列的報導:首次上演的戲劇、賽馬、晚會,也對歌女初次登臺和店鋪開張發生興趣。她知道新款式的時裝,好裁縫的地址,布羅尼森林遊園會的日程和歌劇院的日程。她在爾吉納.徐的小說裡研究家具之描述,她讀巴爾札克和喬治.桑的小說,只是為了在其中獲得一種假想的滿足,對她個人的貪慾之滿足。甚至在飯桌上她也帶著書。當沙勒一面吃飯一面和她說話的時候,她就翻開書頁。看書的時候,她老是想起子爵。她把他和她虛構的人物加以比較。但是以子爵為中心的圓圈在他四周擴大,他的光圈也漸漸遠離他的面孔去照亮另一些夢。
沙勒則騎著馬,風雪無阻地四處奔波。他在農家的飯桌上吃炒雞蛋,睡在潮濕的床上,打針的時候有溫熱的血濺在他臉上,他聽病人呻|吟叫喊,檢查洗臉盆,撩起骯髒的內衣,但是,夜晚回家的時候,他看見的是一爐熊熊的火,擺好了的飯桌,柔軟的家具,一個衣著考究的妻子,迷人的,帶著一股清香。他甚至不知道那香味來自何處,也不知道是否她的體香使襯衫發出香味。
她用許多細心巧思迷住他。有時,她為蠟燭臺剪一個新款式的紙盤,有時她為自己的衣裙換上一道新邊,有時女傭人把菜燒壞了,但是沙勒吃得津津有味,吃完最後一口,她就替那道菜取一個不尋常的名字。她在盧昂看見一些女士在手錶上掛著一串小裝飾品,她也照樣買了一些。她想在壁爐板上放兩個藍玻璃大花瓶,過些時,又要一個象牙盒子,一枚鍍銀頂針。沙勒越是不懂這種考究的東西也就越感到它們的魅力。她為感官增加樂趣,為家庭增加溫暖。那像是在她的生命小徑上灑一點金粉。
這種苦惱會永遠持續下去嗎?她將不能自其中走出嗎?有些女人生活得很幸福,而她並非不如她們。在佛比薩,她有見過一些公爵夫人,她們身材臃腫,也沒有什麼很好的風度。她怨恨上帝的不公平。她把頭靠在和*圖*書牆上哭。她羨慕不平靜的生活,化裝的晚會,不尋常的逸樂,以及一切她不曾體驗過的逸樂帶來的荒唐行徑。
艾瑪有時把他毛衣的紅邊塞進背心裡面,弄正他的領帶,或是把他打算戴上的、褪了色的手套扔開。他以為是為了他,其實她是為自己,由於自私,也由於生厭。有時,她也和他談她在書裡讀到的東西,像一段長篇小說,一個新劇本,或是長篇連載中的有關上流社會的故事,因為沙勒畢竟是一個人,有一對永遠傾聽的耳朵,而且他永遠贊同她的看法。為什麼不和他談話呢?何況她能和小獵犬說知心話。爐壁裡的木柴和座鐘的鐘擺當然都可能做她傾訴的對象。
於是,比海洋更虛幻的巴黎在艾瑪的眼中發亮,在一種朱紅色的氣氛中。那兒的熱鬧生活是被分成幾部份的,歸納成不同的畫面。艾瑪只看到兩、三幅,那兩、三幅遮掩住其他的一切而它們便能代表整個的人生。大使們行走在發亮的地板上,在鑲著鏡子的客廳裡,在橢圓形桌子周圍,桌子被有金色流蘇的綠天鵝絨的桌氈所覆蓋。那兒有拖地的、後擺尖長的衣裙,有大神秘,有被微笑掩飾著的痛苦。然後是大公爵夫人們的世界。她們膚色潔白,午後四時才起床。女士們(可憐的天使)的衣裙下襬上鑲著英吉利花邊,男士們輕浮的外表隱藏著不為人所知的才華。為了尋樂,他們把馬累死,他們去德國的巴得城避暑,最後,在四十歲左右,娶一個富家的女繼承人為妻。吃消夜的時候,他們在酒館裡訂特別房間,在燭光下和形形色|色的文人及女伶在一起笑鬧。他們像帝王一樣揮霍,充滿了野心,理想和瘋狂的妄想。那是一種超乎尋常的生活之上的生活,介乎天地之間,在暴風雨中,像一點什麼崇高的東西。至於其他的人,他們茫然,沒有精確的地位,像是不存在。此外,東西越鄰近,艾瑪的思想越遠離它們。那緊緊包圍著她的一切——令人煩厭的鄕村,傻傻瓜瓜的小資產階級人士,平凡的生活——像是人間的例外,一種禁錮她的特殊的偶然。然而,伸展在彼方的卻是一望無垠的幸福與熱情之國度。在她的欲望中,她把奢華的享受和心靈之悅樂混為一談,把典雅的習慣和情感的細緻混為一談。愛情,一如印度植物,不是需要特殊的溫度和專門為它準備的土壤嗎?因此,月光下的嘆息,久久的擁抱,流在被遺棄的手上的眼淚,肉體的熱情和慵懶的溫存,不能和大城堡中充滿閒暇的陽臺分開;也不能和掛著絲綢帷幕,鋪著厚厚的地毯的閨房分開;也不能和盈滿的花盆分開;也不能和有高架子的床分開;當然也不能和寶石的光彩以及軍服上的飾線分開。
在一種專注的愚鈍中,她傾聽斷斷續續的鐘聲。屋頂上有一隻貓在蒼白的陽光下弓著背,慢慢地走。大路上的風正吹起縷縷塵埃。遠處,不時傳來狗叫聲,鐘以等時的節奏繼續發出單調的音響,漸漸消失於原野中。
「多麼無用的男人!多麼窩囊的男人!」她低聲說,一面咬嘴唇。
她臉色變得蒼白,心也跳得非常劇烈。沙勒要她嗎喝纈草水,讓她用樟腦水洗澡。他試圖為她做的一切,卻使她更為生氣。有些日子,她激動地、滔滔不絕地講話,繼之而來的是猝然的癱瘓,既不說話也不動彈。那時,只有在她胳臂上灑花露水才能使她再變得有生氣。
郵局的一個夥計每天早上穿著大木屐穿過走廊來洗刷母馬。他的襯衫上有一個窟窿和圖書。他赤著脚,那就是她的穿短褲的侍僮。她應該滿足了!工作完畢以後,他就一整天都不再來,因為沙勒夜晚回來的時候是自己把馬牽入馬槽裡,取下馬鞍,解開絡頭,而女傭則抱著一把乾草,用盡氣力扔進馬槽。
失望帶來煩倦之後,她的心靈又空虛了。於是,一連串同樣的日子又開始了。
終於,拿絲逹西淚如泉湧地離開了多斯特,艾瑪找了一個女傭人代替她,一個十四歲的,面容溫婉的孤女。艾瑪不許她戴棉布帽,敎她用第三人稱說話,敎她端一杯水來的時候該用盤子托住,敎她在進到屋子裡以前要先敲門,敎她燙衣服、漿衣服,為她穿衣服,總之要把新傭人訓練成她的侍婢。新傭人為了怕被辭掉所以很聽話,也不敢埋怨。因為夫人每天有把鑰匙留在碗櫥上的習慣,所以費莉西特每晚便可偷一小包糖,做完晚禱之後一個人在床上吃。
在各方面打聽了之後,沙勒聽說內沙德縣有一個大鎮,名叫雍維勒。那兒原有的一位醫師是波蘭的難民,前一個星期走了。於是沙勒寫信給當地的藥房老闆,問那個鎮上有多少居民,最近的同行距離那兒有多遠,原來那位醫生每年有多少收入……等等,藥房老闆的回信令他很滿意,他決定了在春天搬家,假如艾瑪的健康狀態沒有好轉的話。
艾瑪變得任性,變得不容易伺候。她為自己點菜,然而卻又嚐也不嚐。一天只喝純牛奶,第二天卻喝十二杯茶。她常常固執地拒絕外出,然後感到窒息,打開窗子,換薄一點的衣服。在狠狠地折磨了女傭人以後,又送她禮物,或是讓她去鄰舍家去竄門子。同樣地,她有時把錢包裡所有的銀幣扔給窮人,雖然她並不仁慈,也不容易被別人感動,就像大多數出身於鄕野的人,心腸很硬,猶如父親的手那麼粗糙。
他身體健康,氣色也好,聲譽也完全建立了起來。鄕下人喜歡他,因為他不驕傲,他愛撫小孩,從來不泡酒吧間,而且他的品德也激起人們的信心。他尤其擅長醫治感冒和肺病。說實話,為了怕醫死病人,沙勒開的方子幾乎只是止痛劑;不時用一副嘔吐劑,洗脚或是放血。他並不害怕外科,放起血來他簡直把人當馬醫,拔起牙來,手勁可大著呢!
然而,在她心靈深處,她盼望一件事情發生,有如在急難中的水手,她讓絕望的目光在她生命的寂寞上漫遊,一面尋覓是否在遠處有什麼白帆在天邊的霧層裡。她不知道那偶然的機緣是什麼(那被風吹向她的機緣),也不知道那機緣會把她帶到什麼岸邊,更不知道那機緣是小船或是有三個甲板的大船,也不知道那船載著的是痛苦或是滿船的幸福。但是,每天早晨醒來的時候,她一整天都盼望那件事。她傾聽所有的聲音驚跳,為那事情不發生而感到驚訝,然後,當夕陽西下,她變得更憂鬱,希望翌日來到。
將近二月底的時候,老胡歐特先生為了紀念他的腿傷痊癒,親自給女婿送來一隻上好的火雞,在多斯特住了三天。但因沙勒常常和病人在一起,只好由艾瑪陪他在臥室裡抽菸,在火篦上吐痰,談農作物、小牛、母牛、家禽和市議會。當他走了以後,艾瑪把門一關,有一種滿意的感覺,那感覺令她驚訝。而且,她不再隱瞞對任何事或任何人的輕視,有時也故意表示獨特的意見,詆毀別人贊成的看法,贊成邪惡的或不道德的事物,使她的丈夫驚訝得睜大著眼睛。
打從七月開始,她就屈指計算還要多少個星期才能到十月,一面想hetubook.com.com也許昂德維利耶侯爵會在佛比薩城堡再舉行一次舞會。可是九月過去了,既無書信,也無訪客。
每天,在同樣的時辰裡,帶著黑絲絨瓜皮帽的老師打開住宅的百葉窗;工作服上佩著刀的地保,也同時走過。朝朝暮暮,驛馬三匹三匹地從街上走過,來沼澤地喝水。不時,有一家酒吧間的門鈴傳來響聲。有風的日子,理髮師常用來做招牌的小銅盆在兩根鐵桿上鏗鏘有聲,那理髮店的窗玻璃上貼著著一張破舊的時裝畫,還有一尊黄髮女人的蠟像,那些就是理髮店的裝飾品。那理髮師也埋怨這不再令他感到有興趣的職業,以及他茫然的前途。他渴望在一個什麼大城市裡有一家店鋪,比方說盧昂,一家在港口的、靠近戲院的店鋪。在那兒,他將一整天走來走去,從市政府到敎堂,一面等待顧客。波法利夫人抬起頭來的時候,她老是看見那理髮師在那兒,像一個值班的哨兵,灰色的小圓帽蓋住耳朵,穿著一件羊毛呢衣服。
然後她又上樓,關上門,重新加煤炭,在熱爐火旁邊覺得人軟軟的,也感到煩倦更重了,重重地壓在她身上。她很想下樓和女傭人在一起,但是因為不好意思,她沒有那樣做。
她用思想尾隨他們,上山下山,穿過村莊,在星光下沿著大路走。她的思想又送了他們一段路之後,總有一個她的綺夢在那兒幻滅的地方。
「他們明天就會到巴黎!」她對自己說。
打從那時候起,為了保持身材苗條,她開始喝醋,因而患了咳嗽,一種輕微的乾咳,使她完全失去了食慾。
然而,尤其是在用餐時間,她再也不能忍受:樓下的小餐廳,冒煙的爐子,咯吱咯吱地響的門,滲水的牆,潮濕的石子地。她似乎覺得她盤子裡的不是菜,而是人生中所有的苦澀。肉羹冒熱氣的時候,像是一陣一陣的平淡向她的心靈深處昇起。沙勒吃飯很慢,於是她就咬幾個硬殼果,或是用一隻手撐著下巴,另一隻手拿著刀子在檯布上用刀尖劃一道道的線條,劃著玩。
有一天,為了打算作搬家的準備,艾瑪在整理抽屜的時候,有一樣東西刺傷了她的手指。那是她的結婚花束上的一根鐵絲。花蕊已因蒙塵而變黃,緞帶的銀邊也起毛了。她把那花束扔進爐火裡。著火了,燒得比乾草還要快,片刻間那花束像是灰燼上的一叢紅色灌木,慢慢地燒掉。她望著那花束焚燒。小小的硬紙果裂開了,銅絲扭曲了,墜子溶化了,烤硬了的花瓣像黑蝴蝶一樣沿著壁爐板飄揚,最後從煙囪裡飛走了。
她放棄了音樂。彈琴幹什麼?誰聽?不值得費神去練習,既然她永遠不能穿著短袖的白絲絨衣裙在一次音樂會上,在一架艾哈牌的鋼琴上用輕柔的手指敲擊象牙鍵盤,也不能感覺到陶醉的呢喃聲在她四周像一陣微風似的飄過。她也把繪畫簿和刺繡扔在衣櫃裡。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女紅只能使她心煩。
冬天很冷。每天早晨,玻璃窗上凝著一層霜。從凝霜的玻璃窗透進來的陽光,像是透過毛玻璃進來的一樣,顯得無限蒼白,有時一整天都是那麼暗淡,因此午後四時起就要點燈。
對沙勒來說,放棄多斯特是一種很大的犧牲。他在那兒定居了四年,而且也開始出名了。然而,假如必須犧牲,就犧牲吧!他把她帶到盧昂城,看他從前的醫學老師。老師說是神經有毛病,應該換換空氣。
夜間,賣海魚的人駕著送貨車,唱著名字叫「牛至草」的民謠從她窗下經過,把她驚醒。她聽見鐵輪的聲音一出村莊很快和*圖*書就在地上消失了。
下午,她有時候去對門和驛馬夫聊天。夫人則呆在樓上。
下午,有時候理髮廳的窗玻璃後面會出現一個男人的頭,一個被太陽晒黑了的頭,他蓄著黑色的腮鬍子,慢慢地張大著嘴微笑,露出白牙。立刻,華爾滋舞就開始了。在一間小客廳裡,在一架風琴上,有一些像手指那麼高的舞俑:戴著粉紅色頭巾的女人,穿背心的奧地利山地男人,穿黑禮服的猴子,穿短褲的紳士。他們一轉再轉,在沙發椅之間,在長沙發椅之間,或在茶几之間。舞影反映在一塊一塊的鏡子裡,一條金紙把鏡子角連結在一起。領班轉動他的操縱桿,一面左看看,右看看,或望向窗外。他也不時向音樂盒的邊緣吐一口長長的、棕色的唾液,一面用膝頭頂起他的樂器,因為樂器的皮帶使他的肩膀感到痠痛。在一塊花紋曲折的鐵網下,透過一塊粉紅緞子的帷幕,傳來陣陣樂聲,有時悲悽徐緩,有時歡樂輕快。那是一些在別的地方鳴奏的曲子——在戲院裡鳴奏的、在客廳裡歌唱的、在明亮的懸燈下的舞曲,而這只是到達艾瑪耳邊上流社會的回聲。十八世紀的西班牙舞曲薩哈邦徳在艾瑪腦子裡廻盪不已。她的思想,像一個在花地毯上跳舞的印度舞|女,永不休止地搖擺,從一個夢到另一個夢,從一種憂愁到另一種憂愁。當那個賣藝的領班用帽子向觀眾收完了錢以後,他扯下一塊破舊的藍呢帷幕,把風琴揹在背上,拖著沉重的步子遠去。艾瑪望著他走過。
終於,為了不落伍,他訂了一份「醫林」,那是一種新的醫學雜誌,他曾看過廣吿。晚飯以後他看一會兒雜誌,不過,屋子裡的溫暖加上消化作用,五分鐘後他就睡著了。他就呆在那裡,雙手托著下巴,頭髮像馬鬃一樣地在燈下披著。艾瑪聳聳肩望著他。她至少也應該有這樣一個丈夫:沉默但是熱情,夜間從事著作,到了六十歲,患風濕症的時候,在不合身的黑色燕尾服上掛著一個十字勳章。她原本希望波法利那個姓(也是她的姓)變得出名,希望看見那個姓名陳列在書店裡,被報紙一再提起,被全法國所熟悉。但是沙勒沒有一點野心。伊伏多的一個醫生最近曾和他一起會診,在病人的床前和病人的家屬面前有點侮辱了他。沙勒在晚上把那件事吿訴艾瑪的時候,她大駡那個同行。沙勒因而深深感動,帶著一滴眼淚吻她的額頭。這使她感到羞辱和憤怒,幾乎想要打他,走到廊前去打開窗戶,呼吸新鮮空氣使自己平靜下來。
現在,那種日子即將一個接一個地過去,老是相同的,而且多得數不清,也不帶來什麼。別人的生活中,不論多麼平淡,至少有發生什麼事情的可能性。有時,一次奇遇會導致無限的滄桑。然後佈景也更改。但是,在她身上並不發生任何事情。那是上帝的意旨!前途是一條純黑的走廊,走廊的一端,門關得緊緊的。
「書呀,我全讀過了。」她向自己說。
天氣好的日子,她就去花園裡面走走。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了一些銀紗和一些長長的、晶瑩的線,那些線伸展著,從一棵白菜到另一棵白菜。聽不見鳥聲,一切都好像睡著了:被乾草覆蓋的、一排一排的樹,牆簷下像一條大病蛇的葡萄藤。一走近牆就能看見一些多腳的濕生蟲子在爬著。在小松樹之間,靠近籬笆的地方,那個戴著三角帽,唸著經文本的石膏牧師失去了右腳,連凍得剝落了的石膏也在他臉上做成了一些白癣。
星期天,當晚禱的鐘聲響起時,她是多麼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