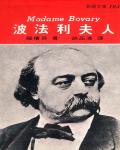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二部
2
「啊!別聽他的,波法利夫人,」歐梅插嘴說,一面俯身向菜盤,「那是百分之百的謙虛。」然後他又向雷翁說:「你說什麼,親愛的朋友!有一天,在你臥室裡,你把守護天使唱得那麼動聽。我在實驗室聽見。你唱得就像一位演員那麼好聽。」
艾瑪又說:
因為害怕患感冒,歐梅請大家允許他不脫希臘帽子。
「啊!很少。」他回答。「有一個叫牧場的地方,在山頂上,或森林的邊緣上。我禮拜天有時去那兒,帶一本書,呆在那兒看落日。」
爐灶的另一邊,一個金髮青年默默地望著她。
歐梅自我介紹過後,向夫人致敬,向醫生致意,說他很高興能為他們做了點事情。然後他又帶著很誠懇的樣子加了一句:因為太太不在家,所以他擅自來此做一名不速之客。
「我有過那種感受。」她回答。
雷翁的確是住在藥劑師家裡,在二樓一間面對廣場的小房間。聽見房東讚美他,他臉都羞紅了。藥劑師已經轉身向醫師,開始向他細數雍維勒的重要居民,一個又一個。他講故事,提供消息。人們不太清楚公證人的經濟情況,還有杜法施那一家人雖然顯得闊氣闊,其實以是虛架子。
那位秘書嘆口氣說:「老呆在一個地方生活真膩味!」
「我太太不管花園,」沙勒說,「雖然大家都勸她運動,但她老是喜歡呆在臥室裡看書。」
上了咖啡以後,費莉西特就去準備新屋裡的臥室,客人們也離開了餐桌。勒佛杭絲瓦太太在餘燼旁邊睡著了,看守馬棚的傭人提著燈,等著送波法利夫婦回家。那傭人的紅頭髮裡沾著乾草,左腳瘸著。當他用另一隻手拿了神父先生的雨傘以後,大家就開始上路。
雷翁一面談天,一面不知不覺地把一隻腳放在波法利夫人的椅子的橫檔上。她打著一條藍絲小領帶,那領帶圈住一條熨成圓筒的麻紗領子,像一種領飾。依照她轉頭的方向,她的和_圖_書下頷有時陷在領子裡,有時可愛地露在外面。當沙勒和藥劑師談話的時候,波法利夫人和雷翁一直侃侃而談。一些偶然的句子總把他倆導向一個固定的中心:相互的好感。巴黎的戲劇、小說的題目、流行的對舞,他倆不熟悉的世界,以及她住過的多斯特和他倆所在的雍維勒。他倆研究一切,談論一切,直到用完晚餐。
雷翁向波法利夫人說:「我倒覺得能常常騎馬再好也沒有了。」然後他又加了一句:「只要辦得到。」
走進廚房之後,艾瑪走近了爐灶。她用指尖從膝蓋的地方提起裙子,提到和足脛平齊的時候,她就把羊腿舉向火焰,讓它轉來轉去。她腳上穿著一雙小黑靴。火照亮她全身,一道烈火穿越她的裙子的經緯,她潔白皮膚上的毛孔,甚至她不時眨動的眼皮。順著從半開的門吹進來的風的方向,一大片紅在她身上移動著。
雍維勒鎮已經睡著了。菜市場的柱子把大大的影子投射在地上。地是灰色的,彷彿是在夏夜。
「我覺得沒有什麼比落日更可愛的東西,」她又說,「尤其是在海濱。」
「你們附近至少有些散步的地方吧?」波法利夫人繼續向那年輕人說。
波法利夫人又說:「你是否覺得在無垠的海上,思想能更自由地浮遊?你是否覺得看海能提昇你的靈魂,且向你提供一些有關無限和理想的意念?」
「對了,」見習律師說,「我覺得那些作品因為不感動人所以遠離了藝術的目的。在人生的幻滅中,能在心裡假想一些尊貴的人格,純潔的感情,幸福的畫面是溫甜的。我在這兒離群索居,閱讀是唯一的消遣。不過在雍維勒難得找到什麼書!」
藥劑師說:「因為路很好,便於駕車,在我們這個地區行醫並不太艱苦。一般說來,農民都比較富有,診費也高。根據醫學報告,除了腸炎、氣管炎、膽炎等尋常的疾病以外,在收穫時期有點間歇熱。總之,沒有什麼嚴重的疾病,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但是有許多人會生瘰癧,那不消說是因為鄉下人的屋子裡不講求衛生。啊!波法利先生,你會發現有許多偏見需要克服,許多頑固的見解需要克服,你天天作科學上的努力,但是你會遇見障礙。因為人們寧可去求九日經,去求聖骨,去求牧師,卻不肯自自然然地求助於醫師或藥劑師。但是,說實話,這裡的氣候不壞,我們這一地區也有九十歲的老人。我曾經觀察過。寒暑表在冬天降到四度。夏天的時候升到攝氏二十五度,最多三十度,也就是說攝氏表最高二十四度或是華氏表(英國算法)五十四度,就不會再多了!事實上,一邊我們有阿格伊森林擋住北風,另一邊有聖日昂山擋住西風。然而這種熱度,由於江河發散出來的水氣,也由於草原上大量的家畜(你知道家畜呼出許多阿摩尼亞混合物,也就是氮氣、氫氣、氧氣,不僅僅是氮氣和氫氣),吸收土地裡的腐朽植物,把所有不同的發散物混在一起,所以我們不妨說捆成一束。假如空氣裡有電的話,那熱度又和大氣中的電相混合,終於產生一種不衛生的瘴氣,像在熱帶國家一樣。我說那暖熱恰巧在它所來自的地方降低了,或者說在從它應該來的地方變得緩和了,那就是說在南邊被東南風降低了。那些風吹過塞納河的時候就自己變得清涼,猝然吹到我們這兒,就像俄國的微風一樣。」https://www•hetubook•com•com
但是,醫生的屋子距離旅店只有五十步之遠,大家馬上互道了晚安。那一群人就分手了。
她是第四次睡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第一次是她進修道院唸書的那一天,第二次是和*圖*書她到達多斯特的那一天,第三次是睡在佛比薩城堡裡的那一天,這是第四次。每次都像是在她的生活中作成一個新階段。她不相信在不同的地方能發生同樣的事情。既然已經生活過的部份並不好,也許待生活的部份會更好些。
「還不熟悉,可是我明年去巴黎讀法學的時候,我會去看義大利歌劇。」
「啊!我崇拜海。」雷翁先生說。
一走進甬道,艾瑪就感到石灰的寒冷像一塊濕布一樣落在她的肩上。牆是新粉刷過的,木梯軋轢有聲。在二樓的臥室裡,一道淺淺的白光正穿過沒有簾子的窗口。她窺見樹梢,以及較遠處的草地,草地一半浸浴在霧裡,霧順著河流的方向氤氳昇起。
「可不是?」她說,一面睜大著黑眼瞪著他。
他們足足用了兩小時半的晚餐,因為女傭人阿德蜜絲老是懶洋洋地在磚地上拖著布鞋走,慢吞吞地上菜,一盤又一盤,忘記一切,什麼也聽不見,而且一直讓彈子間的門虛掩,讓門鉤敲打著牆。
「真是那樣,真是那樣。」她說。
「就像我一樣,」雷翁說,「的確,當風敲打著玻璃窗,當燈亮著的時候,最好的事莫過於在爐火旁夜讀。」
「你愛什麼樣的音樂?」
「你熟悉義大利音樂家嗎?」
「你學的是音樂嗎?」她問。
「什麼也不想,」他繼續說,「時間慢慢的過去,你卻一動也不動地在你自以為看見了的地方漫遊。你的思想和虛構糾結在一起,在細節中嬉戲或是追尋故事的輪廓,思想和人物混在一起,好像是你穿著他們的衣服行動。」
他說:「這就是我特別喜歡詩人的原因。我覺得詩比散文更溫柔,更能使我們哭泣。」
雷翁又說:「妳是否有時在一本書裡面遇見一個妳曾經有過的模糊意念,遇見一個來自遠方的不清晰的形象,好像妳最細緻的情愛完全被展現出來?」
然後他轉向鄰座的女賓說:
「假如你跟我一樣,老是不
www.hetubook.com.com得不騎著馬……」
那年輕人是紀尤曼先生的秘書,他的名字是雷翁.杜布依。他在雍維勒感到無聊,他——金獅客棧的第二位常客——又常常延遲吃晚飯的時間,主要因為他希望旅社裡有什麼旅客在晚上和他聊天。做完了工作的日子,因為不知道有什麼事可做,便只好準時到來,忍受和畢內面對著面,從羹湯到乾酪。因此,他很樂意地接受了旅店女主人的提議:和新來的客人一起吃晚飯。他們走進大廳。為了炫耀,勒佛杭絲瓦太太早就擺好了四份餐具。
「夫人也許有點累了吧?我們的『燕子』顛簸得很厲害。」
聽了最後那幾句話,藥劑師說:「假如夫人肯賞光借閱,我倒是有一個圖書室供你使用,藏書都是最好的作品:伏爾泰、盧騷、德利勒、瓦爾特.司各特,副刊之回聲,等等,此外,我還訂了多種雜誌,其中有盧昂港燈報,那是日刊和_圖_書而且天天收到,因為我是布西、彿爾斯、內沙德,和雍維勒等地區的通訊員。」
「也許和多斯特一樣,」艾瑪說,「因此我總是向一家借閱處預訂。」
在屋子中央,橫七豎八地堆著一些五斗櫃的抽屜,一些瓶子,一些掛窗簾的鐵桿。幾張椅子上放著鍍金的棍子和床墊,地板上放著洗臉盆,因為兩個搬家具的人隨隨便便把東西全丟在那兒。
「不是,但是我愛音樂。」他回答。
「不過,久而久之,詩令人厭倦。」艾瑪說,「相反地,我現在喜歡一口氣連續下去的故事,叫人害怕的故事。我討厭平凡的主角和不強烈的感情,像大自然中的那樣。」
「山景也是一樣,」雷翁又說。「去年,我的一個表弟曾去瑞士旅行,他告訴我人們無法想像湖的詩意、瀑布的美麗、冰山的壯觀。他透過山澗看見大得無法相信的松樹,看見懸在峭壁上的木屋,當雲翳淡淡,能看見整個山谷在你腳下一千公尺的地方展開。那種景象真會激起熱情,使你想祈禱,使你出神入化。為了激起想像力,有一位出名的音樂家老是去一個勝地彈鋼琴。」
「啊!德國音樂,引人入夢的那種。」
藥劑師說:「剛才我曾向妳的先生說到那個逃走了的,可憐的雍達。因為他曾經亂花錢,你們才能住進雍維勒最舒服的一棟屋子裡。對一位醫生來說,那房子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有一扇朝小巷的門,出入都不會被人看見。此外,設備完善,應有盡有:洗衣間,附設食物儲藏室的廚房,客廳,水果間等等。那小子花錢的時候一點也不計較。在花園的近頭,靠近外邊,他叫人搭了一個涼棚專門供夏天喝啤酒之用。假如夫人喜歡園藝,她倒是可以……」
「對,」艾瑪回答說,「但是,動一動也好玩,我喜歡換個地方。」
艾瑪第一個下車,然後是費莉西特、勒何先生,以及奶媽。人們把沙勒喊醒,因為入夜以後,他就在自己的角落裡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