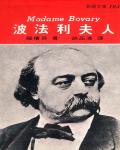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二部
13
「好像,我們看不見何多夫先生了。」
因為她怕別人盤問她,為她治病,不再離開她一步。
「是的。」聽而不聞的沙勒說。
他把籃子遞給她,她輕輕地推開了。
「小心看守她!」波法利低聲說。
該下去了!該上桌了!
他這樣寫著:
「信呢?那封信呢?」
畢竟這是真話,何多夫想,我是為她好,我誠實。
一想到她剛死裡逃生便幾乎使她嚇得昏過去。她閉上眼睛,然後,感到有一隻手觸及她的袖管,不由得哆嗦起來。是費莉西特。
這時,艾瑪漸慚醒來,她說:
一股熱氣垂直地從石板屋頂上落了下來,緊壓著她的太陽穴,令她窒息。她拖著步子走向了頂樓的天窗,拉開了窗閂,耀眼的陽光一下子迸射進來。
艾瑪聞著醋瓶,又睜開了眼睛。
孩子走向前去,伸出雙手摟住母親的脖子。但是艾瑪把頭轉過去,用急躁的聲音說:
「我喘不過氣來。」她一躍而起。
「我不會忘記妳,請相信,我會永遠對妳忠貞,但是有一天,那種熱情遲早會冷卻的(這就是世事的命運)!我們會有厭倦的感覺,而且誰知道我是否會因看見妳後悔而非常痛苦,因必須參與妳的後悔而非常痛苦,既然我是妳的後悔之源。一想到妳的悲傷我就痛苦,艾瑪!忘記我!我為什麼認識了妳?妳為什麼那麼美麗?是我的錯嗎?啊!我的上帝!不,不,不是的我的錯,一切都應該怪命運!」
之後,他抽了三斗菸,就去睡了。
「妳為什麼感到驚訝?我也贊成他不時出去散散心。當一個人有錢且又是個單身漢的時候!……而且,我們的朋友很會玩!他是一個浪子,郎格洛瓦先生告訴我……」
她嗚咽起來了。
「拿出勇氣來,艾瑪,拿出勇氣來!我不願毁掉妳的一生……」
「誰告訴我的?」他驚訝地用粗魯的聲音說:「吉哈說的,我剛才在法蘭西咖啡店門口遇見他。他說主人動身旅行去了,的確,他是應該動身出去走走了。」
說實話,那些寫信的女人同時跑入他的思想中,彼此妨害,彷彿在愛情的同一水平之下,大家平等,全變小了。於是,他拿起一把弄亂了的信,為了好玩。有幾分鐘的功夫,他讓那些信從左手落在右手裡,像瀑布流瀉一樣。最後,他睏了,也覺得無聊,就把盒子放回櫃子裡,一面說:
對了,何多夫想了又想,決定去盧昂。可是,因為從雨歇德到畢西只有雍維勒那一條路可走,他必需穿過那個村鎮。艾瑪認出了他,因為她看到那道像閃電一般劃破黃昏的燈光。
沙勒聽她的話,又坐下,把杏核hetubook.com.com吐在手裡,再放在盤子裡。
她又昏過去了。大家把她抱到床上。
「先生在等著妳,太太,湯已經上了。」
「沒有什麼,」她說,「沒有什麼,只是神經緊張!坐下來!吃吧!」
這句話總括了他的意見。就像在校園裡踩草地的中學生一樣,男女的歡愛在他心上踩得太久了,什麼綠色植物都長不出來。而且,穿過他心靈的東西比學童更糊塗,甚至不在他心扉上刻下名字。
「妳會累壞的,親愛的。」波法利說。
「誰告訴你的?」她哆嗦著說。
她試著吃點東西,但是食物令她窒息。於是她攤開餐巾,彷彿在尋找待補的破洞,想專心於那項工作,想數布幅的經緯線。突然,她想起了那封信。難道她把它丟了?到哪兒去找回來?可是她心靈那麼怠倦,從而無法找個離開餐桌的理由。然後,她變得怯懦,她害怕沙勒;他一定知道了一切。果然,他說了這句話,奇怪地。
「在哪方面?怎麼調整?」波法利說。
想了一陣子,他又寫:
她躺著,張開著嘴,緊閉著眼皮,手攤著,一動也不動,蒼白得像一尊蠟像。眼睛裡流出兩行眼淚,慢慢地流在枕頭上。
「你放心,」他用肘子推推他,「我想,危險已經過去了。」
當他到她家的時候,她正在廚桌上和費莉西特整理一包衣服。
「說話呀!」沙勒說,「說話呀!鎮靜點!是我,是愛妳的沙勒。妳認得出是我嗎?看,這是妳的小女兒,親親她!」
「妳有沒有仔細地考慮過妳的決心?可憐的天使,妳是否知道我把妳拖進一個什麼樣的深淵?妳不知道,是不是?妳瘋狂地,充滿信心地走,相信幸福,相信未來……啊!我們是可憐人,我們也胡鬧!」
「假如她問起我的消息,」他說,「你就說我去旅行去了。必須把籃子親手交給她,小心啊!」
她不禁害怕起來,一面在口袋裡找零錢,一面用茫然的眼睛望著那男工,後者也驚訝地望看她,因為不懂這點小禮物會把人感動到那種地步。他終於走了。費莉西特還是呆在那兒。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奔向客廳,好像要放下杏子。她把籃子倒轉來,翻開葉子,找到了那封信,拆開了。她十分害怕地逃到臥室裡去,好像背後起了大火。
蠟燭的芯在顫抖。何多夫站起來關上了窗戶。當他再坐下的時候,他這樣想:
他一面輕輕地推她走進涼棚裡面,一面說:
女傭人把散在架子上的杏子又放回籃子裡。沙勒沒有注意到妻子紅著臉,叫傭人把杏子給他,拿了一個,咬了一口。
m.hetubook.com•com
突然,一輛藍色的輕馬車由廣場上奔馳而過。艾瑪叫了一聲,向後一仰,僵直地倒在地上。
「全是胡鬧!」
「啊!不,不,不坐這兒。」她有氣無力地說。
剛一回到家,何多夫就在牆上掛著一個作為戰利品的鹿頭下面的書桌前坐下來。但是,當他握住筆的時候,他不知道該寫什麼,只好雙手支頤,沉思起來。他覺得艾瑪已退到了遙遠的過去,好像他剛才作的決定在他倆之間放置了一大段時間。
大家以為她在囈語。午夜以後,她真的囈語起來了:她得了腦炎。
她停住了。
但是,她勉強振作起來,那陣抽搐過去了,然後說:
艾瑪推開門,進去了。
「是的,她現在在休息了,」沙勒回答,望著她睡。「可憐的女人!……可憐的女人!……她又病了……」
他又把信重唸了一遍,覺得很好。
有四十三天的功夫,沙勒沒有離開過她一步。他放棄了所有的病人,不睡覺,不停地為她把脈,貼芥子膏,敷冷水布。他派雨斯丹去內沙德買冰,冰在路上溶化了,他再派他去。他請卡尼維先生來會診,他派人去盧昂請他從前的老師拉利維耶博士。他在絕望中。最使他害怕的是艾瑪的萎靡不振,因為她不說話,什麼也不聽,甚至假裝不痛苦——彷彿她的肉體和靈魂同時停止了騷動。
「聞聞看嘛!好香!」他說,一面把一個杏子在她鼻尖前面晃來晃去。
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點左右,因為睡得很晚),他叫人摘了一籃杏子。他把信放在杏子底下的葡萄葉下面,立刻叫他的犁夫吉哈小心地送到波法利夫人家裡。他已往一直用這種方法和她通信,依照季節送她水果或是獵物。
「不,不……什麼人也不要!」
現在怎麼簽名呢?他對自己說,「妳的忠誠的……?不,妳的朋友……?對了,就是這個——妳的朋友」。
他就這樣一面徘徊在回憶中,一面端詳著拼法繁複的筆跡和書信的風格。那些書信來自不同的女友,有的溫柔,有的愉快,有的詼諧,有的憂鬱,有的要愛情,有的要金錢。有時某一句話就使他記起一些面孔,某些姿勢,一個嗓音;然而有時卻什麼也記不起。
我覺得所有的話都說過了。啊,還要加上這幾句話,免得她再來煩我:
「啊!太好吃了!」他說,「妳嚐嚐看。」
她靠看天窗的窗口,把信唸了一遍,帶著憤怒的笑。但是,她越是專注,她的思想也越是紊亂。她又看見他,聽見他,用雙臂摟住他。她的心好像一隻公羊,在胸口砰砰砰不均勻地跳,一下比一下hetubook.com.com快。她向四周看了一眼,恨不得陷下去。為什麼不結束自己?誰阻止她?她是自由的。她向前走了,望望石板地,一面向自己說:
「我去實驗室拿點香醋來。」藥劑師說。
沙勒在臥室裡,她看見了他。他和她說話,她什麼也聽不見,她繼續往上跑,喘著氣,茫然地,昏昏沉沉地,手裡還是拿著那張可怕的紙,像鐵皮一樣在手裡鏗然有聲。到了三樓的時候,她在關著的門前停下。
「我能肯定,」他說,「即使是死人也能一聞就醒。」
十月中的時候,她已經能靠著枕頭坐在床上。看見她吃第一塊果醬麵包的時候,沙勒哭了。她的精力恢復了。下午,她起來幾個鐘頭。有一天,她覺得好些,他試著讓她挽住他的胳臂在花園裡轉一圈。園徑上的沙在枯葉下面消失了。她穿著拖鞋,一步一步地走,肩膀靠著沙勒,不斷地微笑著。
藥劑師縱續說:「不只是人有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動物也有。所以,你不是不知道,俗名叫小薄荷的那種植物對於貓類動物具有奇特的激發春情的效果。此外,再舉一個我保證確實的例子。布利杜(我的一位老同學,如今住在馬巴路街)有一隻狗,只要人一拿鼻煙給牠聞,牠就渾身抽搐。他常常在吉犬姆森林別墅裡,甚至當著朋友的面作實驗。誰會相信單純的催噴嚏劑能在四腳動物的生理組識上作成如此大的蹂躪?很奇怪,是不是?」
「這是我主人送給妳的。」犁夫說。
「哎!問題就在這裡。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像我最近在報上看見的『丹麥王子』一劇中的話,我是在報上看見的。」
於是,藥劑師問那場意外是怎麼突然發生的。沙勒回答說,當他吃杏子的時候,就那麼猝然來到了。
說我破產了吧?……啊,不!破產並不礙事。因為可以東山再起。我能和這種女人去講理嗎?
「哎!假如妳是那種水性楊花的女人,像我常見到的,由於自私,我會作一種對妳來說是危險的試驗。但是妳那份美妙的、激越的情愫使妳這個可愛的女人變成當局者迷,妨害妳瞭解我們未來的地位的謬誤。那份情愫使妳迷人,也使妳痛苦。起先,我也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憩息在理想幸福的影子下面,像憩息在一株毒性植物的陰影下面,而不預料到後果。」
「啊,不,不會有人看見,」她想,「這兒很好。」
對方帶著善意而自滿的微笑著說:「這件事就向我們證明神經系統中無數的不規則現象。關於嫂夫人,我承認,我一向覺得她真是個敏感的人。因此,我勸告你,我的好朋友,千萬不可用對症https://www.hetubook•com•com下藥的藉口亂開方子,到頭來反而會傷了身體。不,不要隨便用藥,只要節食,如此而已!鎮靜劑!緩和劑!甜化劑!然後,你不覺得她的想像需要調整?」
也許她會以為我是因為吝嗇才放棄的……沒有關係,活該!必須了結!
命運這詞彙永遠會收到良好效果,他對自己說。
「人是殘酷的。不論我們在哪兒,他們都會追踪我們!妳必須忍受盤問、毀謗、輕視,也許還要忍受侮辱——對妳的侮辱。啊!……我這個要把妳放在座台上的人!我這個把對妳的懷念當作護身符一樣帶走的人!因為我以放逐自己作為因傷害了妳而對自己的懲罰!我走了。去哪兒?我不知道。我要發瘋了。再見!請永遠對我仁慈!請記住那個失去了妳的可憐人!請把我的名字告訴妳的女兒,讓她在祈禱文中再說出我的名字。」
「當妳讀這封悲悽的信時,我已遠去;因為我要儘快逃走,為了避免再去看妳,無法自制。請妳堅強!我會再回來。也許,我們日後可以冷靜地談起我們往日的愛情。再見。」
何多夫停筆了,要找一個好藉口。
對面,在屋頂下,田野一望無際地伸展著。在她下面,廣場是空的。人行道上的碎石子在閃著光。屋上的風信雞都靜止著。一種尖銳的聲音從街角一家二樓上傳來了,那是畢內在使用切木機。
「再見」這個字這一次是拆開來寫的(不是Adieu而是A Dieu),意思是在上帝面前見。他覺得那種分寫法頗富情趣。
「得了,」他向自己說,「該開始寫信了!」
吉哈穿上了新的藍襯衫,拿一塊大手帕圍住杏子打了一個結,穿著包鐵的大木底鞋,用又大又重的腳步平靜地走在通往雍維勒的路上。
「奇怪!……」藥劑師說,「可能是杏子引起的昏厥。有些人生來對某些味道特別敏感。就病理學而言,那甚至是她一個極待研究的問題,甚至就生理學而言都值得研究。牧師們知道香味的重要性,所以宗教典禮老是和香味分不開。他們用香味麻醉理智,刺|激感情,在女性方面更容易收到效果,因為她們比較脆弱。有人證明,某些人聞到燒焦了的獸角或是新鮮麵包的氣味就會暈過去。」
為了要再抓住一點屬於她的什麼東西,他去床頭的櫃子裡面找一個來自赫安斯城的舊餅乾盒。通常,他把女友們的信放在那盒子裡,盒子裡散發出一陣潮濕的灰塵味和枯玫瑰花的氣息。首先他看見一條手絹,上面全是淡淡的斑點。那條手帕是她的,有一次散步的時候她流了鼻血,他已不復記憶。旁邊是艾瑪送給他的小照,四個和圖書角都損壞了。他覺得她的衣飾太誇張,她的媚眼也很可悲,然後,由於久久凝視那個畫像和喚起對本人的回憶,艾瑪的眉目面貌漸漸地融混在他的記憶裡,好像活人和畫像互相觸及也互相磨滅。最後,他讀了她幾封信,信裡充滿了有關旅行的解釋,簡短、技術、迫切、倒像商業函件。他想再看看她從前的長信。為了在盒子的底部找到她的信,他翻亂了所有的信。他開始機械地在那一堆紙和物品裡找,找到亂成一團的花束、吊帶,一個黑色面具、髮夾和頭髮——一些頭髮!棕色的、金色的。有幾根甚至在開盒子的時候斷了,因為它掛在鐵盒子的縫裡。
他停住了,因為不想在女傭人面前失態。
「跳呀!跳呀!」
「在這種情況之下使用那枚印章顯得不大適合……得了,沒有關係!」
「在這長凳上坐下,妳會感到舒服。」
況且,這可憐的男人還要為錢發愁。
沙勒站在屋子的末端,藥劑師帶著安靜的沉思狀站在他身旁,那種神情是適合於人生中最嚴肅的場面的。
此刻,她必須鎮靜。她想起了那封信,應該唸完它,但是又不敢。而且,在哪兒唸?怎麼唸?人家會看見。
她覺得頭昏。打從那天晚上開始,她的病又發了,捉摸不定,但是病狀更複雜了。她有時心痛,有時胸口痛,然後是腦痛,然後是四肢痠痛。她有時突然想吐,沙勒以為是癌症的初期現象。
「可憐的小女人!」他溫柔地想。「她將會以為我比一塊磐石還更無情。應該有幾滴眼淚。可是我哭不出來。那不是我的錯」。於是,何多夫把手指浸在璃玻杯裡的水上,讓一大滴水從高處落下,滴落在信上形成一個淡淡的斑點。然後,封口的時候,他看見了「心心相印」那枚印章。
從下面昇起的日光直接把她的身體拉向深淵。她覺得搖晃的廣場在沿著牆升起,覺得地板的末端在傾斜,像一條搖盪的船。她站在邊上,幾乎是懸著的,被一大片空間所包圍。天的蔚藍在侵襲她,空氣在她空虛的頭腦裡循環,她只要順從,只要束手待捕。切木機不停地旋轉著的聲響像是一個呼喚她的、憤怒的聲音。
聽見醫生家裡亂糟糟的,藥劑師趕忙過來了。桌子,連帶所有的碟子,都翻倒了。屋子裡到處都是肉、肉汁、刀子、鹽瓶、油瓶。沙勒大聲求救,貝特嚇得直叫,費莉西特為太太解開衣服,她的手直發抖,而太太則渾身抽搐。
「太太!太太!」沙勒喊。
就那樣,他們一直走到園子的末端,靠著陽台。她慢慢地挺直身子,遙望著很遠的地方,把手放在眼前。但是天邊只有燃燒的草,在小山上冒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