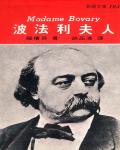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二部
14
「那麼,他們錯了。」布尼賢忍讓地說。
但是,當他作開瓶示範的時候,蘋果酒濺了他們一臉,於是教士笑了,從來不放過這句玩笑:
他說:「我只是想說容忍是把人導向宗教之路的最好方法。」這次他的聲音比較溫和。
畢內也在,那就是說,在更下面一點。他在靠著陽台的牆邊釣蝦子。波法利請他過來乘涼,他對開瓶子非常內行。
波法利腦子裡很快就萌發了去看戲的念頭。他把那個念頭告訴他妻子,後者立刻拒絕了,理由是疲倦及勞民傷財,奇怪的是,沙勒沒有順從,因為他覺得那種娛樂對她是那麼有益。他看不出有任何阻礙。母親給他寄來了三百法朗,他並不靠那筆錢,因為目前並沒有太多的債務,勒何先生的借據距離到期的日子也還遠著,不必操心。而且,沙勒以為她是顧慮得周到,於是愈加堅持,終於,因為拗不過他的糾纏,她也下了決心去。第二天,八點鐘,他們搭乘了「燕子」。
「自然,」歐梅繼續說,「有壞文學,就像有壞藥劑學一樣,但是,以偏概全地批判最重要的藝術,我覺得是一種愚行,是一種野蠻觀念,只有在把義大利名物理學家打進監牢的時代,才有人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地批判文學。」
神父驚訝於這種性向,雖然他覺得艾瑪的宗教由於狂熱可能淪為異端或是有陷入狂妄的危險。神父自覺在超越了限度的宗教狂熱方面自己所知道的並不太多,於是寫信給主教的書商寄給他一些什麼「為一個總明女性」讀的好書。書商漫不經心,好像給黑奴寄鋼鐵器皿一樣,把當時流行的聖書亂七八糟地打包寄來。那是些小小的問答手冊,那是模仿政論家德.麥克特先生的傲慢風格的佈道手冊,以及若干紅色硬封面的小說,風格是軟綿綿的,若非出自神學院的行吟詩人的手筆,便是悔罪的閨秀文豪的把戲。還有「好好地想」、「聖母腳前的上流人」,著者是得若干枚勳章的XX先生,以及為少年讀者的「伏爾泰的錯誤」。
「我認識的。」
但是,他只呆了兩分鐘。他一走,歐梅就向醫師說:「這就是所謂的鬥嘴。你是看見的,我好好的捉弄了他一番。總之,相信我,帶你太太去看戲,哪怕只是為了氣死這個老傢伙也值得,一生中就那麼一次!假如有人替我,我自己都願意陪你們去。快去嘛!拉卡迪只上演一次,倫敦重金禮聘他。有人說那傢伙真有本事。他在金子堆裡打滾。他帶著三個情婦、一個廚師!所有的大藝術https://www.hetubook.com.com家都透支生命,他們需要不羈的生活刺|激想像。但是他們卻死在平民醫院裡,因為年輕的時候沒有積錢的頭腦。好,祝你胃口好。明天見!」
而且,他一切順利。他是內沙德醫院的蘋果酒的法定供應者;紀尤曼先生答應他可以有格呂門尼的泥炭礦股票;他渴望在阿格依和盧昂之間添增一班公用馬車服務站。如果那件事一辦成功,他就能使金獅客棧的破車破產,因為他的車子走得快,收費也較低廉,又能裝更多的貨。這樣一來,雍維勒的商業就會落在他手裡。
「妳的肚子不疼了吧,我的天使?」
自然,艾瑪沒有注意到他無言的慇懃,也沒有注意到他的膽怯。她一點也不知道,從她生命中消失了的愛情就在她身邊顫動,在粗布襯衫下面,在那少年的心中,那顆心向她身上發散出來的美麗敞開著。而且,她現在以大冷漠裹被一切,她的語言那麼親切,目光又那麼高傲,態度那麼變化多端,大家從而無法辨別自私和仁慈,腐敗和道德。比方說,一天晚上,女傭人結結巴巴地找個藉口向她請假外出,她生氣了,然後又突然問:
「先生!」神父睜大著充滿怒火的眼睛說,樣子十分可怕,使藥劑師畏怯了。
有一天,病得最厲害的時候,她自以為快死了,曾經要求領聖餐,大家在她臥室裡張羅聖禮,堆滿了藥瓶的五斗櫃改成了聖壇,費莉西特往地板上撒大理菊。那時候,艾瑪聞到一點有強烈味道的東西掠過,解除了她的痛苦,以及一切知覺、一切情感。她輕盈的肉體不再想什麼,另一種生命卻正在開始。她覺得自己整個的人正升向上帝,即將在那種聖潔的愛中消滅,像一柱點燃了的香消散在氤氳中。有人把聖水澆在床單上,神父從聖符中取出了白色的聖餅,她伸出嘴去接受救主的聖體,她因過度神聖的歡樂而虛弱不堪。她的床帷像雲一樣在她四周鼓起來,五斗櫃上燃著的蠟燭對她來說像是令人目眩的榮光。她垂下頭,以為聽見空中有仙琴在鳴奏,以為看見天父在蔚藍的天空裡,在金質的寶座上,在拿著綠棕櫚的萬聖之間。天父威儀萬千,做了一個手姿,示意有如火焰般翅翼的天使下凡,把她帶走。
「好酒朝眼睛跳(這是雙關語,也可以譯為:很明顯地,他是個好人)。」
初春時候,不顧沙勒的反對,她叫人把花園翻了一遍。看見她終於振作起來,他還是很高興。健康越恢復,她也越振作。首先,她想到了一個辦法把奶媽趕走。後者在她養病期間養成了一種習慣:經常帶著自己兩個吃奶的孩子和一個在她家寄食的孩子到廚房裡覓食,那些孩子全比食人者還更能吃。然後,她擺脫了歐梅一家人,辭謝了其他所有的訪客,先先後後地,甚至也不像從前那麼勤勉地去教堂。這一點,
m.hetubook.com.com藥劑師非常贊成,友善地向她說:老波法利太太覺得兒媳婦沒有可責怪的地方,除非是她不補抹布而是一個勁兒替孤兒打毛線衣。但是老太太在家裡受夠了丈夫的氣,她喜歡兒子家裡的寧靜。為了避免老波法利的嘲笑,她一直住到復活節以後。他每個星期五都要吃血腸而不齋戒。
像從前一樣,布尼賢神父每天下了教理問答課以後還是突然來到。他寧可呆在外面,在「林子」裡呼吸空氣,他把涼棚稱為林子。那是沙勒回家的時辰。他們感到熱。有人拿了甜蘋果酒來,就一起喝酒祝賀夫人痊癒。
那華美的景象一直停留在她記憶中,彷彿是人可能夢見的最美麗的東西。因此,她現在還努力追憶那種感覺,那種感覺雖然繼續存在,也同樣甜美,但是不像當時那麼完全地吸引她。她因驕傲而疼痛的靈魂終於在基督教的謙卑中得到安息。艾瑪品嘗做一個脆弱的人的快樂,她凝視意志力在自己心中摧毀。由於意志力的摧毀,主的恩寵便源源而來。那麼,除了人間的幸福之外,還存在著一些更大的幸福!同時,還有一種駕乎一切愛情之上的愛!那種愛是永無止境的,而且與日俱增!在眾多的幻覺之間,她窺見了一種純潔的境界,那境界從地面飄起,和天空混融,她希望活在天上。她想變成一個聖女。於是她買了唸珠,佩戴符咒,她希望床頭有一個鑲翡翠的盒子,裡面放著先聖的遺物,讓她每晚吻著。
波法利夫人不能用心看任何東西,因為她的智力還沒有完全恢復。而且她看那些書也看得太快。教條的苛刻使她生氣,她討厭論戰文的傲慢,因為作者絲毫不放鬆那些她不認識的人。她又覺得宣揚宗教的世俗故事揭露的只是對世界的隔閡,不知不覺地使她遠離真理,而她卻等待著真理的證實。不過她還是繼續看下去。當書從她手裡落下時,她自以為感染了天主教的最美好的憂鬱。那種憂鬱是一個純潔的靈魂所能有的。
神父抗議說:「我明明知道有好作品,有好作家。可是把男男女女聚集在同一個迷人的屋子裡,加上豪華的陳設,異教徒的服裝、脂粉、燭光,女性的聲音,這一切都會產生精神上的放蕩,引起卑污的思想,不純潔的誘惑。至少,神父都這麼想。」然後,他忽然用一種神秘的聲音,一面用拇指揉一撮鼻煙,一面說:「總之,教會排斥戲劇,自然有它的道理,我們應該服從它的命令。」
「我認識過一些神父,他們穿著世俗的衣服去看舞|女的蹦跳。」
歐梅又說,而且是把音節分開:「我——認——識——的。」
他向四周滿意地看了一眼,一直望到田野的邊際,一面說:你必須在桌子上把瓶子拿直,把繩子割斷,一點一點地推軟木塞,輕輕地,輕輕地,就像人們在飯館裡開塞爾茲水一樣。
「一路順風!」他向m.hetubook.com.com他們說,「你們真幸運!」
夫人為自己買了一頂帽子,一雙手套,一束花。先生非常害怕錯過了開場戲,他們湯也來不及喝就趕到劇院門口,門還沒有開。
神父只嘆了一口氣,藥劑師繼續說:
他用拉丁語說:「一面笑,一面移風易俗,布尼賢神父。所以,請看伏爾泰大部份的悲劇,其中巧妙地充滿了啟蒙哲學意味的話語。那些話語對群眾來說像是一所真正的學校,讓他們學習道德和外交。」
至於對何多夫的回憶,她讓它沉落到心靈深處。那份記憶停留在那兒,比埋在地下的木乃伊還更莊嚴、更靜止。那薰過香的偉大愛情發散著一股氣息,滲透一切,也用溫柔薰著純潔的大氣,她想生活在其中。跪在哥德式的祈禱凳上的時候,她向天主說的話和她從前在偷情的熱烈中向情人所說的話一般甘美。她那樣做是為了使信仰來到,但是沒有任何悅樂從天而降。她再站起來,雙腿疲倦,隱隱約約地感到一種莫大的欺騙。她想,這種追尋值得上天記她一大功,而且,在虔敬的驕傲中,她把自己和過去的貴婦人相比,她曾經看過拉.法利葉的一張畫像,也渴望過她們的榮譽。生活曾傷害過那些貴婦人的心。她們曳著長裙鑲了邊的下擺,帶看一副莊嚴的樣子,隱居在孤寂中,讓眼淚流到基督的腳前。
「你應該承認,聖經真不是一本該給年輕人讀的書。我會惱火,假如我女兒阿達莉……」
「從前妳信教信得太過份了。」
於是她大行善事,為窮人縫衣服,給產婦送木柴。有一天沙勒回來,看見廚房裡坐著三個無賴,在那兒喝濃湯。她生病的時候,丈夫曾把女兒送到奶媽家去,現在她把她接回來了。她要教她唸書。貝特哭也沒有用,她還是不生氣。她認了,她忍讓,那是一種普遍的寬容。不論談到什麼,她的語言都是理想的表達。她向女兒說:
起先,所有的藥都是從歐梅先生那兒拿的,他不知道如何來償還。雖然以醫生的身份他原可以不付錢,可是那種人情使他臉紅。還有,現在是女廚師當家,開銷就大得驚人。發票像雨一般地落在家裡,店鋪老闆也在嘀咕,勒何先生特別煩他。原來,當艾瑪病得最厲害的時候,他趁火打劫,多開了帳,他立刻就把大衣和旅行袋拿來了。艾瑪只訂了一口箱子,他卻搬來了兩口,還拿了一些別的東西來。即使沙勒說不需要那些東西,要了也是枉然,那商人高傲地說訂了的東西不能退。而且,那樣做會影響太太復元,先生要考慮考慮。總之他寧可起訴也不願放棄權利而把東西收回去。後來,沙勒說叫人把那些東西送到他店裡去,可是費莉西特忘了,沙勒又有別的煩惱,也就沒有再想到那回事。勒何先生又來討帳,既恐嚇,也哀求,他手腕那麼好,波法利不得不開給他一張六個月的期票。他剛簽了那張期票,就突然有和_圖_書了一個大膽的念頭:向勒何先生借一千法朗。於是,他帶著一副尷尬的樣子問他是否可以借給他一千法朗,為期一年,利率由債主決定。勒何跑回店裡去,帶來一千法朗,口授一張借據,波法利在借據上說明下年九月一日付清一千零七十法朗,加上原來的一百八十法朗,共計一千二百五十法朗。若此,以六分利借出,加上四分之一的傭金,貨物起碼給他帶來三分之一的盈餘,一年下來就有一百三十法朗好賺。他的希望並不止於此。假如波法利屆時無法償還要續借,那麼他那少數可憐的錢在醫生那兒就像在一家療養院裡,營養充足,有一天會又肥又胖地回到他的身邊,撐破他的口袋。
當布尼賢神父做了一個氣憤的手勢的時候,藥劑師說:
對方不耐煩地說:「勸人讀聖經的是新教徒而不是我們!」
「這句話說得對!這句話說得對!」那好心的神父讓步了,一面再在椅子上坐下。
「是的。」醫師漠然地回答。也許是他和藥劑師意見相同而又不願意冒犯任何人。或是他沒有意見。
婆婆正直的判斷和舉止的端莊給了艾瑪不少力量。除了陪伴婆婆以外,艾瑪幾乎每天都有別的朋友。那是郎格洛瓦太太、卡洪太太、杜布何伊太太、杜法施太太,以及好心的歐梅太太。後者經常在兩點到五點之間來,而且從來不相信別人傳說的關於她鄰居的壞話。歐梅家的孩子們也來看她,雨斯丹陪他們來。他陪他們上樓走到臥室,站在門口,動也不動,話也不說。波法利夫人時常不介意地開始梳妝,取下梳子,一面猛搖她的頭。第一次看見她的黑辮子散開來,一直垂到腿彎的時候,對那可憐的男孩來說,像是忽然走進一個新奇的地方,那兒的華美使他害怕。
事實上,他是個好人。有一天,藥劑師勸沙勒帶太太去盧昂戲院看男高音拉卡迪,讓她散散心。畢內也沒有大驚小怪。歐梅看見他不作聲,想知道他的意見,而神父說他認為文學比音樂更傷風化。
藥劑師問:「為什麼教會拒絕演員皈依宗教?從前他們還公開參加宗教崇拜。是的,他們在唱聖歌的地方上演稱為神秘劇的戲劇,滑稽的地方冒犯了禮法。」
馬車停在佳鄰廣場上的紅十字旅社面前。小城裡所有的郊外都有一家和紅十字旅社相似的旅館,那兒有大馬廐、小臥室。在旅社的院子中央你能看見母雞在馬車下面啄食蕎麥,那些旅行推銷員的馬車上沾滿了泥。那全是一些古老的好旅社。在冬天夜晚,蟲蛀了的木陽臺在風中軋轢有聲。那些旅社永遠有許多人,許多聲音,許多食物。黑色的飯桌因為沾了加了酒和糖的咖啡或茶而變得黏黏的。蒼蠅停滿在厚厚的窗玻璃上,壞酒沾污了潮濕的餐巾。正如穿著中產階級衣服的田夫,那些旅社永遠帶著鄉土味,當街總有一個咖啡座,靠鄉野那邊有一個菜園。沙勒一下車就奔向劇院。他和_圖_書分不清前座,側廳、正廳和包廂,請人解釋了還是不懂。票房時他去經理室。他回到客店又回到劇院,這樣來回了好幾遍,走遍了全城,從劇院直到大馬路。
「好,快走,好好的玩!」
冬天很冷,太太復元得又慢,天氣好的時候,他就把她的沙發椅推到朝向廣場的那扇窗前,因為她現在很討厭花園,靠花園那邊的百葉窗也經常是關著的。她要把馬賣掉,從前她所喜歡的,現在她都討厭。她全部的思想都只限於照顧自己。她坐在床上用點心,按鈴叫女傭人,問她的湯藥煎好了沒有,或是和女傭人聊天。菜市場的屋頂上的雪把縷蒼白的、靜止的光線投射到臥室裡。然後就是下雨。艾瑪每天焦急地等待著必然重複發生的瑣事,而那事對她來說又幾乎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是「燕子」在夜間抵達。那時,客店老闆娘大聲叫著,其他的聲音回答著,同時,伊波利德拿著手提燈在車子裡找箱箱籠籠,像是黑暗中的一顆星。中午的時候,沙勒回來,然後又出去。接著,她喝一碗湯。五點左右,放學回家的孩子們拖著木屐在人行道上走,用他們的尺一個個地敲打窗板的響環。
「聖經裡也一樣……你知道,不止一處,有諷刺的……真荒唐的話語!」
畢內說:「我從前看過一齣名時『巴黎的頑童』的戲,其中有一個神經兮兮的老將軍,他攻擊一個顯赫之家的子弟,那子弟引誘了一個女工,那女工最後……」
然後,看見艾瑪穿著一件有四道滾邊的藍色綢衣裙,他又向她說:
有好幾次,沙勒問自己用什麼方法籌錢還這麼多債。他不斷地思索,想要想出一些權宜之計,例如向父親乞援或是賣掉一點什麼東西。但是他父親不會理睬他,自己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變賣。他感到情況很尷尬,只有不再去想那令人不愉快的事,責怪自己因此而忘記艾瑪,因為他的思想好像全屬於艾瑪。不一直想著艾瑪就像是偷了她什麼東西似的。
她沒有等羞紅著臉的費莉西特的回答,就帶著很難過的樣子說:
但是藥劑師為文學辯護。他認為戲劇是用來批判成見的。在娛樂的面具之下,戲劇宣揚道德。
「好傢伙!他們還有別的花樣呢!」藥劑師大聲說。
「沒有關係!」歐梅說,「我真奇怪,在我們這個時代,在這個光明世紀,卻還有人堅決地禁止一種無傷的精神娛樂,有時甚至是道德的,健康的,是不是,醫師?」
「我覺得妳和愛神一樣美麗!妳將在盧昂出足風頭。」
「沒有的事。」神父說。
布尼賢神父就是在那時候來看她。他問她的病情,告訴她一些新聞,在娓娓動聽的閑談中勸她信教。一看見他的道袍她就覺得心安。
雍維勒鎮並沒有事絆住藥劑師,他只是自以為該呆在那兒。看見沙勒夫婦動身的時候,他嘆了一口氣。
當談話好像是結束了的時候,藥劑師突然又說:
「那麼,妳是愛他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