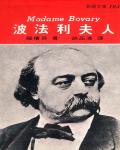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二部
15
一小口一小口地舐著滲糖酒調製成的冰棋淋的沙勒插嘴說:「可是大家都說在最後一幕中,他無懈可擊。我後悔在沒有結束之前就離開了,因為我正開始覺得有興趣。」
但是沙勒說他們第二天就要走了。
波法利問:「那紳士為什麼虐待她?」
從第一景起,他就激起了觀眾熱烈的歡迎。他把呂西緊緊地摟在懷裡,離開她,又回來,好像落入了絕望中:先是大發脾氣,然而又爆出悲歌似的呼號,充滿著無限的溫柔。音符從他赤|裸的喉頭逸出來,充滿著吻和嗚咽。艾瑪俯身看他,一面用指甲抓包廂裡的絲絨座位。她自己的心裡盛滿動聽的哀怨,那哀怨被低音樂器拖長,就像暴風雨之動亂中沉了船的人的呼喊。她體驗過那種陶醉和痛苦,她幾乎快要窒息。那女歌者的聲音就像是她意識的回聲,那令她著迷的幻覺也像是她們生活中的一部份。但是人間從來沒有誰用那種愛情愛過她。最後一夜,在月光下,何多夫沒有像艾德加那樣哭,當他倆互說「明天見,明天見」的時候。大廳裡充滿著喝采聲,全部的複奏又開始了。那對情侶說到他們墳墓上的花、誓言、放逐、命運、希望。最後,他們道別的時候,艾瑪尖叫了一聲,那尖叫和最後的顫音混成一片。
對方做了一個誠懇但毫不在乎的手姿,一面拿起帽子,一面說:
艾瑪解釋也是徒然。打從吉貝在對白中向主人陳述他可怕的陰謀開始,沙勒看見欺騙呂西的假訂婚戒指時,還以為是艾德加送來的愛情紀念品。而且,他承認不懂那個故事,那是因為音樂妨害了臺詞。
被侍女扶著的呂西正向前走來,頭上戴著一個橘花冠,臉色比她絲綢衣裙還更蒼白。艾瑪在想她結婚的那一天,她又看見自己在麥田間,在小徑上,當大家走向教堂。她為什麼沒有像臺上那個新娘那麼拒抗,為什麼沒有央求?相反地,她還滿高興的,不知道自己正奔向深淵……哎!假如,在她青春貌美的時候,在沒有被婚姻玷污的時候,在奸|情幻滅以前,她就把自己的一生託付給一顆偉大的、堅實的心的話,那麼她就不會從幸福的巔峰上摔下來,因為那時,貞潔、柔情、內慾、責任都混在一起。不過,那種幸福一定是一種謊言,為了欺編所有的慾望而編出來的。藝術家總是誇大熱情,她如今認識了熱情之卑劣。為了使自和*圖*書己不往那方面想,艾瑪只好在那幕歌劇(她自己痛苦的複製品)中看一種只是悅目的造型的虛構。她內心甚至帶著一種輕視的憐憫微笑著,當一個穿黑大衣的男人從舞臺深處的絲絨門下出現的時候。
「有話就出去講!出去講!」
他俯身向她的肩膀說:「那是因為我要知道我看的是什麼,妳明明知道。」
沙勒又說他不能離開太久,但是艾瑪可以留下。
「別說話!」正廳有人說,因為第三幕正在開始。
「是,幾乎窒息。走吧!」
那風景是森林中的一條十字路,左邊有一泓泉水,被橡蔭覆蓋著。一些農夫和紳士,肩上披著蘇格蘭大衣,一同唱著一首獵歌。隨即來了一位隊長,舉起雙臂向天,呼喚邪惡天使;另一位隊長又出現了,他們走了,獵人又重新唱歌。
「不要說話!不要說話!」她不耐煩地說。
「多久了?」
雷翁先生小心翼翼地為她披上她長長的花邊圍巾,他們三個人走向港口,在一家露天咖啡館的玻璃窗面前坐下。
他伸出手來,像紳士一般大方。波法利夫人也機械地伸出了自己的手,彷彿是受了強有力的意志的吸引。自從春季某天的黃昏,當雨打綠葉,他們站在窗口道別以來,她就不曾感到意志的存在了。但是,因為很快想起現在的情況需要她寒喧一下,她致力於搖落記憶的癱瘓,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短句:
「是……也許……有點太過份。」他回答,不太肯定地,一方面他領略著樂趣,另一方面他又尊重妻子的看法。
他又轉身向他太太說:「除非妳想一個人留下,我的小貓,嗯?」
但是,從那一刻起,她就不再聽歌劇了。賓客的合唱,阿施東和他男傭人的那一景,D大調的二重唱,這一切都遠去了,好像樂器的聲音轉弱了,人物也往後退了;她在回憶藥劑師家裡的牌戲,他倆一同去奶媽家那一次散步,涼棚下的閱讀,爐火旁的單獨面對。那一段可憐的、安靜的、久長的、含蓄的、溫柔的愛情,而她卻忘記了。他為什麼又來了呢?是什麼巧合又把他放到她的生活中?他站在她後面,肩靠著牆,他鼻孔裡呼出來的熱氣透進她的髮梢裡。在他的呼吸之下,她不時感到自己哆嗦著。
「你在盧昂?」
但是發瘋那個場面一點也不使艾瑪感到興趣。她覺得女演員的戲也太誇張了。
和*圖*書「但是他發誓要向她的家人報仇,當另一個人,剛才來到臺上的那個,說;『我愛呂西,相信她也愛我。』而且他和爸爸手挽手走了。那個帽子上有雄雞羽的醜陋的矮人是他父親吧?是不是?」
「明天六點鐘,講定了,是不是?」
「妳覺得不舒服嗎?」波法利問。
他做了一個姿勢,西斑牙式的大帽子就從他頭上落下來了。立刻,器樂和歌唱者開始了六重奏。冒著怒火的艾德加用他更嘹亮的嗓音蓋過別人。阿施東用低沉的聲音拿行凶的話激逗他,呂西唱出尖銳的悲歌,阿爾杜在一旁用中音歌唱,教士低沉的聲音像一架風琴,發出轟轟的聲音。同時,重複著教士話語的女聲又美妙地合唱起來。他們站在一排,做著手勢。憤怒、妒嫉、恐懼、慈悲、驚愕,全都同時從他們半張開的嘴裡吐出來。受了氣的愛人揮動著他赤|裸的劍,他的花邊領飾隨著胸脯的起伏而波動,他踏著大步左右行走,軟皮靴在腳脛的部位張開著,鍍銀的刺馬距打著地板,鏗然有聲。她想,他一定有用之不竭的愛情才能如此激|情地把愛傾注給觀眾。剛才她還有詆毀熱情的意願。如今,主角的詩情侵襲著她,那意願也隨著消失。人物的幻覺把她拉向那男主角,她試著幻想他,有聲有色的、不尋常的、華美的生活。她覺得自己也應該能過那種生活,假如機緣曾經許可。她和那歌者原會認識的,原會彼此相愛的!她原會和他一起在歐洲周遊列國,從一個首都到另一個首都,分享他的疲倦,他的驕傲,拾起別人扔給他的花,她將為他的衣服繡花。然後,每個夜間,在包廂的深處,在金欄杆後面,她原會張開著嘴,領受他靈魂的傾吐。他唱歌也只為她一個人而唱。當他演唱的時候,他也會從舞臺上望著她。但是一個瘋狂的念頭攫住了她:他正在望著她,的確!她真想奔向他,在他的體力之下獲得庇蔭,一如在愛情的化身中獲得庇蔭。她想向他說:「帶我私奔,帶我走,讓我們走!我所有的熱情,所有的夢都屬於你,屬於你!」
她回答:「不是虐待,他是她的情人。」
「好吧,妳想想看,我們看著辦。黑夜會帶給妳忠告。」
他的膚色有一種蒼白的美,蒼白的美把一點類似大理石的莊嚴賦予南方的熱情民族。一件棕色衣服緊束著他結實的腰身。一把彫
m•hetubook•com.com鏤小刺刀掛在左臀上,他轉動慵懶的眼睛,一面露出白牙。有人說,一天晚上,一位波蘭公主聽見他在比阿利茲海濱唱著歌修理帆船,就愛上了他,並且因他而破產了。他把她扔在那兒,又愛上別的女人,那件風流韻事反而提高了他在藝術上的名聲。在做廣告的時候,那懂得外交的伶人總會想到加上一個詩意的句子,來讀美他形體的魅力和心靈的敏感。美好的歌喉,挺拔的身軀,氣質多於智慧,誇張多於抒情,這一切終於提高了那藝人可讚賞的秉賦,其中既有理髮師的品質,也有鬥牛士的性格。
但是,四周的茶座空了,一個侍者來了,默默地站在他們身邊。沙勒明白了,於是拿出錢包。見習律師用手阻止他,付了帳,甚至沒有忘記在大理石桌面上多擲下兩枚雪白的硬幣,硬幣在桌面上敲得鏗鏘有聲。
他又加了一句:
艾瑪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結結巴巴地說:「我……我也不太知道……」
「猜猜看我在那邊遇見了誰?雷翁先生!」
出場的觀眾在人行道上經過,一面輕輕地哼著或是把嗓子揚得高高地唱:「啊,美麗的天使,我的呂西!」那時,雷翁以業餘者的身份開始談音樂。他看過丹布利尼.魯比尼.貝西阿尼。格利西。拉卡迪雖然聲名大噪,可是和他們比起來,根本算不了什麼。
「呀!你怎麼在這兒?」
「既然你在我們這個地區,我希望你常來我們家吃便飯。」
「其實,他不久還要再上演一次。」見習律師說。
「妳喜歡歌劇嗎?」他挨近她說,那麼近,他那八字鬍子的尖端輕拂著她的面頰。
幕落了。
沒有想到有這麼一個機會,那年輕人帶著希望馬上改變前言。他開始讚美拉卡迪的最後一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於是沙勒堅持了:
「啊,現在還不要去!」波法利說:「她的頭髮散開了,眼看就是一場悲劇。」
然後,他又向陪伴他們的雷翁說:
然後,音樂臺上的蠟燭點燃了。從天花板上垂下的懸燈,藉著無數的小水晶面,突然在大廳裡投下一片歡騰。然後,樂人陸續地進來,首先是一陣久久的低音樂器的喧噪聲,咯吱咯吱的小提琴的調弦,呼拉呼拉的喇叭,咪嗚味嗚的簫笛。但是舞臺上響了三聲,鐃鈸響了,銅樂器伴奏著,幕升起來了,露出一片風景。
為了害怕人家覺得他們可笑,在入m•hetubook.com•com場之前,艾瑪想在港口轉一圈。為了小心起見,波法利把兩張票拿在手裡,把手插在褲袋裡,並且按著肚皮。
「有什麼關係嘛?」艾瑪說,「不要說話!」
「是。」
波法利夫人又置身於少女時期的讀物中,完全是瓦爾特.司各特的氣氛。她好像聽見蘇格蘭風笛的聲音穿過霧層在紫荊棘上一再迴盪。而且,藉著對小說的回憶促成對唱本的瞭解,她一句一句地聽著故事,同時她不容捕捉的思維不久也在音樂的狂風暴雨中消散了。跟隨著樂曲的起伏,她覺得整個人也在顫動,好像小提琴弓是在她的神經上拉來拉去。她沒有足夠的眼睛去看服裝、佈景、人物、有人行走時就搖動的、畫成的樹木、絲絨小帽、大衣、劍器、以及這一切想像。這一切想像在和諧中騷動,你是在另一世界的氣氛中。但是有一位少婦走上前來了,把一個錢包扔給一位綠衣騎士。只剩下她一個人,那時傳來一陣笛聲,像流泉的呢喃或是鳥的啼囀。呂西用嚴肅的神情開始唱一首G大調的短歌,她抱怨愛情,要求翅膀。同樣地,艾瑪也想逃避生活,而且在情人的擁抱中飛去。突然,艾德加.拉卡迪出現了。
於是,他建議離開劇院,去什麼地方吃冰淇淋。
當他說完那句話的時候,雍維勒鎮從前那位見習律師已經進入了包廂。
煤氣味和呼吸混在一起。扇子搧出的風使空氣更悶。艾瑪想出去,走廊上擠滿了人,她又在沙發椅上坐下,帶著令她窒息的心跳。沙勒怕她昏倒,跑到飲料部為她弄來一杯大麥杏仁果汁。
「她叫得太響。」她說,一面轉向傾聽的沙勒。
她淡然地回答:
「好熱!」
然後,雷翁嘆著氣說:
「就是他!他就會來和妳打招呼。」
他說他一定會那樣做,因為他恰巧需要去雍維勒鎮為事務所辦事。天主堂的鐘聲敲響十一點半的時候,他們在聖艾布郎路分手了。
「雷翁!」
「啊!天!不太喜歡。」
沙勒輕輕地說:「真的,你不該付錢,這使我覺得不好意思。」
「天,我以為回不來了。人真多!人真多!」
觀眾靠看牆,對稱地分站在兩旁,關在兩排欄杆當中。在鄰街的轉角處,巨大的廣告重複著花花綠綠的字體:「呂西.德.拉梅木……拉卡迪……歌劇……」。天氣很好,大家都感到熱;汗在鬈髮裡流,人人抽出手絹擦拭紅紅的額頭。有時,河邊吹來一陣暖風,輕輕掀起咖啡館門前掛著的布幔。但是,再往下一點,人們就因冰涼的風而覺得涼爽,風中有羊脂味、皮草味,和油味。那風是從貨車街吹來的。那兒全是又大又黑的棧房,大桶在裡面滾來滾去。和-圖-書
他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因為他手裡拿著杯子,每走一步就有肘子碰到他。他甚至把四分之三的飲料倒在一個穿短袖的盧昂女人的肩上。那女人感到冷飲流到她腰部,像孔雀一樣叫了起來,好像有人想謀殺她。她丈夫是紡織廠的廠長,他向那個笨手笨腳的男人發火。當妻子用手帕拂拭她美麗的櫻桃紅緞子衣裙上的斑點時,丈夫則用粗暴的聲音說要賠償費。沙勒終於回到了妻子身邊,喘著氣向她說:
劇院就要客滿了。大家把望遠鏡從套子裡抽出來。長期訂戶彼此遙望,互相打招呼。他們耽心貨物的銷路,到藝術中尋找排遣,但是仍然忘不了「生意」,仍舊談著棉花,酒精或靛青。你能在劇院裡看見一些沒有表情的、平平靜靜的老人。他們的頭髮和皮膚全是淺白的,就像因蒸氣而失落了光的銀質獎章。正廳裡有美少年傲然而行,在背心的開口處展示他們粉紅的或蘋果綠的領帶。他們用戴著黃手套的手掌貼在有金柄的手杖上,波法利夫人從樓上欣賞他們。
大家轉過身來望著他們,他們只好不說話了。
她一走進過廳心就跳起來了。看見人群由另一個過廳向右奔去,她卻踏上包廂的樓梯,她不自禁地因虛榮心之滿足而微笑了。用手推開蒙著氈子的大門時,她像小孩一樣快樂,她用力吸入甬道中的灰塵氣息。在包廂裡坐下了以後,她向後仰著,從容不迫,好像一位公爵夫人。
「妳星期天回去好了。哎!打定主意嘛!假如妳覺得對妳沒有好處,妳就錯了。」
「對,無法忍受!」
首先,他們談她的病,雖然艾瑪不時打斷話題,她說那是為了怕雷翁先生嫌煩。後者說他來到盧昂一家出名的律師事務所實習兩年,因為在諾曼第執行業務和巴黎大不相同。然後他問起貝特,歐梅一家人,勒佛杭絲瓦太太。因為丈夫在場,他和艾瑪不再有什麼好說的,於是結束了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