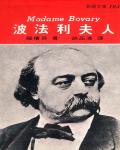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三部
1
面對著那種畏怯,艾瑪彷彿有點害怕,對她來說,畏怯比張開雙臂走向她的何多夫還更危險。在她的感覺中,從來沒有過一個比他更美的男人。他的舉止中有一種美妙的坦率,他垂下長長的、彎曲的睫毛。她想他細皮嫩肉的臉因慾望而羞紅著。艾瑪覺得有一股不可克服的意欲:吻他的臉。於是,好像為了想看時間,她俯身向鐘:
「我的上帝!這麼晚了!我們只顧談話!」
「哎,雷翁!……我不知道我是否該……」她先是嬌聲嗲氣,然後便帶著一本正經的樣子。
「至少也該從北門走,可以看看『復活』、『最後審判』、『天堂』、『大衛王』以及地獄火焰裡的罪人。」
「誰阻止我們重頭來過?」
「但是不會像愛妳這樣愛她們。」他說。
波法利夫人把頭轉開了,為了不讓他看見她唇上那不可抗拒的微笑,她自己正感到那笑意升起。
「你願不願意……」
站在一旁的門警心裡很生那個年輕人的氣,他居然自由自主地一個人欣賞那座教堂。他覺得他行為不軌,有點像盜竊,幾乎是褻瀆聖靈。
馬車又走了回頭路,那時,既無主見也無方向,只是任馬所往。它徘徊在聖・波勒,在雷古何,在卡爾剛高地區,在紅沼,在美林廣場,在馬拉德何利街,在迪內昂徳何利街,在聖・何曼面前,在聖・維維安面前,在聖・馬克路面前,在聖・尼格斯面前,在海關面前,在下老塔,在三煙斗,在紀念墓園。馬車夫不時從座位上向酒店投下絕望的目光。他不明白是什麼原因驅使那兩個顧客不停地向前。他試著停了好幾次,每次停下他就聽見後面傳來一陣忿怒的叫聲。於是,他使勁鞭打那兩匹流汗的羸馬,但是不提防顛簸,這裡一撞,那裡一碰,一點也不在乎。他垂頭喪氣,又渴又倦又傷心,幾乎快要哭了。
「這塊石板蓋著的是比耶・德・布黑塞,他從前是拉法倫和布利薩克的封建領主,是波阿都的大元帥,諾曼第的總督,一四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死於孟雷利之役。」
於是,他把頭從她肩上向前伸,像是在她眼中尋求同意。她的眼光落向他,充滿著冰冷的莊嚴。
「不是。」對方說。
「啊!對不起。」他說,一面往後退。
雷翁一面咬嘴唇,一面蹬脚。
她好像在想,然後急促地說:
他一面不停地說,一面把他們推向一個堆滿了欄杆的側殿,移動了幾根,露出一塊石頭,那可能是一個雕壞了的石像。
她說:「我很想在一家醫院做女修士。」
「不,我的朋友,」她回答說,「我太老了,你太年輕……請忘記我!有別人會愛你,你也會愛她們。」
車夫問:「先生去哪兒?」
她點了點頭,像鳥一般飛進旁邊的屋子。
「因為我曾經狂熱地愛過妳!」
「先生不在。」一個傭人說。
「什麼事?」
「太太大概不是本地人吧?太太想不想參觀敎堂裡的珍品?」
雷翁逃避著。因為他覺得他的愛情,差不多兩小時以來曾經在敎堂裡變得和石頭一般靜止的,如今要煙消雲散了,從那個像長方形籠子似的煙囱口裡。那煙囱在敎堂上面以一種很奇怪的方式橫七豎八,像是一個古怪鍋匠的怪主意。
「最可悲的就是像我這樣過著一種徙然的生活,是不是?假如我們的痛苦能對什麼人有點用處,那麼,就算是犧牲也會是一種安慰!」
她說:「可是,對不起,我錯了!我老是抱怨,使你心煩。」
「真的嗎?」雷翁說。
馬車沿著河流,在鋪著石子的拉縴路上奔去,久久地,靠著島外的歐瓦色那邊走去。
屋頂,圓拱的起點和一部份的玫瑰花玻璃窗映在聖水盆裡。但是圖畫的反光在大理石盆的邊緣上折斷了,彷彿一塊彩色地氈在較遠的地方攤開。外面的日光從三扇敞開著的門射進來,在教堂裡形成三道巨光。在教堂深處不時有一位教士走過,他也和匆忙的信徒一樣斜斜地跪了一下。從天花板上垂下來的水晶吊燈一動也不動。唱詩班所在的地方點著一盞銀燈。由側殿裡,由教堂陰沉的角落裡,和圖書不時發出像嘆息的聲音。同時一道鐵柵門關上的聲音在高高的圈拱屋頂下迴盪著。
她又說,一面把含著眼淚的美麗眼睛望向天花板:「假如你知道我曾渴望過的一切!」
雷翁用嚴肅的步伐沿著牆走。對他來說,人生從來不曾像現在一般顯得那麼美麗過。她一會兒就要來,艷麗、慌張、擔心著後面追蹤她的目光——穿著多疊的衣裙,掛著金邊眼鏡,穿著小靴。還有他從來不曾領略過的華麗衣飾,以及即將屈服的貞操,那屈服有不可描述的誘惑力。教堂在她四周展開,像一間巨大的閨房,圓拱著腰,為了在陰影中收集她愛的供認。玻璃窗發著光,為的是照亮她的面孔。爐香即將點燃,為了讓她在香煙繚繞下像天使一般出現。
「她有點像你。」
「為什麼要人用護腳毯包著你安葬?」
於是,他們互相訴說及那一段遙遠生活中的小事件,那段生活中有歡笑也有憂戚,他們剛才只用了一句話就概括了那些歡樂和哀愁。他追憶牡丹蔓的架子,她穿過的衣服,她臥室裡的家具,她整個的屋子。
站在門檻上的門警大聲向他們說:
艾瑪微微聳了一下肩膀,打斷了他的話題,抱怨她的病,她說在那場病中幾乎死去,可惜並沒有!假如死了,此刻就不會有痛苦。雷翁立刻羨慕「墳墓的寧靜」,而且有一天晚上,他甚至寫了遺囑,叫人把他葬在她送給他的那條美麗的絲絨護腳毯子裡。他們原就希望曾經那樣活過,各自有一個理想,依據那個理想,調整他們過去的生活。
「還太早。」他想,一面向理髮店裡的時鐘望去,才九點。
當他試著重新拾起被打斷了的話題時,她向他說:
它走下大橋街,穿過了藝術廣場、拿破崙碼頭、新橋,猝然停在比耶・柯乃依的雕像前面。
他覺得那是吉兆。他上了樓。
她好像準備讓他一個人說話而不插嘴。她低著頭,交叉著雙臂,端詳著繡在拖鞋上的玫瑰花,腳指不時在鞋緞裡做點小小的動作。
第二天,雷翁打開了窗子,在陽臺上,一面哼著歌,一面擦自己的皮鞋,塗了好幾層油。他穿了一條白褲,一雙很細的襪子,一件綠色禮服,把所有的香水灑在手帕上。然後,因為把頭髮弄得太鬈了,他又把頭髮弄直,使頭髮有一份自然美。
但是,關於他編出來的那個有關護腳氈的故事,她問:
然後,雷翁一面用眼角窺視她的面部表情,一面因突破了難關而為自己喝采。
「很不應該,你知道嗎?」
「啊,我猜到了。」雷翁說。
但是,雷翁急忙地從口袋裡掏出了一枚銀幣,又抓住艾瑪的胳臂,門警感到十分驚訝,因為不明白這種不得體的賞賜。還有許多東西要讓陌生人看呢!所以他提醒他:
然而,經過三年的別離,再看見她的時候,他的熱情又甦醒了。他想,必須下定決心佔有她。而且,由於經常和輕佻的女伴在一起,他已不再畏怯。當他再來到外省的時候,他輕視一切不用亮晶晶的皮鞋踩柏油大馬路的人。在一個穿花邊衣服的巴黎女人身邊,在一位名醫(有勳章有馬車的人物)的客廳裡,那可憐的見習律師也許會像一個孩子那樣發抖,但是在盧昂港口上,在那小醫生的妻子面前,他自覺十分泰然,事先他就能肯定可以唬住她。信心要看環境:在五樓的人說話和在地下室及底樓之間的人說話不一樣。富裕的女人,為了保護貞潔,用所有的鈔票包圍著自己,像緊身上衣夾縫裡的甲冑一樣。
「隨便。」雷翁說,一面把艾瑪推進車裡。
那孩子像皮球一樣奔進了四風街,他們單獨地面對了幾分鐘,有點窘。
嚮導繼續說:
他認出了是門警。原來那門警腋下夾著二十來本大大的平裝書,此刻用肚皮頂著那些書,使它平衡,全部都是有關敎堂的論述。
佳鄰區有許多寄宿舍,教堂和荒涼的大旅館。那時,鐘聲傳來了,正是八點。他們不再說話了。但是,當他們互相凝視的時候,他們感覺到腦子裡有hetubook•com.com輕微的聲音,好像有什麼聲響從他們凝定的瞳仁中逃逸出來了。如今他們手握著手,過去、未來、回憶、夢幻全都在狂喜的溫柔中混在一起。暮色在變濃,牆上掛著四幅版畫:內勒塔四景。版畫下部有西斑牙文和法文的說明。那四幅畫的粗俗的顏色在陰影中朦朧,但是依然發著亮。從嵌入壁櫃內的窗口,他們看見天空的一角,在一些尖屋頂之間。
那種迷信的宗教狂熱使那年輕人生氣。然後,他又感到一種魅力——看她在幽會的時候像西班牙昂達魯西地區的侯爵夫人一樣迷失在禱文中,然後他又立刻感到厭煩,因為她沒完沒了。
因為他們是站著的,艾瑪低著頭,他在她後面,他俯身向她的脖子,久久地吻著。
雷翁快速地把雙唇貼在她手上。深深地呼吸了以後,他又說:
「先生一定不是本地人吧?先生是不是想看教堂裡的寶物?」
「不要!」
他向雷翁迎面走去,帶著哄騙的、和善的微笑,像教士問小孩子話的時候泛起的那種微笑:
「為什麼?」
他深深地嘆息著說:「從前,那石像裝飾過獅心李沙(諾曼第公爵兼英皇)的墳墓。先生,都是宗教改革家卡萬的信徒們把那石像弄成了這個樣子。由於壞心眼,他們把石像埋在地裡,在大主教的寶座下面。瞧,這就是通向大主教住宅的門。現在我們去看畫著聖人何曼除毒蛇之害的玻璃窗。」
「在那段時間裡,對我來說,妳是我所不知道的一股不可瞭解的力量,那力量囚禁著我的生命。比方說,有一次我去了妳家,妳一定忘了。」
可是馬車老是不來,雷翁怕她又走進敎堂。終於,馬車來了。
「可憐的朋友!」她說,一面握住他的手。
他等她說話。她終於回答了:
「好吧!」
「那個跪在他身邊哭泣的女人是他的妻子——荻安・徳・波阿紀葉,布里塞地方的伯爵夫人,瓦郞丁諾阿地方的公爵夫人。她生於一四九九年,死於一五六六年。左邊那個抱著一個孩子的是聖母。現在,你們向這邊看。這是昂布阿斯一家人的墳墓。他們全做過紅衣主敎和盧昂城的大主敎。這一位做過路易十二的大臣,給了禮拜堂許多好處。他在遺囑裡說留三萬金幣送給窮人。」
「不,因為你不是女人。」
然後,一面輕輕地撫弄著她那白色長腰帶的藍鑲邊,他又說:
「多麼美好的夢!」雷翁喃喃地說。
「我們去看別的!」雷翁說。
門警正好站在左邊的門檻上,在跳舞的瑪莉安下面,頭上是羽盔,脛上是長劍,手心上是柱杖,他比紅衣主教還要莊嚴,像聖杯一樣發光。
可是,他怕被人看見,毅然走進了教堂。
「謝了!」雷翁說。
那是一個美麗的夏天早晨。銀樓裡的銀器閃耀著,斜射在教堂上的太陽使灰色石頭的裂縫閃爍不已,一群鳥在藍空中,圍著飾以苜蓿花的鐘樓飛翔。廣場上迴盪著呼叫聲,發出花香,廣場所在地四周放著玫瑰、茉莉、石竹、水仙、玉簪,那些花被一些濕草、小薄荷和餵鳥用的蘩蕗不等距離地隔開著。噴泉在中央嘩嘩地響,有些賣花女在大傘底下,在砌成金字塔形的西瓜之間光著頭用紙包紮紫羅蘭花。
然而,她嘆氣了。
為了表現自己,或是天真地模仿這種感染他的憂鬱,那年輕人說在求學時代他感到非常無聊。法律激怒hetubook.com.com他,一些別的興趣吸引他,母親在每封信裡都折磨他。他倆各自都能愈來愈精確地說明他們痛苦的原因,他們互相傾訴衷曲,也漸漸地因而感到興奮。但是當他們在陳述他們的觀念時,他們就停住,而且尋覓一個能表達那個觀念的句子。她不向他承認她曾經熱愛過另一個男人,他也不說曾經忘記過她。
他明白了她的暗示,找他的帽子。
艾瑪在祈禱,或者不如說她在努力祈禱,希望有個猝然的決心從天降落。為了央求上天援助,她讓眼睛裡充滿神龕的輝煌,她吸進大瓶子裡盛開著白葇莄花的芳香,聆聽敎堂的沉靜,而敎堂的寧靜只徒然增加她內心的紊亂。
馬車立刻再上路,經過聖・色維、古杭迪耶碼頭、磨坊碼頭,又一次經過橋,經過戰神廣場,到了醫院的花園後面,那兒有穿黑衣的老年人在散步,在陽光下,沿著一個被長春藤覆蓋的陽臺。馬車又走上布伏何衣大道,走過戈施瓦斯大道,走上整個的利布徳高地,直到德維勒那邊。
「明天十一點,在教堂。」
雷翁在巴黎讀法律的時候,經常去光顧大茅舍舞廳。在那兒很受女侍們的歡迎,她們覺得他風度高貴。他是最循規蹈矩的學生,頭髮既不太長也不太短,他不寅吃卯糧,和教授們也處得很好。由於斯文,也由於優柔寡斷,他從來不讓自己做太過份的事情。
他又說:「我常給妳寫信,然後又撕掉。」
雷翁退了三步,打算走了。他在門檻上站住,然後用顫抖的聲音輕輕地說:
「先生你應該看看,那鐘樓有四百四十尺高,比埃及的金字塔只矮九尺,上下全是鐵……」
「妳在樓下,在候客室裡,正打算出去,走在臺階上。……妳戴著一頂有小藍花的帽子,妳根本沒有邀請我,我不由自主地就陪著妳走。而每分鐘,我愈來愈覺得我傻,我繼續走在妳身邊,既不敢緊跟著妳,也不願離開妳。當妳走進一家店鋪的時候,我就站在街上,隔著玻璃窗看妳脫下手套,在櫃臺上算錢。然後,妳按了杜法施家的門鈴,有人為妳開了門,我像一個傻瓜似的站在那笨重的大門口,門又在妳後面關上了。」
「先生!」
她這樣說是認真的嗎?艾瑪自己也一定不知道,因為她心裡就只有兩件事:誘惑的魔力和自衛的必要。她一面用溫柔的目光凝視那年輕人,一面輕輕地摒拒他那顫抖的手畏怯的愛撫。
波法利夫人拿起了眼鏡。雷翁一動也不動地望著她,甚至不再試圖說一句話、做一個手勢。面對著她的饒舌和冷漠的雙重決心,他覺得非常失望。
「隨便妳。」
「我們可憐的仙人掌到哪兒去了?」
「我有時幻想著,一個偶然的機會能使妳我重逢。我曾以為在街角上認出了妳,凡是門上飄著一條像妳的披肩的馬車,我都跑去追趕。」
「啊!我能想像得到……」
他讀了一本舊時裝雜誌,抽了一枝雪茄,然後走了出去,走了三條街,覺得是慢慢走向聖母院門前廣場的時候了。
然後,六點左右,馬車停在佳鄰區的一條小街道上。一個女人從馬車裡走了下來,面紗拉得低低的,頭也不回。
那像是風起雲開見天日。使她倆憂鬱的悲思從她的藍眼中消失,她變得容光煥然。
「在哪方面?」見習律師說,「在巴黎,大家都這樣做。」
「啊,別開玩笑!夠了,夠了!請可憐可憐我,讓我再見妳一面……僅僅一面。」
「啊,不,不能在這兒!」
「右邊那位穿一身鎧甲,騎著一匹踢後蹄的馬的紳士是他的孫子路易・徳・布黑塞;他從前是布何法和蒙壽維的封建領主,摩勒佛內耶的伯爵、摩尼的男爵、御前大臣、榮譽騎士,也同樣地做過諾曼第的總督。正如碑文所說的,他死於一五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天。下面刻的那個正準備往墳墓裡走的那個人就是他。把虛無表現到這種境界是不能再好了,是不是?」和*圖*書
她向自己說:「他會來的,我親手交給他。」
「可是我還要見妳,」他說,「我有話同妳講。」
她向他解釋他們之間的愛情之不可能,說他們應該和從前一樣,保持單純的友誼。
「怎麼?……」她回答。
「我早就知道……」
「走呀!」車裡有一個聲音說。
「你真是個小孩!好的,你真乖!我要你乖!」
於是,為了「依著順序看」,門警把他們帶到靠近廣場的入口處,用手杖指著一個黑石大圓圈,沒有銘文的,也沒有彫飾。
可是,她還是沒有來。他站到一張椅子上去,看見一塊藍色的玻璃窗上有提著籃子的船夫。他久久地凝視那塊玻璃窗,專心地。他數魚鱗和甲冑的鈕孔,而思想則在漫遊,尋找艾瑪。
那笨重的馬車出發了。
但是,馬車忽然一躍而馳過四塘、傻城、大堤、厄爾伯街,在植物園面前又停了下來。
「真的。」
「是的,」她說,「我的決定是一項錯誤。當一個人有做不完的事的時候,不該習慣於尋樂。」
「不,直走!」同一個聲音說。
馬車又繼續走,打從拉法耶十字路口起,就直往下奔,馬放開了蹄子,駛進火車站。
但是男人也有他們的煩惱,於是他們的談話中增添了哲學意味。艾瑪大談其人間愛情的痛苦以及永恆的孤立,內心永遠陷入孤立中。
他首先沿著教堂中央兩側的通道轉了一圈。然後又望向廣場。艾瑪沒有來,他一直走到唱詩斑所在的地方。
然後,他用一種顫抖的聲音說:
他回答說:「哎,男人沒有這種聖職,任何地方都沒有一種什麼神聖的職務……也許,除非做醫生。」
「笨蛋!」雷翁嘀咕著,一面衝出了敎堂。
晚上,艾瑪寫了一封沒有寫完的信給見習律師取消約會:現在,一切都完了。為了他們的幸福,他們不應該再見面。可是,當她把信封了口以後,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她不知道雷翁的地址。
「去年冬天凍死了。」
他開始歌頌道德、責任,和默默的犧牲,因為他自己也有一種難似置信的需要:對誰奉獻自己,可是他無法滿足那種需要。
「我會去。」他說,一面握住她的雙手,她掙脫了。
當他呆在臥室裡唸書,或夜間坐在盧森堡公園的菩提樹下的時候,他又會想起艾瑪。漸漸地,那份情感轉弱了,上面積聚著其他的欲望,因為雷翁並沒有放棄全部的希望,那感情仍然透過別的貪欲一直持續著。對他來說,有一個不確定的承諾在未來中搖盪,像一枚掛在奇異枝頭上的金果。
她不回答。他繼續說:
機會已經錯過了,因為第二天她就要動身回家。
馬車走出了柵欄門,不久來到了林蔭大道,放慢步伐,走在高大的榆樹之間。馬車夫拭了一下額頭,把皮帽子放在雙膝之間,把馬車推到橫街之外,靠著河邊的草地。
但是石板地上有絲裙的簌簌聲,有帽子邊,有黑色短大衣……是她!雷翁站起來,向她奔去。
「妳決定留下了?」他又說。
「有時,我也想過。」她說。
「走嘛!」那聲音更氣忿地叫著。
「哎!我曾多麼想念它們,妳知道嗎?我常常看見它們和從前一樣,當夏天早晨太陽照書百葉窗的時候……我也看見妳赤|裸著雙臂從花間穿過。」
在港口,在貨車及木桶之間,在街角的界石旁邊,中產階級人士瞪圓著眼睛,驚訝地望著那個在那兒不常見的東西:一輛垂下了簾子的馬車,不停地走著,比墳墓還要和_圖_書嚴密,像船一般搖晃。
一個小男孩在敎堂門口的空地上玩。
「去替我叫一部馬車來!」
也許他已經忘了舞會以後和女孩子吃晚飯的情形,她也不記得她從前的幽會,當她早晨在草地上走向情人的城堡。城裡的喧囂聲幾乎傳不到他們的耳邊,臥房顯得很小,像是故意的,為了能把他們的寂寞更緊密地連在一起似的。艾瑪穿著一件條紋布的浴衣,髮髻靠著舊沙發的椅背。黃色的壁紙像是她後面的金色背景,她沒有戴帽子,鏡子反映著中分頭髮的那條白紋路,以及露在兩邊頭髮外而的耳梢。
見習律師說:
年輕人買了一束紫羅蘭。這是他第一次買花送給女人。聞那些花的時候,他心裡充滿了驕傲,好像對那個女人的敬意變成了對自己的敬意。
「怎麼?……」雷翁說。
「可是,你瘋了,啊,你瘋了!」她一面說,一面發出響亮的笑聲,而吻也越來越多了。
那句話像一種不可駁斥的理論,使她下定了決心。
「明天見。」
「我們去哪兒嘛?」她問。
艾瑪臉色蒼白,走得很快。
「為什麼不?」她說。
他莊嚴地說:「這是昂布瓦斯大鐘的鐘口,重約四萬磅。全歐洲沒有第二個,鑄鐘匠一完成就高興而死了。」
「一件又嚴正又認真的事。而且,不,妳不能走,那不可能!假如妳知道……妳聽我說……難道妳不明白我的意思?難道妳沒有猜到?」
見習律師說理想的天性是不容易瞭解的。至於他,他對她是一見鍾情。一想到他們原可能有的幸福他就絕望。假如機緣曾經讓他們早點相逢,他們原可能終生相愛,永不分離。
「先生,鐘樓,鐘樓!」
「不,決不,決不。」
他說是直覺引領他走向她。她微笑了起來,為了挽救他剛才那句傻話,雷翁立刻說他費了一個早晨在城裡每家旅社找她。
五斗櫃上有兩枝蠟燭,她站起來點蠟燭,又坐了下來。
看見他來,她並不慌亂,相反地,她請他原諒因為忘記了告訴他住在哪裡。
「而我呢!我也受夠了苦。我經常外出散步,沿著河岸徘徊,在嘈雜的人群中胡鬧,但是卻不能擺脫糾纏我的思想。大馬路上有一家版畫店,那兒有一張義大利版畫,刻的是詩之女神繆司。她披著一件希臘式長袍,望著月亮,散開的頭髮上插著一束玻璃草花。似乎有什麼東西不斷地把我引向那版畫店,我在那兒一呆就是好幾個小時。」
第二天五點左右,他走進了旅社的廚房,喉頭很緊,面頰蒼白,像一個壞蛋下了決心幹到底。
聽他說話的時候,波法利夫人覺得很奇怪:自己已經那麼老了.這些再現的事物好像使她的生活變得廣闊,那像是遼闊的情感空間,她又回到其中,她半閉著眼,不時低聲說,「是,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
「什麼話?」
她打住了,然後又像是改變了意思:
「我甚至忘了歌劇!可憐的波法利特別讓我留下就是為了去看歌劇。住在大橋街的洛爾摩先生該送我和她太太去劇院的。」
當她正要站起,當他們正要走的時候,門警急忙走過來問:
前夕離開波法利夫婦的時候,雷翁在街上遠遠地目送他們。看見他們停在紅十字旅社以後,他就回頭,費了一整夜去作一個計劃。
「可是,你很會說話。」艾瑪說。
有一次,在鄕野間,當正午的太陽強烈地照著古舊的鍍銀馬車燈時,一隻赤|裸的手從黃帆布小帷幕下伸了出來,扔掉撕碎了的紙片,那些紙片迎風散開,遠遠飄去,像白蝴蝶一般落向一片盛開的紅苜蓿中。
「我記得,」她說,「說下去!」
「怎麼猜到的?」
雷翁不回答,繼續迅速地走。當波法利夫人正把手指浸浴在聖水裡的時候,他們聽見後面有一陣沉重的喘息,夾著有規律的手杖聲,雷翁回過頭。
因為她要用搖晃的貞節抓住聖母,抓住雕刻,抓住墳墓,抓住一切機會。
他遲疑了一會兒。
「怎麼直到現在從來沒有人向我表達過這種情感?」
門警又開始走;再回到聖母殿以後,他伸出雙臂做個綜合示範姿勢,而且比一個給你看果木的鄕下地主還要驕傲。
「你看吧!」她說,一面遞給他一張紙。「啊!不要這樣。」她急忙縮回她的手,為了要走進聖母教堂,她靠著一張椅子,開始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