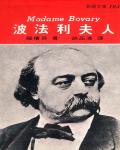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三部
2
「我也不是完全反對那本書!作者是醫生。其中有些科學方面的常識是一個男人最好能知道的,而且我敢說是應該知道的。然而不是現在,不是現在!至少等到你成人以後,等到性情穩定以後。」
「太太,妳立刻去歐梅先生家!有急事。」
艾瑪讓他說。兩天以來,她煩死了。
這時,艾瑪轉向歐梅太太說:
阿達莉拉著他的大衣說:
同時,她回答了:「是,我知道,我知道。」
「他甚至不再想到那件事!」她向自己說,一面望著那個可憐人。汗珠從他茂密的紅頭髮上流下來。
他把帽子拉下了,蓋著眼睛,雙手放在背後。他一面微笑,一面輕輕地吹著口哨,他正視著她,帶著不可忍受的樣子。他是否懷疑什麼?她茫然了,迷失在形形色|色的恐懼中。可是,最後他還是說了:
「是的,」她漠然地說,「是我剛才向一個女乞丐買的。」
「不!別碰那本書。」歐梅說。
「五十八。」
艾瑪忘了要問他為什麼要她到這兒來,藥劑師繼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波法利在錢包裡找一枚小錢。對他來說,那個站在那兒的男人的在場是一種羞耻,是一種譴責的化身(對他不可挽救的無能的譴責),而他卻好像是不懂。
沙勒臉紅了,直到耳根。
歐梅太太說,一面雙手合十:
「哎!我的上帝,」那好心的女人帶著傷心的樣子插嘴說:「我該怎麼告訴妳才好呢?……真是不幸!」
「我們和好了,我現在又有一個新的建議。」
是的,老波法利先生前天從飯桌上站起來的時候,突然因中風而死了。波法利先生過份擔心艾瑪敏感,請歐梅先生慢慢地把那個壞消息向她透露。
他抓住雨斯丹的衣領猛搖,從口袋裡搖出了一本書。
「是的,儲藏室的鑰匙!鎖苛性鹹和酸的鑰匙!去拿一隻後備鍋,一隻有蓋的鍋!我自己也許永遠不用的一隻鍋!在我們醫學微妙的運用上,一切都有各自的重要性,好傢伙!我們必需分清涇渭,藥學上的東西不能挪到家庭使用。那好像是用手術刀殺雞,好像一位法官……。」
但是,婆婆一走,艾瑪立刻表露出現實的一面,令沙勒感到驚訝。必須多方打聽,研究抵押的東西,看看是否需要拍賣或是清算。她偶而引證術語,說出「程序」、「未來」、「先見之明」等堂皇的字樣,而且常常誇大繼承的困難。有一天,她索興把一張樣本委託書拿給他看,其中是授權處理下列事務:「委託代理人處理業務,辦理貸款,簽署一切字據,償付一切款項等等。和圖書」她聽從了勒何的指示。
「親愛的,妳可不可以……?」
他不希望母親知道借據的事,因為怕她責備。
一坐到自己的角落裡,她就閉上了眼睛,只在到了山脚下的時候才再張開。在山脚下,她遠遠地看見了費莉西特,後者站在鐵匠鋪前瞭望。伊維勒住了馬,那女厨師踮起脚來,在車窗口神秘兮兮地說:
她好像懂了,因為她站了起來,沙勒向母親說:
孩子們叫起來了,好像他們已經覺得肚子非常疼。
「可是你……」
孩子們想看圖。
「可是妳明明知道嘛!」勒何說,「就是為妳的那些小把戲,那些旅行盒子。」
「我……不知道。」
突然,他們看見布商勒何從柵欄門進來了。
「除非雷翁……」沉思的沙勒回答說。
一刻鐘以後,他又加了一句:
「你爹多大年紀?」
「怎麼了?出了什麼事?」波法利夫人問。
「出了什麼事?」藥劑師說:「我們在煮水果做果醬,但是湯太多了,就要滿出來。我叫他去拿另外一個盆子來。而他,由於缺乏意志力,又懶惰,他去了我的實驗室,把儲藏室裡掛在釘子上的鑰匙拿來了。」
回到旅館的時候,波法利夫人感到驚訝,因為沒有看見馬車。等了她五十三分鐘的伊維終於走了。
「還好。」
他曾經推敲他的措詞,使語句變得委婉、文飾而有節奏。那是一篇傑作,謹慎而有步驟,語法也優美含蓄。但是憤怒趕走了修辭學。
沙勒想著父親,他從前以為他不怎麼愛父親,現在因為覺得那麼愛他而感到驚訝。老波法利太太想著丈夫。從前最壞的日子又顯得是可羡慕的。相處久了已經成為習慣,如今在本能的惋惜下,怨恨也就消失了。不時,當她做針線的時候,一大滴眼淚沿著鼻子流下,停留片刻。艾瑪想:四十八小時以前,她和雷翁還在一起,遠離人群,在陶醉中只恨沒有足夠的眼睛彼此相望。她試著再捕捉那過去了的一天的最不可覺察的細節。但是在場的丈夫和婆婆卻妨礙了她。她希望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只靜靜的追憶她的愛情。不論她做什麼,那份愛情因外在的感覺而漸漸消失。
「沒有什麼!也許是家裡的一些小事。」
「他甚至最好讓什麼人分擔,比方說,讓妳。妳有代理人的權利也方便多了。那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在一起做點小生意……」
他們出去了。
她再也沒話可說了。
艾瑪不想聽細節,離開了藥房,因為歐梅先生又謾罵起來了。然而,他還是平靜了,現在只是用父https://m•hetubook•com•com親似的口吻嘀咕,一面把希臘帽子當扇子搧著。
第二天,她就搭乘了「燕子」,去盧昂向雷翁先生請教。她在盧昂呆了三天。
然而,他卻壓抑住自己的痛苦,問她:
僕人結結巴巴地說:
他們聽見一根棍子的乾硬聲音在過道的地板上響起。是伊波利德把夫人的行李拿來了。他用假腿使勁畫了一個四分之一的圓才好不容易把行李放下了。
艾瑪把信還給了他。吃晚飯的時候,為了識大體,她裝出一副吃不下的樣子。可是,因為他的勸說,她就下決心吃了,而面對她的沙勒一動也不動,看來很疲倦。
「對了,太太,妳的公公死了!」
他不時抬起頭,久久地望著她,目光中充滿了憂傷。有一次,他嘆了一口氣:
他首先用大步子踱起方步,用手指挾著那本書,轉動著眼睛,像是窒息,又像是中風,又像是患了水腫,然後走到他的學徒面前,交叉著雙臂,往前一站:
「夫婦……之愛!」他慢慢地把四個字分成兩組唸。「啊!好極了!好極了!很美!還有圖!啊!太過份了!」
「妳真好!」他說,一面吻她的額頭。
「非常抱歉,」他說,「我想私下說幾句話。」
歐梅太太走上前去。
他給她看母親報喪的信,文字之間不帶任何虛偽的傷感。她唯一的遺憾是丈夫沒有受到宗教的超渡,因為他在雍維勒一家咖啡館和退役軍官舉行愛國聚餐。飯後倒在門檻上就死了。
「我現在非常後悔照顧了你!我原就該把你留在貧苦中,留在爛泥裡,我確信那樣做會好得多。你永遠只配看守牲口!在科學方面你沒有一點特長!你幾乎連標籤都不會貼!而你在我這裡,像一位牧師,像一隻啄食的雄雞,除了吃還是吃!」
然後,他低聲說:「你知道……是關於那件事。」
他慢慢地彎下身子吻她。但是,一接觸到他的嘴唇,她想起了另一個男人,哆嗦著摸摸臉。
但是書信難以達意。她建議自己去一趟。他婉謝了。她堅持要去。兩人客氣了半天。最後,她假裝生氣地說:
「昨天玩得好嗎?」
「他們叫我來……」
「出去!」他暴躁地說。
他要延長波法利簽的借據。不過,「先生」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不必折磨自己,尤其是他現在將有許多「困境」。
「哎!親愛的!……」
沙勒拿起那束紫羅蘭,一面拂拭哭紅了的眼睛,一面小心地聞。她急忙地從他手裡把花拿過來,插在一杯水裡。
「啊!」
「啊,是……」
她
和圖書沒有說完。藥劑師又吼了起來:拿掉了桌布以後,波法利沒有站起來,艾瑪也沒有。她望著他,那單調的景象漸漸地把惻隱之心從她心中剔除了。他顯得萎縮、軟弱、無能,總之是一隻可憐蟲,從任何方向來說。怎麼擺脫他呢?好長的夜,有點什麼像鴉片一般令人麻醉的東西在使她痲痺。
因為看見她沉默,沙勒以為她難過,於是強迫自己不說什麼,免得引起她傷心。
沙勒在等艾瑪回來。聽見她敲門,他張開雙臂迎上前去,用帶淚的聲音對她說:
「不,算我求你,我去。」
她趕快理好了箱子,付了帳,在院子裡僱了一輛馬車,催促馬夫,鼓勵馬夫,每分鐘打聽時間和里數,終於在干岡布瓦地區頭幾棟房子的地方趕上了「燕子」。
「我不太相信他。代書的名譽都很不好。也許該請教於……我們只認識……啊,誰也不認識!」
他又說:
僕人彎下腰,歐梅搶先拾了起來,瞪圓著眼睛,張大著嘴看了一下。
「或是毒死一個病人。」藥劑師繼續說:「難道你要我上重罪法庭,坐在刑事犯的長凳上?難道你要看我上斷頭臺?你不知道我在管理方面是多麼操心,雖然我已經習慣了。我自己都時常害怕,當我想到我的責任!因為政府迫害我們,管轄我們的荒謬的立法是一把真正的達摩克雷斯的刀,懸在我們的頭上!」
「嘿!妳有一束美麗的花!」他說,一面望著放在壁爐板上的紫羅蘭,雷翁送的。
「剛才…….」藥劑師向雨斯丹說,「你知道你所冒的險嗎?……你難道沒看見左邊角落裡,第三張小桌子上面的東西嗎?說話呀,回答呀,怎麼沒有一點聲音呀?」
沙勒天真地問她那張委託書是哪兒來的?
他來效勞,因為他們遭逢變故。艾瑪回答說她覺得可以免了。那商人就是不認輸。
其實,並沒有什麼事要她非走不可。但是她說過當天晚上要回家的。此外,沙勒在等著她。而且,她心裡已經感到一種怯懦的溫馴。對許多女人來說,溫馴既是姦淫的懲罰,也是贖罪。
他不是叫人把那塊呢料送來,而是自己拿來了。然後hetubook.com.com他又來量身;又找別的藉口再來,每次都試著做出一副和顏悅色、樂於服務的樣子,歐梅會做出一副陪臣的樣子,而且老是勸她考慮代理權的問題。他一點也不提到借據,她也沒有想到借據;在她疾病初癒的時候,他曾經向她提起過,但是她心事重重也就不再記得。加之,她對金錢的事絕口不提,老波法利太太因而感到驚訝,把那種態度歸諸在病中皈依宗教的結果,是宗教信仰使她的本性有所改變。
而且她十分鎮靜地說:
「啊!你不知道!好!我呀!我知道!你看見了一個藍玻璃瓶,用黄蠟封住了的,裡面裝的是白粉,我還在上面寫了『危險』!你知道裡面是什麼嗎?砒霜!而你去碰它!去拿旁邊的一隻鍋!」
「誰叫你到儲藏室裡去拿的?」
「你別發火嘛!」歐梅太太說。
她在拆一件大衣的夾裡,斷線殘幅散落在四周;老波法利太太低著頭把剪刀弄得吱咯吱咯地響;沙勒穿著布鞋和棕色的舊大衣(當晨衣用的),兩隻手插在口袋裡,也不說話。在他們旁邊,穿著小白圍裙的貝特正在用鏟子鏟園徑上的沙。
「妳穿著的那一件只能夠在家裡穿,應該有一件為出門的時候穿。在進門的時候,我一眼就看出了。我有像美國人一樣敏銳的眼晴。」
「我可憐的母親……她現在怎麼辦?」
「爸爸!爸爸!」
她問他什麼誤會,因為沙勒沒有告訴她關於那次訂貨的爭論。
屋頂下有一個小房間,裡面全是職業上的器具和貨物。藥劑師管那間小房子叫做儲藏室。他時常在那兒貼標籤,往瓶子裡注流汁,解開繩子又再捆上,一呆就是好幾小時。他不把那間屋子看做儲藏室,而把它視為真正的內殿,從那兒出來的是他親手製成的各色藥品:小藥丸、大藥丸、煎藥、洗滌劑、湯藥,使他遠近馳名。他不許任何人走進那間屋子,他尊重那間屋子,親自灑掃,總之,假如說藥房是他展示他驕矜的地方,歡迎任何來者,儲藏室卻是避難所,歐梅在其中聚精會神,隨心所欲,唯我是視;所以,雨斯丹的輕妄被他視為大不敬。漲紅著臉(比覆盆子還要紅),他一再說:
「你簡直無惡不作,小渾蛋……小心啊!你在往下陷,無可自拔!……你難道沒有想過,這本髒書可能落在我孩子手裡,在他們腦子裡引起火花,沾污阿達莉的純潔,敗壞拿破崙?他眼看就是大人了。你是否能肯定,他們沒有唸過?你是否能向我保證……?」
她做了一個不知道的手勢。
她走進藥房。大扶手椅翻倒了,連盧昂港燈報也在地https://m.hetubook.com.com上,在兩個杵臼之間。她推開了過道的門。沙糖、方糖,桌上的天秤,火上的盆子,和盛滿著去了皮的覆盆子的棕色罐子亂成一片。在厨房裡,她看見歐梅一家大小,飯巾一直垂到下巴,手裡拿著叉子。雨斯丹低著頭站著,藥劑師直叫道:
「妳現在完全好了嗎?」他繼續說,「妳可憐的丈夫真吃夠了苦頭,我看見的。他是個好人,雖然我們之間有點誤會。」
艾瑪說:
第二天,老波法利太太來了。母子二人大哭了一場。艾瑪找了一個有話要吩咐的藉口,走開了。
「不要吵!走開!」藥劑師說,「別煩我!說實話,這倒成了雜貨店!好啦!什麼也不必尊敬!弄破!放出螞蝗!燒掉木檯!用藥瓶裝黄瓜!撕破紗布!」
只剩下布商和艾瑪在一起。勒何開門見山地恭喜艾瑪繼承遺產,然後又談些無關緊要的事,談果樹,談收成,談他自己的健康狀況,「永遠是不好不壞」。事實上,他儘管賣命,他連抹麵包的牛油都喫不起,偏偏別人說他有錢。
「倒空!洗乾淨!拿走!快!」
「從紀尤曼先生那兒來的。」
「再能看見他就好了!」
那村子和平常一般寂靜。街角上,有一堆一堆粉紅色的東西在空中冒煙,那是做果醬的季節,雍維勒的每戶人家都在同一天做。但是人人羡慕藥房門口那一堆,大多了,也好多了。製藥室的果醬應該比一般人家的爐灶更出眾,那不僅是供應一般的需求,也是個人喜好的顯示。
艾瑪說:「可是,先生,你究竟有沒有話和我說?」
「這就是你報答我對你的恩惠的方式!我對你就像父親一般慈愛,這就是你的報答!你想想,假如沒有我,你會在哪兒?你會做什麼?誰供給你衣食、敎育、以及將來體體面面置身於社會中的一切方便?但是,為了達到那個地步,必須胼手胝足使勁划船。」他又用拉丁文說:「匠以工得名,心無二用。」
他氣壞了,所以引用拉丁文中的成語。假如他懂中文和格林蘭文,他也會引用。因為他如今正在這種狀態中,不分靑紅皂白地把靈魂深處全部的東西倒出來,就像暴風雨中的海洋,攤出海濱的墨角菜,也攤出深淵中的沙礫。
她不懂。他緘默著。然後,他又談到生意,「夫人」能不能向他買點什麼。他有一塊黑色呢料,十二呎,正好做一件衣裙。他會叫人送來。
「砒霜!你要把我們全家毒死!」
她一直保持緘默。終於,她明白了該說點什麼:
第三天,大家必須一同商議喪事。他們拿著女紅盒子,坐在水邊的涼棚下。
他心慌意亂地轉身向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