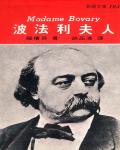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三部
8
何多夫打斷她的話,說他自己也很拮据。
他用哲學口吻回答說:
因為板壁不厚,她聽見飯廳裡刀叉在盤子上鏗鏘。
然後,她開始非常可怕地叫起來了。她咒駡毒藥,謾駡毒藥,又乞求毒藥快點生效,用僵直的手臂推開沙勒努力使她喝的東西,其實沙勒比她更痛苦。他站著,用手絹蒙著嘴,又哭又叫,因嗚咽而窒息,全身因嗚咽而發抖。費莉西特在臥室裡跑來跑去;歐梅動也不動,深深地嘆氣,一直平靜的卡尼維也開始慌張了。
她大哭起來了,何多夫以為是由於愛的爆炸使她說不出話,他以為她害羞,他說:
他問她,她不回答。她不動,怕一動就想吐。可是,她感到一陣寒冷從脚上升到心上。
但是,他突然鎭靜了。
「妳不是覺得更不舒服了吧?」沙勒問。
然後她回家,突然平靜了,幾乎像是履行了一項義務那麼寧靜。
首先,她望了他幾分鐘。
她突然覺得有些火球在空中爆裂,就像一團一團的彈藥炸開了,在地面上粉碎了,旋轉著,旋轉著,在樹枝之間和雪溶在一起。在每個火球中央都有何多夫的臉。火球越來越多,越來越彼此接近,鑽進她體內,不見了。就像看見屋子裡的燈火在霧中遠遠地照耀著。
「人要是窮呀,鎗銃上就不會有銀子!」然後,她又指著布勒式的烏木掛鐘說,「人要是窮呀,就不會買鑲玳瑁的烏木掛鐘!也不會買為馬鞭的鍍銀哨子(她摸那些哨子)——也不會買鑲珠寶的錶鍊。」啊!他什麼都有!臥房裡也有酒櫃。「你愛自己,你過得舒服,你有城堡、農莊、樹林,你騎馬打獵,你去巴黎旅行……」她一面拿起壁爐板的袖扣,一面說,「光是這小玩藝兒也能賣錢!啊!我不會要的,你留著吧!」
然後,病狀停止了一會兒;她不像剛才那麼激動;每逢她說一句無關緊要的話,每逢她的呼吸平靜一點,他又懷著希望。當卡尼維進來的時候,他哭著投入他的懷裡:
沙勒用雙臂抱住他的身體,驚惶而又哀求地注視著他,幾乎暈倒在他胸前。
正拿著一堆碟子的雨斯丹發起抖來了。
她出賣了自己,也在毀滅自己。
事實上,她在慢慢地向四周環顧,好像一個從夢裡醒來的人。然後,她用很清楚的聲音說要一面鏡子,照了一會兒,直到一大滴一大滴的眼淚流下來。然後,她一面往後仰,一面又倒在枕頭上。
吃過幾口之後,醫師覺得最好讓他聽聽病情。
她看起來太可愛了,一滴淚在眼睛裡顫動,像藍杯裡的一滴澄汁。
他的出現比神的出現還更令人興奮,波法利舉起了手,卡尼維突然停止了開藥方,那醫師還沒有進來,歐梅就取下了希臘帽子。
夜已降臨,鳥已歸巢。
「不必,我回頭告訴他,用燈照亮我。」
她醒了,因為聞到口裡有苦澀的味道。她窺見了沙勒,又把眼睛閉上。
他望著她,眼裡充滿著她從來沒有見過的柔情。
「你以為是那樣嗎?」她走近他說。
「夠了!把她抱走!」沙勒在床前哭著說。
「啊,那是可悲的魅力,」她苦澀地說,「既然你輕視。」
「高脚玻璃!!!」歐梅低聲說。
他把她拉到膝蓋上,用手背摸她兩片光滑的、貼在耳邊的頭髮。一縷最後的陽光,就著黃昏的微明,像一枚金箭在她頭髮上閃爍。她低下了頭,他終於用嘴唇輕輕地吻了她的眼瞼。
「假如我們是在城裡,我們至少可以買到餡兒蹄子。」
他又回到家裡去寫信給卡尼維先生和拉利維耶博士。他昏了頭,起了十五六張草稿,伊波利德動身去內沙德送信,雨斯丹拼命踢波法利的馬。馬累得幾乎倒地不起,他只好把馬丟在紀尤姆森林。
「我曾經想做一次分析,醫師,首先,我曾經在管子裡放進……」
「讓我們上去!」
神父擦乾了手指,把蘸過油的棉花扔在火裡,再回來坐在垂死者的身邊,向她說她現在該把自己的痛苦和基督的痛苦合而為一,並且接受神的憐憫。
「她究竟是怎麼中毒的?」
「把孩子帶來給我。」她說,一面用肘子撐著自己。
沙勒想翻醫學字典,他看不清楚,字好像全在跳舞。
她想,折磨著她的一切背叛,一切卑劣行為,一切數不清的貪慾快終止了。她現在不恨任何人,有一種黃昏的朦朧落在她的思想上,人間一切的喧囂她都聽不見,除了她可憐的內心和*圖*書間歇的哀號,溫柔的,不太清楚的,像一曲漸漸遠去的交響樂的最後的回聲。
「不!別去!」
「別張揚出去,那會害了你主人!」
「是的……也許。」
但是,他慢慢地用肩膀做了一個姿勢。波法利望著他,他們互相注視;然而,那個習慣於痛苦景象的人也忍不住掉眼淚了,眼淚滴落在胸飾上。
「啊!何多夫!我一直都那麼愛你,假如你能知道就好了!」
「啊,是妳!」他突然站起來說。
然而,面對著他所謂的「使命」,他並不怯步。他陪著卡尼維先生回到波法利家,拉利維耶先生動身前曾一再叮嚀卡尼維去參與後事。假如太太不反對的話,他會把兩個兒子帶去,讓他們習慣於人生大事,讓大事變成教訓,變成例子,變成一幅莊嚴的畫面。日後,那畫面將會永遠留在他們的腦海中。
汗珠從她微藍的臉上冒出來,臉好像凝固在一層金屬的蒸汽中。她的牙齒咯咯作響,睜大了的眼睛茫然地向四周環顧,問她什麼問題她都用搖頭做回答,她甚至微笑了兩三次。漸漸地,她呻|吟得更厲害了,不自禁地大吼了一聲,但是她假裝說好些了,說一會兒就起來。但是她抽搐著,她叫:
那位醫學博士轉過身去。
最後,拉利維耶先生要走了。歐梅太太請他診斷一下她丈夫。他的血太多了,每天吃過晚飯就想睡。
他又回到她身邊,在地毯上坐下,把頭靠著床邊哭泣。
「禮物在哪兒嘛?媽!」
「我馬上回來。」
她已經回來了。
「啊!妨礙他的不是『性』」(在法文中「血」和「性」發音相同,假如不把「性」字中的字尾S唸出來)。
她的目光停在一枝嵌銀的短鎗上,鎗在一排武器中發光。
她作了一切的努力,就是無法開口。
最後,他冷靜地說:
「但是……」
「分析呀!分析呀!救救她。」
艾瑪突然笑起來,一種可怕的笑,一種瘋狂的笑、絕望的笑,以為看見那可憐人的恐怖的面孔矗立在永恆的黑暗中,像一種恫嚇。
「砂糖,大夫。」
他跟著她。
「我怕!」那孩子說,一面後退。
「救救她呀!」波法利直喊。
「你沒有!我原該免了最後這場羞辱的,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你也比別人好不到哪兒去!」
「你怎麼了?」藥劑師說。
「是的,是我!……何多夫,我想請你提供一點意見。」
「啊!死算不了一回事!」她嘆了一口氣,她想,「我就要睡著了,一切就完了!」
「不能吃呀!」他撲向她說。
「可是……可是……」他說,一面慚漸地站起來,面部表情變得很嚴肅。
「你明天看,從現在起,我求你別問我任何問題!不,一個也別問。」
「啊,原諒我!我只喜歡妳一個人。我又笨又可惡!我愛妳,我永遠愛妳。……妳有什麼事?說呀!」
他一進門就皺眉了,因為他看見艾瑪的臉色像屍體一樣的蒼白。她仰著睡,張開著嘴。然後,他一面裝著聽卡尼維的話,一面把食指放在鼻孔下,一再地說:
艾瑪又坐了起來,像一具觸了電的屍體,首如飛蓬,眼睛定定的而且木然。
「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向我解釋好不好?」
「鑰匙!樓上的……」
「別哭!」她說:「不久我就不會折磨你了。」
神父又站起來拿十字架;那時,她像一個口渴的人,把脖子伸出來,把嘴唇貼在基督的聖體上,盡全力去給聖體一個最大的愛之吻,前所未有的一個吻。然後,牧師背誦著願主慈悲和賜恩,把右手的大拇指浸在油裡,開始塗油:首先是在眼睛上,那雙眼睛曾經非常貪戀人間的榮華;然後在那喜歡微風和愛之芳香的鼻孔裡;然後在嘴上,那張嘴曾為說謊而張開,曾因驕傲而呻|吟,因淫慾而叫喚;然後在手上,那雙手曾經喜歡撫觸柔軟的東西;最後在脚掌上,那雙脚從前曾因為滿足肉|欲而疾步如飛,而現在再也不能步行了。
於是,他開始解釋他的行為。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藉口,他用含糊的話語請求原諒。
「我看不見我的小鞋!」
沙勒在屋子裡茫茫然的轉圈子,話也說不清楚,幾乎要倒下了。他撞到傢具,扯自己的頭髮,藥劑師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景象。
母親望著她。
「我不知道,醫師,我甚至不知道她在哪兒弄到了砒霜。」
艾瑪說:「至少我們的分手對你來說是好的吧?」
「我沒有三千法朗,親愛的夫人。」
她走了。牆在震動,天花板壓著她。她又走上了那條長長的園徑,隨風和-圖-書飄揚的一堆落葉絆著她。她終於來到了鐵柵門前的濠溝旁邊,她忙著開門,鎖弄傷了她的手。再走了百步之後,她停了下來,她喘不過氣,幾乎要摔倒。她再回頭望一眼那無情的城堡,大大小小的花園,那三個庭院以及正面所有的窗子。
「沒有你,你要我怎麼活?當一個人已經習慣於幸福的時候,沒有幸福就不成了。我曾經絕望!我以為會死去。我要告訴你那一切,但是你卻逃避我。」
然而,她並不太蒼白,她的面部表情很寧靜,好像臨終聖典治好了她。
「效果也該停止,」歐梅說,「那是很明顯的。」
「你現在就走?」
可是她大聲說:
「別叫,會有人來的……」
一陣痙攣使她倒在床墊上,大家都圍攏過來,她已不復存在了。
她突然想吐,幾乎來不及拿枕頭下面的手絹。
她一面唱歌,一面自己:「我該說什麼呢?我怎麼開始說呢?」她一邊向前走,一邊認出了灌木叢、樹群、小山上的帶刺金雀花矮樹,那邊的城堡。她覺得自己又置身於最初的柔情感受中,她可憐的,被壓抑了的心又在昔日的柔情中膨脹。溫暖的風吹著她的面孔,正在溶化的雪一滴一滴地從樹椏上落在草上。
然後,他叫孩子們全下樓來,他急於想知道那外科醫師對他們的身體的意見。
一如往昔,她從花園裡的一扇小門進去,然後來到了正面的院子裡,四周有兩排茂密的菩提樹。長長的枝椏搖曳著,發出如口哨般的聲音。狗舍裡的狗全都在叫,叫聲迴盪但是卻沒有人出來。她走上了一座又寬又直的樓梯,樓梯有木欄杆,通向一條蒙塵的、鋪著石板的甬道,甬道的兩側有一排一排的臥室,像在寺院裡或旅舍裡一樣。何多夫的臥室是在左邊的最末端。當她把手放在鎖上的時候,她莫名其妙地失落了氣力。她怕他不在家,幾乎是希望他不在家,然而那卻是她唯一的希望,是她最後一個得救的機會。她沉思了一分鐘,感到現在有見他的必要,於是她鼓足勇氣進去了。
「我要鑰匙,給我嘛!」
「他們在吃晚飯,讓我等一等。」
費莉西特使她俯身向床,而她老是向壁爐那邊望。
「人生就是這樣!」
藥劑師還在假定:「這種危險也許是轉機。」卡尼維不聽他的假說,打算開解毒劑。那時,傳來了一陣馬鞭聲。所有的玻璃窗都震動起來。一輛驛車被三匹泥巴濺到耳邊的馬拖著,在菜市場的一角停下了。是拉利維耶博士來了。
他跳到書桌面前,拆開信,高聲唸:「別控吿任何人……」他沒有再唸下去,用手摸了一下眼睛,又唸。
「什麼?」
「你沒有!」
「妳沒有變,還是那麼有魅力。」
「雨斯丹!」藥劑師在不耐煩地叫,牆上掛著一把有標籤的鑰匙。
「哎!何多夫,我破產了!借我三千法朗!」
「好,好。」
「奇怪!奇怪!」他一再說。
「啊!我可憐你!」艾瑪說,「你相當可憐!」
歐梅遵照他那一套原則,把神父比做被死屍的氣味所吸引的烏鴉。他一看見神父就不愉快,因為道袍使他想起屍衣,他討厭道袍,因為他害怕屍衣。
她很快就吐血了,舌頭也縮得更緊。四肢抽搐著,全身浮起了棕色的斑點,脈在手腕下緊張著,像一根就要折斷的豎琴弦。
因為,三年來,他一直小心地逃避她,因為男性天生就懦弱,那是他們的特性。艾瑪繼續和他說話,做出可愛的姿態,比一隻多情的貓還會撒嬌。
歐梅因為請到了貴賓而喜笑顏開,他的行為原本就有自私的成份,想起痛苦的波法利反而更高興了。那位醫學博士的在場令他欣喜若狂,他炫耀自己的博學,他紛紛引證芜菁,爪哇人用植物提鍊的毒藥「烏巴斯」、死人樹及毒蛇。
「但是,要是我,我會付出一切,變賣一切,用我的手工作,我會去街上行乞,只是為了看你微笑,為了讓你瞧我一眼,為了聽你說聲『謝謝』。而你卻靜靜地坐在沙發椅子裡,好像你還沒有讓我吃夠苦頭。你可知道,沒有你,我原本可能活得快樂?是誰迫使你那麼做的?是一場打賭嗎?可是你一直說你愛我……剛才還說過……哎!最好攆我走!我手上還有你的熱吻,在地毯上,在這地方,你曾在我膝上發誓永遠愛我。你曾使我相信你的誓言。有兩年的功夫,你把我牽引到一個最美妙的夢中!啊!我們的旅行計劃,你還記得嗎?啊,你的信,你的信,它撕碎了我的心!然後,當我再回到他身邊(他富有、幸福、自由!)求他幫個忙(人人都會幫的),央求他,帶給他我所有的柔情的時候,他卻拒絕我,因為那會浪費他三千法朗!」
「啊,媽,妳的眼
和*圖*書睛好大,妳的臉好蒼白!妳流好多好多的汗!」於是,他小心地,幾乎是愛撫地,用手摸她的胃。她尖叫了一聲,他嚇得往後退了。
他不是說謊。假如他有,他一定會給,雖然一般說來做好事並不好玩。摧殘愛情的暴風雨有許多種,而借錢是冷酷也最具摧毀性的。
他連忙派人去金獅客棧買鴿子,去牛肉店買所有的牛排,去杜法施家買乳酪,去雷斯迪布多瓦家買雞蛋。藥劑師親自幫著做準備工作,歐梅太太卻拉著衣帶說:
另一位外科醫師卡尼維沒有說話,因為剛才私下裡由於開嘔吐劑而受了一場教訓。診治跛脚的那天,卡尼維既傲慢又多言,他今天卻十分謙虛,不斷地微笑,帶著一副贊同的樣子。
然後,她就直直地在床上躺下了。
她輕輕地轉動著頭,那姿勢充滿著痛苦。她攤開著手絹,好像她舌頭上有點什麼太重的東西隨時會吐出來,八點鐘的時候,嘔吐開始了。
「啊,走開!」
女傭人把孩子抱來了,孩子穿著長睡袍,赤脚露在外面,樣子很嚴肅,幾乎有點像做夢。她驚訝地望著亂成一團糟的屋子,眨著眼睛,因為桌上燃著的蠟燭令她目眩。也許,蠟燭使她想起新年或四旬齋的早晨,因為在那種早晨也有燭光,人們很早就把她叫醒,她到母親床前接受禮物,所以她問:
「她的情況很嚴重,是不是?貼芥子膏好不好?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您想想辦法嘛!救過許多性命的您。」
歐梅太太又出來了,拿著一具搖搖晃晃的燒酒精的機器,因為歐梅堅持要在飯桌上煮咖啡,而且是他親自焙好了、磨好了、調好了的。
她走進了甬道,甬道的門通向實驗室。
「應該通知先生。」
她又用急促的、溫柔的、誘惑的嗓音說:
「什麼?……救命呀!來人呀!」他大聲叫。
「不是!不是!」
「開始了。」她低聲說。
他沒有主意了,想大聲叫。
「為什麼?是誰逼妳的?」
為了辛勤地拾起
鐮刀收穫的麥穂
我的拿内德俯身
向賜給我們麥穗的犂痕。
鐮刀收穫的麥穂
我的拿内德俯身
向賜給我們麥穗的犂痕。
「反正,我受夠了苦!」
藥劑師和他們在廣場上碰頭。他生來就是要和名人在一起。他想請拉利維耶吃午飯,求他光臨。
她說:
他望著她,因她的臉色蒼白而驚訝,她蒼白的臉與黑夜的背景正成對比。他覺得她非常美,像幽靈一般莊嚴,他不知道她要什麼,但是卻預料到一點什麼可怕的事。
她嘆了一口氣:
「可是,妳哭了,為什麼?」
「拿掉枕頭!」她急忙說,「扔掉!」
歐梅叫起來了:「笨蛋,笨手笨脚的傻瓜,笨驢!」
奶媽那個稱呼使波法利夫人想起通姦和災禍,一聽見說起奶媽,她就把頭轉開,好像有一種更強烈的毒物向口裡冒,而貝特還坐在床上。
他在爐火前面,雙腳放在壁爐板上,正在抽煙斗。
「啊!既不好也不壞。」
「不,你弄錯了!」
她的處境又呈現在她眼前,像一個深淵。她氣喘得胸口都要裂開了。然而,她突然興起了一個英雄的念頭,那念頭使她變得幾乎快樂起來,她跑下山,穿過了讓牛走的木板、小徑、園徑、菜市場,到了藥房門口。
她喝了一口水,把身子轉向牆。
他出去了,和卡尼維一起,像是有話吩咐馬車夫,其實他們兩人都不願看見艾瑪死在他們的懷抱裡。
突然,人行道上傳來一陣大木屐的聲音和手杖敲打地面的聲音,一個沙啞的聲音唱著:
「說話呀!妳吃了什麼?看上天份上,回答我!」
然後,她裝著毫不在乎的樣子說:
她被他的語言打動了,尤其是被他的聲音和面容打動了,她假裝相信,或者真的相信他們分手的藉口。那是一個秘密,牽涉到一個第三者的名譽甚至生命的秘密。
他把糖遞給大夫,一面用拉丁文說:
一個晴天的溫暖
常使少女夢想愛情。
常使少女夢想愛情。
「坦白地說吧,你現在愛別人。啊,我瞭解她們,我原諒她們。像你曾經勾引我,你也勾引了她們。你是一個男人,又有使女人愛你的一切條件。然而,我們可以從頭開始,是不是?我們會彼此相愛吧?瞧!我在笑,我幸福,……你說話嘛!」
大家的注意力因布尼賢神父的出現而分散了,他正帶著聖油從菜市場下面走過。
那同行的看法和他的不一樣。像他向自己所說的,別「亂兜圈子」,他開了一帖嘔吐劑,徹底清除腸胃。
沙勒給他看信,是砒霜。
「首先我們知道她喉頭痛,https://m.hetubook.com.com然後是上腹痛得厲害,嘔吐,和昏迷。」
然後她開始呻|吟,首先是輕輕地。她肩膀哆嗦得厲害,她痙攣的手指抓住床單,臉色變得比床單更白。她不均勻的脈搏現在幾乎感覺不出來。
「好痛苦,我的上帝!」
她坐在書桌面前寫了一封信,慢慢地封了口,一面加上日子和時辰。然後,她用莊嚴的語氣說:
不久,她開始急劇地氣喘。整個舌頭都從嘴裡伸了出來。她的雙眼一面轉動一面變得蒼白,像兩盞正在熄滅的圓燈。如果不是兩肋急速地抽動,還真以為她死了,一陣急促的呼吸搖撼著她的雙肋,活像靈魂掙著要脫離軀體。費莉西特在十字架面前跪下,連藥劑師也屈膝了,卡尼維先生茫然地望著廣場。布尼賢又開始祈禱了,臉靠著床緣,黑色的長道袍拖在他後面。沙勒跪在床的另一邊,雙臂伸向艾瑪。他握住了她的手,抓得緊緊地。每逢她心跳一次,他也哆嗦一次,像是有一個傾塌的廢墟震撼著他。哮喘變得越強烈,神父也越加速祈禱。禱文和波法利壓抑了的嗚咽混在一起。有時,一切都像是消失在低沉的拉丁文音節裡,音節像鐘聲一般。
他跪下了。
「好吧……那兒……」她用微弱的嗓音說。
那外科醫師說:「最好是把你的手指放進她的喉嚨裡。」
因為他知道,只要是毒藥就該作一次分析,對方不懂,只是說:
「是的,這是真話,你很善良!」
「妳不快樂嗎?是我的錯嗎?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力量了。」
她說了好幾遍:
他只能一再說這個字:「服毒!服毒!」費莉西特跑到歐梅家去,他在廣場上大叫;勒佛杭絲瓦太太在金獅客棧聽見了他的叫聲,有幾個人起來向鄰居宣佈這個消息,村子裡的人一整夜都沒有睡。
她因驚愕而迷惘,忘了自己存在,除了脈搏的聲音。而她一聽見脈搏的聾音就跳了起來,像震破耳膜的香樂,充滿著鄉野氣息。她腳下的泥土比水波還軟,她覺得犁痕像大大的棕色浪濤舒展著。她腦子裡所有的回憶和意念都一下逃逸出來,像火焰迸出的萬千火花。她看見她爸爸,勒何的工作室,她和雷翁的臥室,以及另一種風景。她快要瘋了,她害怕了,終於以一種昏昏沉沉的方式鎮定下來,那是真的;因為她並不記得自己為什麼會處在這種可怕的處境中,也就是錢的問題。她只因愛情而痛苦,覺得心靈藉回憶而遺棄她,就像受傷的人在臨終時覺得生命從流著血的傷口走掉。
何多夫十分冷靜的回答說:「我沒有那筆錢!」那種冷靜好像是用以掩護忍讓的憤怒。
「你安靜一點!」藥劑師說。「只要開一點強烈解毒劑,是什麼毒藥?」
口裡還是有可怕的墨水味。
「妳少說廢話!……開飯了,醫師!」
「我渴!……啊,我口好渴!」她嘆了一口氣。
「也許還不該絕望。」他想。
雨斯丹回來了,她敲了窗,他出來了。
艾瑪拿起她的手來吻,她掙脫了。
她把那兩枚袖扣扔得遠遠的,金鍊子在牆上碰斷了。
沙勒看見痰盂底上有一種白粒黏在瓷上。
她慢慢地把臉轉過來了,好像因為突然看見神父的紫帶而喜悅,一定是在不尋常的平靜之中她又找到了已失落的快|感——她早期的宗教狂和如今正在開始的永恆的福澤之幻景。
「啊,是您!謝謝!您真好!可是一切都比剛才更好了,瞧她!」
他們進去的時候,臥室裡充滿著悲哀的莊嚴感。鋪著一塊白檯布的女紅桌上有一個銀盤,其中放著五、六個棉花球,銀盤在一個大十字架旁邊,在兩枝燃著的蠟燭之間。艾瑪的下巴靠著胸口,眼睛睜得大大的,她可憐的雙手用可怕而又溫馴的姿態垂在床單上,彷彿已經被屍衣覆蓋著。沙勒站在床前,面對著她,蒼白得像尊雕像,眼睛紅得像煤炭。一旁的神父用一隻脚跪在地上,口中唸唸有詞。
當沙勒因聽見沒收家具而回家的時候,艾瑪剛剛出去。他叫,他哭,他暈倒了,但是,她沒有回來。她可能到哪兒去了?他派費莉西特去歐梅家,去杜法施家,去勒何家,去金獅客棧,去所有的地方;痛苦之餘,他看見自己身敗名裂,破產了,貝特的前途也毁了!是為了什麼緣故?……一句話也沒有!他一直等到晚上六點。最後,他忍不住了,以為她去了盧昂,他在公路上走了半里路,沒有遇見人,再等了一會,只好回來。
鑰匙在鎖孔裡旋轉了,記憶帶她一直走向架子的第三層,抓住了藍色的藥瓶,拔開了塞子,把手伸進去,抓了一大把白粉,開始吃起來。
沒有人,她預備進去,但是,聽見門鈴聲,可能有人會來。於是她滑過柵欄、屏住氣、摸著牆,到了廚房門口。灶上點著hetubook.com.com一枝蠟燭,穿著襯衫的雨斯丹正端走一盤菜。
「也許我們不該分手的。」
拉利維耶屬於畢沙門下的偉大外科學派,那是哲學醫師派,如今已經消失了。他們熱愛自己的醫道,行醫的時候既有熱情也有智慧。他生氣的時候,整個醫院的工作人員都會發抖,他的學生非常尊敬他,行醫的牌子剛剛掛起時就努力模仿他,因此,在附近的城裡,你會發現他們和他一樣,在服飾方面,他永遠穿著一件羊絨大衣,一身寬適的黑禮服,敞開的袖口微微掩蓋著他那肥胖的、美麗的手,他從來不戴手套,像是為了更易於投入疾苦之中。他輕視十字勳章,學院頭銜,他樂善好施,對窮人非常慈祥,他力行道德而不相信道德,假如不因精明而被視為魔鬼,他幾乎可以算是一位聖人。他的目光比他的解剖刀還更尖銳,深入你的心靈。藉了引證和含蓄,他能解析一切謊言。他就這樣為人處世,充滿著和善的莊嚴,那莊嚴來自他的才能、財富,和四十年來勤勞的、無懈可擊的生活。
她帶著好奇心偵察自己,看會不會難受。不!還不!她聽見鐘的嘀嗒聲,火的聲音,以及站在床前的沙勒的呼吸聲。
神父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他甚至向波法利先生解釋,有時天主故意延長垂死者的生命,當他覺得那樣做對垂死者的得救有幫助的時候。沙勒也想起來了,有一天她也幾乎死去,而且領了聖餐。
「那個瞎子!」她說。
「好,必須分析一下。」藥劑師說。
「妳究竟怎麼了?」沙勒說,遞給她一杯水。
聽見這個問題,那年輕人讓手裡的盤子唏哩嘩啦全掉在地上。
「對不起,先生,因為我們這小地方,假如不是頭一天通知的話……」
那天風很大
短裙飛揚!
短裙飛揚!
這時,她握住了他的手,他們手指交叉著手指好一會兒——像第一天,在農產品改進競賽會的時候。他被感動了,但是用一個驕傲的手勢掙脫她。而她伏在他懷裡說:
「沒有什麼!……開窗……我不能呼吸!」
大夫一面開門,一面微笑,因為沒有人聽出了那句雙關語。藥房裡擠滿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擺脫了他們:杜法施先生怕他太太害肺炎,因為她老是往灰裡吐痰;接著是畢內,他有時突然覺得餓;卡洪太太渾身癢癢;勒何先生頭昏;雷斯廸布多瓦有風濕病;勒佛杭絲瓦太太胃酸過多。終於,那三匹馬出發了,很不馴良。
勸告完了以後,他試著把一枝聖燭放在她手裡,那聖燭象徵即將包圍她的天國的榮耀。艾瑪太虛弱了,無法把手合攏,假如沒有布尼賢神父的幫助,聖燭就會掉在地下。
他想把卡尼維帶到隔壁那間屋子裡去。沙勒跟著他。
她說老鼠吵得她睡不著,她需要毒鼠藥。
她急忙地說:「你知道,我丈夫把所有的錢交給一位律師經管,他逃走了。我們借了債,病人不付診費。再加上,遺產還沒清算,我們日後還會有錢的。但是,今天,由於缺少三千法朗,他們要沒收我們的財產,就是現在,就是此刻。因為信賴你的友情,所以我就來了。」
她用手撫摸他的頭髮,慢慢地。那甜蜜的感覺增加了他的悲傷,一想到將失去她,他整個人都崩潰下來了,而她卻相反地訴說她比任何時間都更愛他。他找不出任何理由,他什麼也不知道,他也不敢問,因為她急著立刻下決心就使他心慌意亂。
「是不是奶媽拿走了?」她問。
「天!……可是她已經吐乾淨了——原因一消滅……」
因為大家都不說話,她說:
「我可憐的孩子,拿出勇氣來!再也沒有辦法了。」
「大夫,我甚至在書裡讀到過,有些人吃燻得太厲害的血腸就會中毒而死,像遭雷殛一樣。至少出名的卡德.德.卡西古在一篇美好的報告中就提起過,他是我們的大師,是藥學權威!」
「妳說什麼?」
「我認為必須這樣做,親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