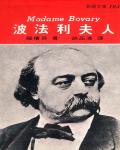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三部
7
他坦白地說房東不喜歡他接待女賓。
「不……但是……」
稅務員像是在聽,一面瞪大著眼睛,好像聽不懂。她在繼續說,帶著溫柔的、央求的樣子。她喘著氣走近他,他們停止了說話。
但是,當她向他借一千銀幣的時候,他咬了一下嘴唇,然後說可惜他從前不曾經管她的財產,因為女人也有許多方法使金錢生利。不論是格呂門尼的泥炭礦也好,或是哈佛港的地皮也好,全是上好的投機事業,而且十拿九穩會賺錢。然後他讓她想著自己原可能賺天文數字的錢,而且因失去了機會而憤怒。
「可愛!……很美!」
但是他無法壓抑他太強烈的慾望:
她穿上了黑色衣裙,戴上有黑星片的帽子。為了怕被人看見(廣場上一直有很多人),她選了河邊上的小路。
「啊!她來了!」杜法施太太說。
「去哪兒弄?」
他平板的聲音唧噥著,像一條流著的小溪。透過眼鏡的亮光,他的瞳仁裡迸出了一粒火花。他把雙手伸入艾瑪的袖口,摸她的前臂。她覺得臉上有他急促的呼吸,這個男人令她感到非常不安。
他們終於走了,費莉西特進來了。艾瑪曾經派她去窺伺波法利,把他支開。看守沒收品的人說什麼也不肯走,她急忙地把他安頓在頂樓上。
「啊!是書信!」哈杭律師含蓄地微笑著說,「但是請允許我看一看,因為我不知道盒子裡是否有別的東西。」
「很高興看見妳!」他向艾瑪說,一面伸出手來扶她走上「燕子」。
「幾點鐘了?」她問。
天氣很好;是三月裡一個晴朗凜冽的日子,太陽在全白的天空裡照耀著。穿著星期天的外出服的盧昂人在散步,個個喜形於色。她到了教堂門前的廣場,信徒們剛做完晚禱,分別從三扇門出來,像一條河流過一座有三個圓拱的橋。門警站在中央,比磐石還更靜止。
於是,他傻傻地說:
「摩勒兒今晚回來!我相信他不會拒絕我。」(摩勒兒是他的一個朋友,父親是富商)「我明天把錢送來。」他又說。
她一到就喝了一大杯水。她臉色很蒼白。她向他說:
「先生馬上就要回來了。」
她緊握著他的手,一面搖他,一面說:
她去了奶媽家,是恐懼感把她從家屋裡攆出來的。
「她在勾引他嗎?」杜法施太太問。
她敘述的時候也帶著罵勒何幾句。聽見她責怪勒何,律師說幾句不關緊要的話來應付。他一面吃豬排,一面喝茶,一面低下頭,下巴觸及天藍色的領帶,領帶上別著兩枚鑽石別針,那兩枚領帶別針被一根小金鍊繫住。同時,他的微笑也奇怪,既溫柔又曖昧。當他看見她的鞋子濕了的時候,他說:
「美好的東西不會弄壞任何東西。」
「小心!」一個聲音說,那聲音來自一扇正在開的車門。
四點鐘響了;她站起來,動身回雍維勒,像一個機器人服從習慣的推動力。
那時,會有一陣嗚咽,然後他會大哭,驚愕過去以後,他會原諒她的。
然後他們默默地相對而坐,在壁爐的兩角,一動也不動。艾瑪聳聳肩,一面蹬腳。他聽見她說:
她跑去告訴卡洪太太。那兩個女人上了頂樓,躲在晾衣服的竿子後面,她們很方便地站在一個地方,可以看見畢內的屋子。
「可是……」
「是的,妳去嘛!去沒有錯。」
有一刻鐘的功夫,她們列舉雍維勒鎮可能願意幫助她的人。每逢費莉西特說出一個名字,艾瑪就說:
「誰讓妳來這兒的?」
「去嘛!試試看!一定要奔走一番!……啊!你去試試!我會愛你
https://m.hetubook.com.com的。」
她開始訴說她的處境。
她燃燒的瞳孔裡流露出一種像地獄的大膽,她用淫|盪的及鼓舞的方式微閤雙眸,在那個要他犯罪的女人沉默的意志力下,那年輕人覺得自己太脆弱了。於是,他害怕了。為了避免一切解釋,他搥搥額頭說:
他原以為艾瑪聽了會很高興,可是她並沒抱著希望的樣子。她在懷疑他說謊嗎?他又紅著臉說:
所以他知道(比她自己還要更清楚)那些票據的悠久歷史,首先是小數目,寫著不同貸款人的姓名,期限很長,又不斷地延長,到後來,集合所有的拒付證明書,布商請凡薩出面追索借款,免得他的同鄉把他視為猛虎。
律師進來了,左手壓著他那印著棕櫚樹的睡袍,另一隻手取下又連忙戴上他的棕色絲絨帽,那頂帽子是斜斜地戴著的,神氣活現地向右歪,帽子下面露出三綹金髮,沿著後腦,那些金髮圍著他的禿頭。
她怕把壁爐弄髒了。律師用討好女人的語氣說:
「可以看嗎,太太?可以看嗎?」
「朋友,這種可怕的病你生了很久嗎?你最好節食,不要在酒店裡喝醉。」
「去你的事務所!」
艾瑪沒有回答。她喘著氣,向四周環顧,那鄉下女人被她面部的表情嚇壞了,本能地往後退,以為她瘋了。突然,她搥打自己的額頭,大叫一聲,因為對何多夫的回憶像一道大閃電一般在黑夜裡掠過,射入了他的心靈。他是那麼仁慈、那麼細心、那麼慷慨!而且,對於幫忙這件事,假如他有所遲疑的話,她會知道如何強迫他,只要她一眨眼,失落了的舊情又會復燃,於是,她動身去雨歇德,不知道自己此去是獻身給從前那麼激怒過她的羞辱,或是去出賣自己的身體。
瞎子坐在自己的腿彎上,頭向後仰。他一面轉動他微綠的眼睛,一面伸出禿頭,一面用雙手擦自己的肚皮,同時還發出低沉的聲音,像一條饑餓的狗。覺得噁心的艾瑪從肩上扔給他一枚五法朗的硬幣。那是她全部的財產,她覺得把財產那樣扔掉很美。
而且,誰知道?一瞬之間可能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為什麼不?連勒何也可能死去。
「等什麼?」律師說,他突然變得臉色蒼白。
他也顧不到睡袍,一下跪在她面前:
「別吃澱粉汁和乳品!穿羊毛內衣,有皮膚病的地方用檜柏果子薰。」
她覺得自己弄錯了人。而且,她根本就不知道是否弄錯了。一切,內心的或外界的一切,都遺棄了她。她自覺迷失了,在無以訴說的深淵中亂滾。當她到達紅十字旅社,看見好心的歐梅把一個裝滿了藥品的大盒子放在馬車上的時候,她幾乎是高興的。他手裡拿著一塊圍巾,圍巾包著六個「鐵路工人」,那是送給他妻子的小麵包。
他們從波法利先生的診斷室開始,沒有記下為研究腦相學用的頭顱,認為是那是「職業用具」;但是他們數了廚房裡的盤子、鍋子、椅子、燭臺,也記下了臥室裡架子上所有的古董。他們檢查她的衣服、內衣、梳妝間。像一件被當做檢驗的屍首,她生活最隱密的部份都攤在那三個人的眼前。
歐梅太太非常歡喜那種又小又重的,像包頭布的麵包,那是在四旬齋的時候用鹹牛油塗著吃的。那種麵包是哥德式食物的最後樣品,可以追溯到十字軍時代,從前健壯的諾曼第人總是吃那種麵包,在火把的金光下,在一瓶一瓶的甜藥酒和一大塊一大塊的豬肉之間,他們想像那些麵包是回教徒的頭顱。藥劑師太太
https://www.hetubook.com.com的牙齒雖然不大好,但還是像諾曼第人一般英勇地啃那種麵包。因此,每逢歐梅上城裡去,他總不忘記去屠宰街那家大麵包店去買一些帶給她。
那可憐的女傭人非常激動,遞給女主人一張黃紙,是她剛從門上扯下來的。艾瑪一眼就看見了:拍賣她全部的家具。
此刻,她因為不曾首先想到他而感到驚訝。他昨天答應了的,他不會不守信用;她已經看見自己在勒何家裡,把三張鈔票攤在他書桌上。然後該編個向波法利解釋的故事。什麼故事呢?
「雷翁!幫我一個忙。」
艾瑪想:「這才像個飯廳,我就需要這樣的一個。」
瞎子把帽子伸過來了,帽子在車窗口晃來晃去,像一個口袋。
因為說那些話的時候,她消失了;然後,看見她穿過大街,向右轉,好像要去公墓,她們就開始亂猜。
那兒有一張寫字檯,她把何多夫的信鎖在裡面。必須打開。
他出去後,一個鐘頭以後又回來了,帶著莊嚴的樣子說:
「她在哪裡?」杜法施太太說。
何雷太太走出去,朝天空中最亮的那邊舉起手來,看看錶,慢慢地走回來說:
於是她試著感動他,他自己也很激動,她向他講述起她家庭的拮据,她的困擾,她的需要。他明白:一個衣飾典雅的女人!他完全轉過身來面對著她但是沒有停止用餐。轉身的時候,他的膝蓋撞到了她的靴子,鞋底彎彎的,在爐子旁邊冒煙。
「還沒有!」
「求妳不要走!我愛妳!」
「快!」
聽見門鈴聲,穿著紅背心的德歐多在臺階上出現了。他開了門,像是一見如故,請她在飯廳裡坐。
「這是一枚兩法朗的硬幣,找我三分之二的零錢。別忘記我的話,那樣吃那樣喝你會好的。」
「我去了三戶人家,沒有辦法。」
看到家的時候,她有一種癱瘓的感覺。她無法向前走,可是又該向前走。而且,逃到哪兒去?
「是的,」她咬著牙嘀咕,「他呀,他不會有一百萬送給我,讓我原諒他認識了我。即使他有,我也不原諒他,決不!決不!」
艾瑪的臉立刻泛起一片深紅。她後退了一步,樣子很可怕,一面說:
常常,他也讚賞地說:
「可是他不賣任何東西。」
「為什麼?妳那麼怕我?相反地,可憐的是我!我們幾乎是陌生人!我卻對妳非常忠誠,我希望妳不再懷疑我。」
「那筆錢。」
「何雷太太,」她一到奶媽家就說,「請替我解開衣服,我喘不過氣來了。」
他一把摟住了她的腰。
「不!」她說,「是風吹動了一扇開著的天窗。」
「快三點了。」
「好啦!有啦!」
「太太!太太!」費莉西特一面進來,一面叫著,「太可怕了!」
她停下,讓一匹黑馬走過,馬在車架裡踢前蹄,駕車的人是一位穿貂皮衣服的紳士。是誰?……她認識他。……車子駛過去了,不見了。
他們去了布羅尼旅館,在他們的臥室裡。
「誰招惹她了?」奶媽問自己,「她為什麼到這兒來?」
「怎麼?」
「先生,我在等!」
早晨九點鐘的時候,她被廣場上的人聲吵醒了。菜市場周圍有一群人在看佈告,那一張大佈告是貼在一個木樁上的。雨斯丹爬在一塊界石上撕去佈告,但是,在他要撕的時候,地保用手抓住了他的衣領。歐梅也從藥房裡出來了,勒佛杭絲瓦太太像在人群之間演說。
「應該用鞭子打這種女人!」杜法施太太說。
「歐梅先生,菜市場附近,夠出名的。」
「你呀,你是個窩囊廢!」她說。和*圖*書
第二天,當哈杭律師——法警——帶兩個證人來她家記錄沒收的物品時,她以堅忍的態度任他們擺佈。
因為這樣就更應該想想辦法,弄三千法朗並非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雷翁可以替她擔保。
登記完了房間以後,他們上了頂樓。
「怎麼樣?」
「妳要我怎麼……?」
然後,他把麵包掛在網帶上,光著頭,交叉著雙臂,做出一副拿破崙沉思的樣子。
「你聽我說,我需要八千法朗。」
雷翁就要來了。那是一定的!他一定會弄到錢。但是他也許會去她家,因為他不知道她在這兒,於是,她叫奶媽去她家把他帶來。
「有什麼事,波法利太太?」
「波法利太太,妳真那樣想嗎?」
請她坐下以後,他開始吃早點,一面請她原諒他的不禮貌。
終於,那兩位女士覺得聽見了法朗那兩個字,杜法施太太低聲說:
兩點鐘的時候,她跑去雷翁的住所,敲門。沒有人開,他終於出來了。
她喘著氣走到了律師的鐵柵欄門前,天很陰沉,還飄著一點雪。
一個大瓷壁爐的火熊熊地燃燒著,上面的壁龕上放著一盆仙人掌。橡木壁紙上掛著一幅施特來的「艾絲梅拉達」和壽平的「菩提法」,兩幅畫都配著黑木框。早餐準備好了。兩個銀暖鍋,水晶門鈕,地板和家具都乾淨得發亮,很英吉利式的。在每個角落裡,玻璃窗都是彩色的。
當車子再動身的時候,歐梅突然從窗口俯身向外說:
律師知道她的處境,因為他和那個布商暗中有來往,有人向他抵押貸款的時候,他總能在布商那兒弄到現金。
「你厚顏無恥地趁人之危,先生!我雖值得同情,但是我不出賣自己!」
「啊!不在這兒!在我們家。」
這個疑問句的意思是:
「妳靠近壁爐嘛!……再高點……靠著瓷板。」
那時,她記起了某一天。那一天,她帶著焦慮和希望走進了那寬廣的教堂中部,教堂中部伸展在她面前,但是沒有她的愛情深厚。她繼續行走,在面紗下哭泣,頭昏昏的,步履蹣跚,幾乎要暈倒。
他勸他喝好酒,喝好啤酒,吃好烤肉。瞎子繼續唱他的歌,而且他像個傻瓜。歐梅終於打開了他的錢包。
「她是來向他訂貨嗎?」杜法施太太說。
伊維大聲表示懷疑他治瘰癧症的方法。但是,藥劑師保證用他自製的消炎膏能治好他的病,並給了他地址:
第二天是星期天,她去了盧昂,尋訪所有她知道姓名的銀行家。他們或是下鄉去了,或是在旅行中。但她不灰心,凡是她找到了的,她都向他們要錢,說她需要錢,她會還的。但是他們都拒絕了,有幾個還嘲笑她。
「表面上很像。」
一如往常,那個瞎子乞丐在山腳下出現了。歐梅說:
她跳起來說:
「妳家沒有人!」
「妳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也許一千來個銀幣就能使對方不鬧了。」
「讓要發生的事發生吧!」她向自己說。
然後,他又重寫一遍,把筆插|進手裡拿著的牛角墨水瓶裡,蘸了一下。
她仰著臉躺
m.hetubook.com.com在那兒,一動也不動,眼睛直直的。雖然她用一種木然的眼神凝視,她還是只能隱隱約約地看見一些東西。她注視著牆上的剝蝕,兩塊相對著冒煙的木柴,一隻在她頭上的樑縫裡爬行的長長的蜘蛛。終於,她把思想集中起來。她回憶……有一天,同雷翁……啊!多麼遙遠……那天,太陽照著河面,鐵線蓮吐著芬芳……回憶像一條澎湃的急流帶走了她,不久她又回憶到前夕。
她全都試過了,如今再也沒有什麼好做的。那麼,當沙勒回來的時候,她應該向他說:
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瘋狂地吻了一下,然後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膝上,他一面甜言蜜語,一面小心地玩弄她的手指。
「妳是因為他的男傭人而認識男主人的,那男主人有時談起過我嗎?」
一想到波法利佔上風就使她憤怒。不論她供認或是不供認,等一會兒或是明天,他都會知道那場災禍,那麼要等那場可怕的爭吵,忍受他的寬宏大量。她又想再去找勒何,可是又有什麼用?給父親寫信嗎?太遲了。也許她現在追悔沒有順從另外那個男人。她忽然間聽見沙勒的馬蹄在園徑上躂躂地響,是他,他在開柵欄門,臉色比石灰牆還更蒼白。她跳下了樓梯,急忙逃到廣場上,市長夫人在教堂面前和雷斯迪布多瓦談話,看見她去稅務員的家。
「我知道……讓我一個人呆一會兒。」
「先生,」她說,「我想請你……」
漸漸地,在她眼前掠過的熟悉的風景使艾瑪忘卻了目前的痛苦。一種不可忍受的疲倦使她精疲力竭。到家的時候,她是在一種呆癡和絕望的狀態中,幾乎要睡著了。
他把信封斜著舉起來,輕輕地,像是要讓信封裡的金幣掉出來似的。看見那隻肥胖的手放在那些信上,她生氣了,在那些信裡,她的心曾跳過,而那些手指是紅紅的,軟得像肉蟲一般令人噁心。
一定是她在向他建議一件可怕的事,因為稅務員(他是個勇敢的人,他曾經在寶陳打過仗,在盧陳打過仗,曾經參加過法蘭西之役,十字勳章的候補名單上也有他的名字)突然像看見了蛇,後退了一步,一面說:
「她好像在求他允許她緩繳她的捐稅。」
艾瑪說:「沒有怎麼樣。」
「得了,你忙了一陣子,只是要演戲給我們看。」
「這是瘰癧症!」藥劑師說。
「啊!沒有人。先生在哭,他叫妳,大家都在找妳。」
「我不懂當局為什麼還容忍這種犯罪的行為!應該把他們關起來,強迫他們工作。說實話,進步慢得像烏龜的步子!我們還停頓在野蠻時期!」
他又說:「妳從前為什麼沒有來找我?」
於是,他拿鑰匙,她阻止了他。
她們看見她在踱方步,端詳靠著牆放的餐巾圈子、燭臺、欄杆的柱頭。同時,畢內滿意地摸自己的鬍子。
費莉西特在門口等她。
雖然他認識那個可憐人,他還是假裝第一次看見他,且一面嘀咕著「角膜」、「暗角膜」、「鞏膜」、「面貌」等字樣,然後他用慈祥的語氣問他:
他握了她的手,覺得她的手毫無生氣。艾瑪再也沒有力氣表達任何感覺。
晚上的時候,沙勒顯得有心事。艾瑪用充滿了痛苦的目光窺視著他,覺得在他的皺紋裡看出了責怪。然後,她的目光落在裝飾壁爐的中國屏風上,落在大窗簾上,落在沙發椅上,總之落在一切使她苦澀的生活變為溫甜的東西上。那時,她感到後悔了,一種大悔恨,那悔恨不但不毀滅她的熱情反而激起她的熱情。沙勒安安靜靜地撥著爐火,兩隻腳放在鐵篦子上。
「啊!https://www.hetubook.com.com別轉了!」她輕輕地說,以為聽見的是畢內的切木機。
「以前我不知道。」她說。
她立刻告訴他被沒收家產的事,向他說她的困苦;因為沙勒什麼也不知道,她婆婆討厭她,父親無能為力,只有雷翁能為她奔走,去弄那筆不可缺少的錢……。
然後,她注視他。
「不過,假如妳三點鐘不見我來,就別等我,親愛的。現在我該走了,再見,請原諒我。」
「可能嗎?他們不會願意的!」
「太太,假如我是妳,我就去紀尤曼先生家。」
「妳瘋了!」
可是,奶媽老是不回來。也許,因為茅屋沒有鐘,艾瑪怕自己也許誇大了時間的漫長。然後,她開始在花園裡漫步。她沿著靠籬笆的那條小徑走,又急忙地回來,因為怕何雷嫂走另一條路回來。最後,她等得厭煩了,起了疑心卻又拒絕懷疑,也因為不知道她在這兒呆了一個世紀或是一分鐘,她在一個角落裡坐下了,閉上眼,蒙住耳朵。這時柵欄門響了,她驚跳了起來。她還沒有開口,何雷嫂就先說了:
「妳覺得那是辦法嗎?」
「假如我是你,我會弄到。」
畢內臉紅了,直到耳邊,她握住了他的手。
她倒在床上,嗚咽著。何雷太太用一條裙子把她蓋上,站在她身邊,因為她不答話,那好心的女人就走開了,拿起紡輪紡麻。
主僕二人默然地互相注視。她們之間沒有秘密。費莉西特終於嘆了一口氣。
是,就是他,那子爵!她回過頭,街上沒有人,她覺得那麼疲倦,那麼憂傷,她只有靠著牆,否則便會摔倒。
「是人在上面走路?」沙勒問。
「我有話和你講。」她說。
但是因為切木機轉動發出的響聲,她聽不見她的話。
哈杭律師穿著一件薄薄的黑禮服,打著白領帶,鞋底間的皮帶繫得緊緊的。他不時問:
「走開!你踩著的地毯不再是我們的。在你家裡,你不再有一樣家具、一個別針、一根麥草,而毀了你的是我,可憐的人!」
有一會兒的功夫,那沒收品看守者也許是在小屋裡感到無聊,做出了一點聲音。
律師大為驚愕,雙眼瞪著他美麗的繡花拖鞋,那是一份愛的禮物。看見那雙拖鞋,他終於感到欣慰了。再加上,假如和艾瑪有一手,恐怕會牽連自己太多。
「謝謝!謝謝!」
「我的好太太,我這就去!我這就去嘛!」
「太過份了!」
「多麼混帳、多麼下流!多麼卑鄙!」她對自己說,一邊踉蹌地在路旁的白梅樹下逃走。失敗帶來的屈辱加強了她的憤怒——因貞節受到凌|辱而感到憤怒。她覺得上天故意和她過不去,她也因而更加傲慢了。她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自尊心,也沒有如此輕視過別人。有點什麼好戰的心理使她發狂,她想打男人,向他們臉上吐痰,把他們全碾碎!她繼續快步向前走,臉色蒼白,哆嗦著,十分氣憤,一面用含淚的眼睛審視空虛的天邊。憎恨令她窒息,她卻好像喜歡那份憎恨。
「我打攪你嗎?」
他一個人在頂樓,正在用木頭仿製一件無法描述的象牙飾物,由月牙形的東西和一個套一個的空心球構成的,看起來像一座紀念碑,但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他正在做最後一部份,就要大功告成了。在半透明的工作室裡,他的工具上揚起金色的塵土,彷彿一匹奔馳的馬的鐵蹄下迸出火花。兩個輪子轉動著,轟隆有聲;畢內在低著頭微笑,張開著鼻孔,好像沉沒在十全十美的幸福裡面,他也許只屬於平凡的工作,那種工作說難又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它使你感到好玩也滿足你,也實現了夢想,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