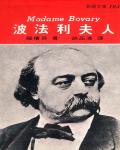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三部
6
附近的咖啡館都坐滿了人。他們看見港口裡有一家小飯店,老闆為他們在五樓開了一個小房間。
「我們同意……妳說?」
因此,某一個星期四,艾瑪大為驚訝,因為她在金獅客棧的廚房裡遇見了歐梅先生;他穿著旅行裝,也就是說,穿著一件別人從未看見他穿過的舊大衣,一手拿著一隻手提箱,另一隻手拿著藥房裡的暖腳器。他不曾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計劃,因為怕顧客因他外出而感到不安。
那個站著的陌生人用好奇的目光左邊望望,右邊望望,他金色的濃眉遮著好奇的目光。他天真地問:
雷翁絕望地看著時鐘,藥劑師又吃又喝又談。
「但是,假如我給你幾千法朗,全數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或是差不多全數?」
「叫妳的傭人好了。妳知道,小乖乖,媽不要人吵她。」
幽會是她的大節日。她要排場!當他的錢不夠開銷的時候,她就慷慨地予以補足,幾乎每次都是那樣。他試著要她明白別處也一樣好,甚至在一個較廉價的旅館裡,但是她反對。
她常常害怕的大叫一聲,沙勒就向她奔來。
「以後再說。」他說,一面轉過身,背對著她。
她跳過了幾行,看見下面的幾句話:
「我送你去。」歐梅說。
她在店裡找到了他,後者正在用繩子捆一個包裹。
然後,他一面打開帳簿,一面說:
自然,想到重訪他渡過青春的地方不禁令他興奮起來,因此他一路都滔滔不絕。一到盧昂,他就急急忙忙跳下車去找雷翁。見習律師想擺脫他也是徒然,歐梅先生拉他去諾曼第咖啡店,他戴著帽子堂皇地走進去,因為他認為在公共場所脫帽很土氣。
他不是開玩笑。但是,因為虛榮心,雷翁不顧一切地否認了。而且,他只愛黑頭髮的女人。
為了籌錢,她開始賣舊手套,舊帽子,賣破銅爛鐵,討起價來毫不讓步——農婦的血液驅使她賺錢。上城的時候,她就買些便宜貨,假如勒何缺貨,一定會向她收買。她買駝鳥毛,買中國瓷器,買箱櫃,她向費莉西特借錢,向勒佛杭絲瓦太太借錢,向紅十字旅館的女主人借錢,向每個人借錢,在各處借錢。她用賣巴納城房子的錢付了兩張期票,另外一千五百法朗又到期了。她又續借,而且永遠那樣。
「啊!毫無辦法。」
她派女傭人去他家找他。但是他沒有來。
勒何從保險箱裡取出了一張收據,那是她收到凡薩預付一千八百法朗的時候給他的。
「這是一件衣料,三法朗半一公尺,保證不褪色!我要是一叫起來呀,大家會搶著買。其實,妳明白,我才不向他們說真話。」他想用這種騙人的話使她相信他為人正直。
「黑種女人呢?」見習律師問。
「我要讓別人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我會告訴我丈夫……」
「至少,讓我知道價錢?」
她哭了,甚至叫他「我的好勒何先生」。但是他把一切推在「凡薩那混蛋」身上。而且,他自己一分錢也沒有,現在誰也不付給他錢,人家啃他背上的皮,一個像他那麼窮的生意人無法替她墊錢。
於是,由於怯懦,由於愚蠢,由於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他讓藥劑師帶他去布立杜家裡。他們看見他在小院子裡,監督三個男孩喘著氣轉動一部機器的輪子,製造塞爾茲水。歐梅給他們提供了一些意見,吻了布立杜,喝了健胃飮料。曾有十二次,雷翁想走,但是藥劑師抓住他的胳臂說:
因為雷翁堅持要去事務所,藥劑師說:
「怎麼?」
「走。」(他說的是英文)
她詭辯:她事先不知道……這一切是沒有料想到的事……。
走到布羅尼旅館門口的時候,雷翁突然丢下了他,上了樓,發現他的情婦焦急萬狀。
「瞧!」
「啊!很簡單!法庭審判,然後是沒收家產……哎!」
然後,他比一個扒手還快,用藍紙把花邊包起來,塞在艾瑪手裡。
於是,他抑制自己。
「是的,疏通凡薩先生。妳不知道他的為人,他比阿拉伯人還凶。」
但是有一次,她家裡來了一個瘦削的,羞怯的,秃頭的男人,說是盧昂的凡薩先生派他來的。他綠色的長大衣側面的口袋上別著許多別針,把口袋封得緊緊的。他取下了那些別針,別在袖子上,有禮貌地遞給她一張紙。
「啊,隨便你m.hetubook.com.com,我全同意。」
原來有人給他母親寫了一封很長的匿名信,告訴她說「他不務正業,和一個有夫之婦相好」。那好心的老太太立刻看見了家庭裡永恆的禍害,也就是說那無以名之的害人精、妖婦——住在愛情的深處。她寫了一封信給兒子的上司——杜波卡施律師,後者精於此道,和雷翁談了三刻鐘,教他睜開眼睛,敎他認識深淵,說這種越軌的行為會影響他將來的成就。他要他和艾瑪斷絕來往,假如他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至少也該看在杜波卡施的份上犧牲才是。
「不過,我也是迫不得已,有刀架在我喉頭。」
他不敢問她問題,但是看見她那麼有經驗,他向自己說她應該遭受過各種快樂的或痛苦的考驗。從前令他著迷的如今使他害怕。而且她愈來愈想完全佔據他,使他反感。她永遠是勝利者,他因而生她的氣。他甚至試著不再愛她,然而,一聽見她的靴聲,他又變得怯懦,像酒徒看見強烈的酒精一樣失去了意志力。
他一面想,一面覺得他情婦的樣子很奇怪,也許,別人要他疏遠她並非沒有理由。
雷翁發誓說他必須回事務所,藥劑師於是取笑公文和訴訟。「見鬼,冷落一下古日亞斯和巴多勒嘛!大膽一點!去布立杜家,你去看看他那條很奇怪的狗。」
然後,他又叫她回來,讓她看三四尺花邊,他是在一次「拍賣」中買來的。
「我答應你,我再簽……」她說。
他把她輕輕地推向樓梯口。
可是勒何先生該幫忙。
沒有關係。她不快樂,她從來沒有快樂過。為什麼總覺得生活中缺少了什麼?為什麼被她依賴的事物立刻就腐朽?但是,假如某地有一個健壯俊俏的男人,天性美好,既激越又細膩,有詩人的心和天使的外表,像一具鏗鏘的七弦琴,向天空鳴奏哀怨的賀婚詩,為什麼她就不會和他邂逅相遇?啊!多麼不可能!而且,沒有什麼值得追求的,一切都是謊言!每個微笑隱藏著煩倦的呵欠,每種歡樂都隱藏著詛咒,一切的逸樂都隱藏著厭惡,最好的吻也只在唇上留下一種不可實現的慾望——對一種更大的逸樂的慾望。
要不然,姦淫重新燃起了她內心的火焰。她喘著氣,十分激動,充滿著欲|火,她打開窗戶呼吸冷空氣,把茂密的頭髮散開在風中,一面望著星星,一面嚮往王子的愛情。她想念雷翁。為了獲得一次滿足她的幽會,她願意付出一切。
「可是我愛他。」她對自己說。
「你渾蛋!」她說。
女傭人出來了,艾瑪懂了,問他要多少錢才能停止訴訟。
她哭起來了。
「我會給他看……我會給他看!」
說實話,她有時也試著計算,可是她發現有些地方太過份了,因而無法相信。她又重頭算起,越弄越糊塗,索興擱在一旁不再去想。
雷翁和藥劑師在兩點鐘時還面對面坐在飯桌上。大廳空了,爐管是棕櫚形,向天花板攤開鍍金枝葉,攤成圓形。窗外靠近他們的地方,小噴水池在太陽下呼呼嘩嘩地響,打著大理石的水盤,水池裡瓢著水芹和龍鬚菜,三隻麻痺了的龍蝦躺著,緊靠著一堆一堆側臥的鵪鶉。
「勒何先生,我求你緩期幾天!」
「女傭人!」
如今,他也感到厭煩,當艾瑪突然偎在他胸口上嗚咽起來的時候,就像某些人只能忍受少量的音樂,而他的心一聽見愛的喧囂就因淡漠而昏昏欲睡,他已經分辨不出愛情的細緻了。
她希望能夠監視他的生活,她想到要派人在街上跟蹤他。旅館附近總有一些和旅客搭訕的無業遊民,他們會接受她的要求,但是她的自尊心反抗她。
然後,他一面讓木屐踩響店鋪裡的地板,一面領著波法利夫人上二樓。他帶她走進一間小屋,裡面有一張樅木大書桌,桌上有幾本大帳簿,被一根上了鎖的橫鐵條壓著。靠牆的地方堆著一些零頭印花布,下面是一個保險箱,那保險箱非常大,裡面不止放著票據和錢。原來勒何先生還做抵押放款的生意,波法利夫人的金鍊子就是放在那個保險箱裡,可憐的徳利耶先生hetubook•com•com的耳環也是。徳利耶先生是在走頭無路之餘變賣它的,而在干岡布瓦買了一個小雜貨店,在那兒患黏膜炎死了,臉比包圍著他的蠟燭還黃。
但是,寫的時候,她看見另一個男人——她最熱烈的回憶,她最美的讀物,她最大的貪慾構成的魅影——最後,那魅影變得那麼地真實,那麼可接近,她也因感到奇妙而心顫,卻又無法清晰地想像,因為他像一位神,在祂的萬能中飄忽不定。他住在微藍的國度裡,那兒有絲綢的繩梯搖盪,在陽台上,在花的呼吸下,在月光裡。她覺得他在她身邊,他即將來到,在一吻之中把她帶走。而她隨即又摔倒在地上,摔得粉碎,因為那種飄渺的激|情比縱慾更令她疲倦。
「活該!法院承認了。有過判決!妳也收到了通知!而且,不是我要這麼做,是凡薩。」
「不是。」
「一會兒。」
「多漂亮!」勒何說,「現在很多人用來做沙發靠背,很時尙。」
「教訓從來不敗事。」他說。
她為什麼會發脾氣?沙勒用她昔日的神經病解釋一切。他責備自己自私,把她的疾病視為他的過失,想跑去吻她。
如今,她經常覺得全身痠痛。當她收到傳票和貼了印花的公文,她連看都不看。她希望不再活下去或是永遠沉睡不醒。
可是第二天中午她收到一張拒付證明書。那是一張貼了印花的公文,上面用大寫字母印著好幾次「哈杭律師——畢西地方的法警」。看見那張公文,她害怕了,趕忙跑到布商勒何家去。
「於二十四小時之内償還八千法朗,不得延期。」下面甚至還有一句:「逾時不付,即將依法執行,沒收什物及家具。」
她去他家見他,故意裝出毫不在乎的樣子。
「我贊成你,」藥劑師說,「她們更熱情。」
他停了一下,像怕做傻事一般。
艾瑪不說話,咬著一枝筆上的羽毛的勒何也許因她的沉默而感到不安。他說:
她讓他看那張紙。
四旬齋第三周的星期五那天,她沒有回到雍維勒。晚上,她參加了化裝舞會。她穿著一條絲絨褲和紅襪子,梳了一個十八世紀流行的假髮髻,耳朵上掛著小燈籠。跟著喇叭的節奏,她跳了一整夜的舞。早晨,她發現自己在劇院的廻廊裡,在五六個化裝成水手和女卸貨員的雷翁的朋友之間,他們說要去吃消夜。
「啊,吿許他我沒有錢,」艾瑪說,「下星期還。是的,讓他等到下星期。」
然後他不經意地讓她看幾種新貨品,但是依他的看法,沒有一樣配得上她。
「誰?」
「我還可以賣東西。」
「你使我走頭無路!」
「我知道這並不好玩,然而畢竟沒有誰會因這個而死去。既然這是唯一使妳還錢的方法……」
歐梅盡情享受著,雖然他陶醉於豪華更甚於美食。波馬酒卻有點刺|激他的感官。上甘蔗酒炒雞蛋的時候,他發表了一些關於女人的不道德言論。最吸引他的是「摩登」。在一間家具美好的屋子裡,他歡喜女人服飾典雅。就肉體方面來說,他不討厭「豐|滿」。
最後,雷翁不耐煩地問:「我們走不走?」
他們彼此熟悉了,不再因互相佔有而驚喜。她討厭他,他也對她感到厭倦。艾瑪在姦淫之中又發現了像婚姻一般的平淡。
「安涅德!別忘了第十四號的三塊零頭。」
他一面和他在街道上走,一面談他的太太、孩子、他們的藥房和未來;說那家藥房從前多麼不景氣,以及他如何使藥房臻於完美。
那年輕人想擺脫他,說有事要辦。
「而且,只要巴納城的欠款一到……」
那個人一句話也沒說就走了。
「我才不管啦!」他說,一面關上門。
因此,他們常談到和他們愛情無關的事物;寫信的時候談花、談詩、談月亮、談星星,那都是些天真的策略,他們藉那些外援使衰微的熱情復燃。她不斷地答應自己在下一次去盧昂的時候要使自己有更深沉的幸福感,然後又向自己供認並沒有感覺到什麼特殊的東西。但是那種失望在新希望下很快就消失了,艾瑪再回到他身邊的時候更熱情,也更貪慾。她狂野地脫下衣服,扯開胸罩的細帶,細帶在她臀部簌簌有聲,像滑行的水蛇一般。她踮著赤脚走,去再看一看門是否關上了,然後一下脫掉所有的衣服——最後,嚴肅地、默然地,和_圖_書她偎在他的胸前,臉色蒼白,久久地哆嗦不已。
「我是在耍一招。」藥劑師看見雷翁的時候說,「我覺得你並不願意和那個人打交道,所以我來打斷你的尋訪。我們去布立杜酒店喝一種對胃有益處的飮料。」
「是的。」
艾瑪等了雷翁三刻鐘。最後,她去事務所找他。她迷失在各種的猜測中,罵他無情,也責怪自己的脆弱,額頭貼著玻璃窗,就那樣過了一下午。
「好!」歐梅回答說,「再說,我是該再去見見世面,我在這兒生鏽了。我們去看戲,上上館子,我們玩個痛快!」
然後他走到她身邊,用溫和的嗓子說:
然後,她又變得冷靜了,終於覺得她也許寃枉了他。但是,侮蔑所愛的人會使我們疏遠他們。偶像是碰不得的,一碰到的話金粉就會落在手上。
「我也去。等你的時候,我看報紙,或者翻翻六法全書。」
勒何並沒有因而停止工作。有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女孩幫他的忙,她有點駝背,是他的店員也是女厨師。
「你能不能……?」
當天晚上,艾瑪就催丈夫給母親寫信,請她立刻把遺產的餘款寄來。婆婆回信說沒有餘款,清算已結束,除了巴納城的房產以外,他們只有六百鎊的年俸,她會準時送來。
一聽見藥劑師的名字,她就生氣了。可是,他列舉了許多理由;那不是他的錯,她難道不認識歐梅?難道她以為他喜歡和藥劑師在一起?但是她轉身要走,他挽留她,跪下來用雙臂摟住她的腰,姿態很慵懶,充滿著誘惑和央求。
「但願凡薩聽我的話!就這麼說定了。我不浪費時間了,我再豪爽也沒有。」
從前,藥劑師不會說這種話。可是他現在做出一副巴黎人的談笑風生的樣子,他覺得那是一種最好的氣質。一如他的鄰居波法利夫人,他帶著好奇心向見習律師打聽首都的風俗習慣。為了向中產階級人士炫耀,他甚至說俚語:當他想說「我走了」的時候,他卻說「髒地方」,「百貨公司」,「帥人兒」,「公子哥兒」,「布仕達街」,「我砸了它」。
說實話,她對他無微不至,為他準備講究的食物,為他穿漂亮的衣服,用嬌慵的目光注視他,她從雍維勒抱來一束玫瑰花,往他臉上扔,她表示關切他的健康,並敎他為人處世的方法。為了能更長久的抓住他,也因為希望上天能保佑他們,她在他脖子上掛一條有聖母像的項鍊。像一位良母,她問起他的同事。她向他說:
天開始亮了,一大片朝霞在靠近聖.卡德琳那邊蒼白的天空裡擴散,鉛灰色的河在風中顫慄,橋上沒有人,路燈也滅了。
「妳說什麼?」
「得了,說老實話!你否認在雍維勒……」
「我就來為妳服務!」他說。
於是,他閉上眼睛思索,寫了幾個數字,一面說他也有大困難,說事情很棘手,他在玩命。他開了四張期票,每張二百五十法朗,相隔一個月到期。
他突然說:「你在盧昂也許很寂寞,而且你的意中人住得很遠。」
「你瞧!」
「我怎麼向凡薩先生回話?」
「可是……總得講講理。」
怎麼辦?……二十四小時內,就是明天!她想,勒何又想恐嚇她;因為她一下就猜到了他所有的行為,他獻殷勤的目的。令她耽心的是那個誇大的數字。
「按裁判宣告書謄本,茲判決……」
勒何在一張草做的大扶手椅上坐下了,一面說:
「好哇!現在竟用眼淚!」
有一天,她從袋子裡拿出六把小鍍銀調羹(父親送她的結婚禮物),要雷翁立刻替她拿到當鋪裡去。雖然雷翁不高興,他怕受到連累,但還是去了。
「去布立杜家裡嘛!在馬巴呂街,兩步就到了。」
雷翁終於發誓不再見艾瑪。一想到那女人還會替他帶來麻煩和申斥(姑且不論同事們早晨圍爐時取笑他),他就覺得他會自責的,假如他違背誓言。而且他就要升為一等見習律師,是應該嚴肅的時候了。因此,他放棄激|情和想像——因為任何中產階級人士在青春的熱情中(哪怕是一分鐘,一秒鐘)都以為自己擁有偉大的熱情和崇高的希望。最平凡的登徒子也夢想過土耳其女王,每個法院書記官的心中也會具有一點詩人的品質。
「算了吧!」他聳聳肩說,「妳什麼也沒有了。」
「皇上,法律及司法當局命波法利
hetubook.com.com夫人……」
「夫人,妳以為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會一輩子白賣給妳東西,做妳的銀行?說句公道話嘛,我也得收回我放出去的錢!」
「啊!啊!不要那樣嘛!」他說。
艾瑪真想打他,但是忍住了。她委婉地問他是否有辦法疏通凡薩先生。
「那麼,妳聽我說!直到現在,我覺得我對妳夠好了。」
男士們在一個角落裡唧卿噥噥地說話,也許是計算開銷。他們是一個見習律師、兩個醫學院的學生、一個店員。她和他們混在一起,算什麼呀!至於女人,聽她們說話的腔調,她很快就知道她們全屬於最下流社會。那時,她害怕極了,把椅子往後挪,並低下頭。
夫人在臥室裡,誰也不能上去。她整天呆在那兒,像癱瘓了,幾乎不|穿衣服。有時,她點著從盧昂一家阿爾吉利亞人開的鋪子裡買來的宮香。夜晚,她不要丈夫睡在她身邊。她裝出猙獰的表情,她終於把他趕到三樓,她徹夜不眠,看些奇奇怪怪的書,有放蕩的描述,也有血淋淋的場面。
然而,由於購買,由於賒帳,由於借貸,由於簽期票,由於每逢到期以後的續簽,利上滾利,她真的為勒何先生積下了一筆資金,他急著要那筆資金做投機事業。
「至少,假如哪一天我有進帳,我也許能……」
那是她簽的一張七百法朗的借據。勒何雖然說過不會讓那張借據落到別人手裡,但是那張借據還是轉到凡薩手裡去了。
他又說,「妳以為那可憐又可愛的男人不明白妳的盜竊行為?」
「滾開!妳好像想引誘我。」
「啊!別敎訓我!」
「得了!妳朋友多著啦!」
「讓我們看看……八月三號,兩百法朗……六月十七,一百五十……三月二十三,四十六……四月……」
判決?什麼判決?對了,前夕還有人送來另一份公文而她卻不知道;所以她因這些話大為驚愕:
「怎麼了?妳不覺得我老住在藥物的毒氣間會有損健康嗎?女人的性格就是這樣:妒嫉科學,然後又反對最正當的娛樂。不管它,我一定去。有一天,我會去盧昂,我們一起把錢花個痛快。」
「可是,我到哪兒去弄錢?」艾瑪說,一面扭著自己的前臂。
她剛剛懷著恨離開了,他的失約對她是一種侮辱。她在心中數落著他的缺點:他沒有英雄氣慨、脆弱、平凡,比女人還懦弱、吝嗇、優柔寡斷。
於是他俯身向他朋友,吿訴他如何看出一個女人是否熱情。他甚至扯到人類學上去了;德國女人憂鬱,法國女人放蕩,義大利女人熱情。
她說沒想到數目居然那麼大。
「這個,我有什麼辦法?」
「不要和他們來往,不要出去,只想到我們自己,愛我!」
於是,波法利夫人把診費單送到兩三個病人家裡,因為這個辦法非常成功,她就大加利用。寄診費單的時候,她總記得加上一句:「閣下深知外子生性孤高,請勿提及,尙希原宥是幸。」有幾個人寫信抱怨,全被她扣留了。
「哎!我的好朋友。」歐梅太太溫柔地,低聲地說,她害怕了,彷彿覺得丈夫是心甘情願地去冒險。
「是誰的錯?」勒何諷刺地鞠了一個躬,「當我像黑人一般工作的時候,妳卻玩得很好。」
别人開始吃飯了,她卻沒有吃,額頭滾燙,眼皮痠痛,皮膚冰冷。她腦子裡仍然覺得舞池在成千上萬的舞者的脚下起伏著。然後五味酒的氣味和雪茄煙使她頭暈,她昏了過去;有人把她抱到窗口。
他望著她,樣子既精明又可怕。她連五臟也為之顫慄。
「我看夠了妳的簽名!」
「不!沒有用。」
可是,怎麼擺脫呢?儘管她因這種幸福的卑劣而感到羞辱,但是由於習慣或是由於淫穢,她仍然不放手,她一天比一天抓得更緊。因為她希望太多的幸福,所以耗竭了所有的幸福。她責怪雷翁使她失望,好像他曾經對她不忠,她甚至希望有一種災禍使他們分手,因為她實在沒有勇氣下決心分手。
她軟下去了,比受到當頭一棒還更嚴重。他從窗口走到書桌面前,一再地說:
一種金屬聲在空氣裡拖得長長的,那是修道院傳來的四下鐘聲。四點鐘了!而她覺得在那長凳上坐了無限長的時間。但是一分鐘可以包藏熱情之無限,一如小小的空間可以容納一群人。艾瑪活著只為情感忙碌,她比一位大公爵夫人還更不www.hetubook.com.com為金錢煩心。
「你走開!」她說。
「太晚了!」
艾瑪的憤怒,歐梅的饒舌,過飽的午餐,這一切弄昏了雷翁的頭,他猶疑不決,而且藥劑師又一再地說:
但是,臨走之前,他要看一下老闆,向他道賀。
「有什麼事?」
當他聽說郎格羅瓦還沒有把錢付清的時候,他感到驚訝了。然後用甜甜的嗓子說:
有一個牛眼窗開向店鋪。他對著牛眼窗說:
可是他仍然擺脫了藥劑師,奔回旅館。艾瑪已經走了。
於是,她生氣了,提醒他說過的話:不讓她的借據轉到別人手裡;他也承認。
因為對方臉紅了,藥劑師又說:
「你會再來,是不是?」
結婚的頭幾個月,在森林中騎著馬的漫遊,那個跳華爾滋的子爵,唱歌的拉卡迪,這一切都在她眼前掠過……突然,她覺得雷翁也和其他的人一般遙遠。
現在,波法利家可真凄慘極了。你可以看見生意人從他們家出來,怒形於色,灶頭上有手絹,小貝特穿著破襪子,連歐梅太太都覺得太不像話。假如沙勒膽怯地說她幾句,她就粗暴地說那不是她的錯。
晚飯後,他一個人在花園裡散步。他讓貝特坐在他膝上,打開醫學雜誌,試著敎她認字。那個從來不唸書的孩子立刻睜大著憂鬱的眼睛,哭起來了。於是,他安慰她,去噴壺裡拿水在沙上做一道河流,或者折幾枝香附子,把它們當樹栽在花床上,花園裡原就長滿了高高的草,栽幾根樹枝也不會顯得難看。他們欠了雷斯迪布多瓦許多天的工錢!後來,孩子覺得冷,要媽媽。
他慢慢地轉過身來,交叉著雙臂對她說:
「好,我呀,我也要讓妳丈夫看點東西!」
回到家的時候,費莉西德給她看座鐘後面的一張灰色的紙。上面寫著:
她突然溜走了,脫掉了化裝舞會中所穿的衣服,一個人呆在布羅尼旅館裡。她覺得一切都無法再忍受,連她自己在內。她希望像一隻鳥一般飛到一個很遠的、純潔無瑕的、可以使自己變得年輕的空間裡。她走出了旅館,穿過了大馬路,戈施瓦廣場和市郊,來到一條面對著花園的寬街。她走得非常快,郊區的空氣使她冷靜;漸漸地,人群、面具、對舞、懸燈、消夜、那幾個女人,一切都像霧一般消失了。再回到紅十字旅社的時候,她倒在床上,在三樓的小臥室裡,那兒掛著一些畫,全都是內勒塔。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伊維叫醒了她。
然而,在被冷汗覆蓋的頭額上,在期期艾艾的嘴唇上,在茫然的瞳孔中,在擁抱中,雷翁覺得有點什麼極端、隱約而又陰沉的東西微妙地滑到他們之間,使他們不得不分手。
「而且我不提妳先生簽的借據:一張七百法朗,另一張三百!至於妳所借的錢,連本帶利,沒完沒了,算都算不清。我不再管了。」
「你不是在追波法利太太家的……?」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是和我開玩笑吧?」
「現在會發生什麼事?」她問。
「活該,讓他對我不忠好了,管它呢!我在乎嗎?」
她害怕了,求他;她甚至把雪白、美麗的手放在勒何先生的膝上。
可是,她又醒過來了,想到睡在女傭人屋裡的貝特。這時一輛裝滿了長鐵條的貨車靠著牆走過,發出金屬的震動聲。
「我馬上走!我們去『盧昂港燈報』看看報館裡的人,我把你介紹給多馬珊。」
秋天已經開始,葉子飄落了——就像兩年前她生病的時候一樣。這一切究竟什麼時候才終止?他繼續走,雙手放在背後。
那年輕人口吃了。
雷翁去雍維勒看艾瑪的時候常常在藥劑師家裡吃飯。由於禮尚往來,他覺得必須回請。
「是藝術家的愛好。」歐梅說:「伙計!再來半杯!」
「啊,不!」他向自己說,「我會惹她心煩。」
有一天,他們分手得較早。她一個人在馬路上走,看見了修道院的牆。於是她在榆樹蔭下一張長凳上坐下。昔日是多麼寧靜!她多麼羡慕那種不容描述的愛情,那些愛情是她依照讀物而想像的。
她還是繼續給他寫情書。依照她的想法,女人永遠該給情人寫信。
她是站著的;她燃燒著的大眼莊嚴地望著他,幾乎是以一種可怕的方式。然後,眼淚使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粉紅的眼睛垂了下來,她讓雷翁握住她的手,舉向唇邊。那時,一個茶房來了,說有人找他。
「什麼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