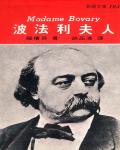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三部
5
這是一種她獲得許可的方式,今後她赴幽會的時候可以無所顧忌。因此,她放膽利用,且盡量利用。她一想著雷翁就找任何藉口去盧昂。有一天,那並非預定約會的日子,所以她去事務所找他。
艾瑪有點弄不清那些帳目,她的耳朵直響,好像金幣漲破了袋子,掉在地板上,在她四周鳴響。最後勒何解釋說,他有一個姓凡薩的朋友是盧昂的銀行家,他可以預付那四張期票。然後他會把清理了債務以後的餘款親自交給夫人。
雷翁繼續在人行道上走。她跟著他,一直到旅館。她上樓,開門,進去……他們擁抱得多麼緊!
假如她不曾向他提起那些期票,那是省得他為家用發愁。她在他膝上坐下,輕撫著他,嬌聲嬌氣的說話,詳詳細細列舉那些賒來的,但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相反地,該等一等,試探那小子。值得去看他一趟。因為她不能去,勒何建議由他替她跑一趟,和郎格羅瓦就地商談,回來的時候,他說買主願意出四千法朗。
「我們現在不快樂嗎?」年輕人慢慢地說,一面用手摸她耳邊那兩片頭髮。
晚上十一點左右,沙勒終於忍不住了,駕著車,鞭策著馬,凌晨二時趕到了紅十字旅社。並沒有找到她。他想,見習律師可能看見了她,但是他住在哪兒?所幸,沙勒記得他上司的地址,他便奔了去。
當他走進那條街時候,艾瑪從那條街的另一端迎面而來。他不是吻她而是向她撲過去,一面問:
「可能!」
「對,我們快樂,」她說,「我瘋了;吻我!」
第二天一大早,艾瑪跑到勒何家裡去請他另做一份不超過一千法朗的帳,因為假如給婆婆看那筆四千法朗的帳,就必須說已付了四分之三,也因而要承認賣了房子。賣屋是勒何作的妥善安排,要等很久才拆穿得了。
「總之,你該承認價錢不貴,因為數量可觀。」
他問:
是禮拜四。她起床後,輕輕地穿衣服以免吵醒沙勒,他會說她準備得太早。然後,她踱著方步,站在窗前,望向廣場。曙光在菜市場的柱子中間流動,藥房的窗板關著,迎著蒼白的黎明,顯出招牌上面的大寫字母。
突然,她把他的頭抱在手裡,急忙吻他的額頭,一面說「再見」,一面奔下樓梯。
每次,雷翁必須向她報告自從上一次幽會以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她向他要詩,為她寫的詩,獻給她的「情詩」;他老是找不到第二行的韻腳,只好從一本紀念冊上抄了一首十四行詩應付過去。
那年輕人相信她,但還是問她那男人是幹什麼的。
她說座落在歐馬勒附近巴納城的那棟破房子並沒有什麼收入。從前是附屬於老波法利賣出去的一個小農莊。勒何知道一切,包括面積和鄰居的姓名。
天已開始亮了。他看見一扇門上的盾章,敲了門。有人在門裡告訴了他雷翁的地址,一面大罵夜裡吵醒人的人。
她立刻收到了一半的賣價。當她付帳的時候,那商人向她說:
下禮拜四午後,在旅館的臥室中,和雷翁在一起的時候,簡直是河流決口!她哭,她笑,她歌,她舞,她叫人把冷飲送上樓來,還要抽煙。他覺得她太過份了,但是卻可愛得無與倫比。
「總之是男人嘛!」
「在郎伯赫小姐家裡。」她回答,一面用手摸摸額頭。
「謝謝妳啦!」老太太說。
她望著那些鈔票。她一面想那兩千法朗所代表的不可數計的幽會,一面結結巴巴地說:
他下星期又來,誇言煞費周章才找到了一個叫郎格羅瓦的人,他很久就覬覦那棟屋子,但是不肯開價。
「說實話,看見妳一下就花光這麼一大筆錢我真難過。」
對丈夫來說,她越來越可愛了,她為他做松仁酪,晚飯後為他彈華爾滋。他覺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艾瑪也無憂無慮地生活著,直到一天晚上,她丈夫突然問:
城市被淹沒在霧裡,從上面傾斜而下,像一個圓形劇場,在橋的那一邊就變寬了。然後是一大片田野以單調的動作往上升起,和朦朧的、蒼白的天邊融合在一起。從高處望去,整個的風景像畫一般平靜。拋了錨的船堆在一個角落裡;河流在綠油油的山腳下蜿蜓,長方形的島像大大的黑魚停在水面上。工廠裡的煙囪冒出一縷縷的棕色輕煙,飛hetubook•com.com散在天空裡。一些教堂矗立在霧中,清脆的鐘聲和鑄冶廠的降隆聲混在一起。馬路上的枯樹在房屋之間形成紫色的荊棘,因雨水而發光的屋頂依著市區的高低像鏡子一般參差照耀。有時,一陣風把雲吹向聖.凱瑟琳山,像汽體的波浪靜靜地使自身粉碎在一方懸崖上。人群裡好像有點什麼令人暈眩的東西為她發散出來,她的心從而脹得滿滿的,好像活在那兒的十二萬人同時把他們的熱情的噓息輸送給他,她假想他們全都有熱情。面對著空間,她的愛情也變得磅礴了,而且隨著模糊的市囂而充滿著騷動。她把愛情傾洩出來了,在廣場上,在林蔭道上,在街上。那古老的諾曼第城在她眼前攤開著,像一個碩大無比的首都,她像是在進入巴比倫。她用雙手扶著車窗,俯身,呼吸著微風;那三匹馬在奔馳,石子在泥地裡發出響聲,馬車搖晃著。遠遠地,伊維和公路上的馬車打招呼,同時在紀尤姆森林過夜的中產階級人士坐著私家馬車靜靜地跑下山坡。
但是羅謨一家人已經不住在盧昂。
「哎!媽,夠了!夠了!」
然後,「燕子」裡的乘客終於睡著了,有的張開著嘴,有的低著頭,靠在身邊的人的肩上,或是用手抓住安全皮帶,隨著車子的顛簸有規律地搖晃。外面,在車尾上搖晃的燈光從巧克力色的布簾上透進來,把血紅的影子投射到所有那些靜止的人的身上。陷入憂鬱中的艾瑪在衣服下面打著寒顫,覺得腳越來越冷,覺得死亡在接近心靈。
「什麼價錢都成!」她說。
「什麼?」艾瑪問。
她要他穿一身黑衣,要他在下巴上留一撮鬍鬚,為了模仿路易十三的肖像。她想認識他的住所,覺得那住所很平凡,他臉紅了,她也不介意,然後勸他買和她家一樣的窗簾。他說太貴。
「什麼?……在哪看病的?……怎麼病的?」
那像是晴天霹靂。不過,她還是回答了,樣子很自然。
然後,她走了!走上大街,到了紅十字旅社,又穿上她早晨藏在長凳下面的套鞋,在不耐煩的旅客之間,縮在自己的位子上。有幾個人走到山腳下去了。她一個人呆在車子裡。
她說付不出。勒何哼聲嘆氣,提醒她說他從前對她多麼好。
親吻之後就是滔滔不絕的談話。他們互相訴說這一個星期來的苦惱。對書信的預感和牽掛,現在都拋到腦後去了。他們互相對視,帶著逸樂,帶著柔情。
她去喜劇街一家理髮廳梳理她中分的那兩片頭髮,黑夜已降臨,理髮店裡有人在點煤氣燈。
「可是,我有她的收據。你來看!」
他第一次嚐到女性的不可言喻的美妙。他從來沒有遇見過那種語言的優美,誘人的衣著,好像在假寐中的鴿子安詳之姿態。他欣賞她心靈的激越,也欣賞她裙裾的花邊。而且,她不是一位上流社會的女人嗎?不是一位有夫之婦嗎?總而言之,是一個真正的情婦!
她俯身向他,呢喃著,好像因陶醉而感到窒息。
「錢是有,但是她要看發票。」
他向自己說:「我瘋了。一定是羅謨先生留她吃晚飯。」
茲收到三個月的學費六十五法朗。
「好了!你走吧。」她說。
「妳瞭解……在商界……有時……請寫上日期……日期。」
他一面注視她,一面把拿在手裡的兩張長長的紙塞在她手裡。最後,他一面打開錢包,一面把四張期票放在桌上,每張是壹千法朗。
這個回答不是防止對方作進一步的調查嗎?而且,一個天生英武而又習慣於人們的讚美的船長居然傾心於她的故事不就是提高了她的身價嗎?
他又加了一句:「坦白地說,價錢不錯。」
這句話像一陣清風,迎面吹來。
丈夫常常注意到她臉色蒼白,問她是否覺得不舒服。
艾瑪倒在長椅上,儘可能平心靜氣地回答:
母親聳聳肩說:「那都是裝出來的。」
艾瑪笑起來了,一種尖銳的、爆發的、持續的笑聲:她神經病又發作了。
她低下頭。他說:
儘管每樣東西的價錢都很便宜,老波法利太太還是覺得開銷太大。
他跑在馬車後面,唱著一首小歌:
可是,他送來的不是兩千法朗而是一千八百法朗,hetubook.com.com因為按照規矩,凡薩先生扣除兩百法朗的傭金和回扣。
晴天的溫暖,
使少女想著情郎。
使少女想著情郎。
她管他叫「孩子」。
可是,三天以後,他走進了她的臥室,關上門說:
這句恭維話使沙勒感到舒暢,因為它用正經的職業掩蓋了他的弱點。
「但是,假如妳沒有現款,妳有房地產呀。」
終於,他用了早餐,披上了粗大衣,點燃了煙斗,拿起了馬鞭,安安靜靜地在位子上坐下。
「見鬼,收據怎麼會在我的鞋子裡?」
「燕子」在柵欄面前停下了;艾瑪脫下了套鞋,換了手套,理好披肩,在二十步之外走下了「燕子」。
艾瑪從頭到尾地熟悉這一條路。她知道過了一處牧場就是一根木樁,然後就是一株榆樹,一個倉房或是修路工人的小屋。有時,她要使自己驚奇,故意閉上眼睛。然而,在對路程遠近的感覺方面,她永遠不會有錯誤。
婆婆繼續教訓她,預言他們會流落到救濟院裡去。而且,是波法利的錯。所幸,他答應了取消那張代理書。
她的心境富於變化,有時很神秘,有時快樂,有時愛說話,有時沉默,有時縱慾,有時不在乎。這種多變的心境激起他心中的萬千慾望,激起本能和回憶。她是所有小說中的戀人,所有戲劇中的女主角,所有詩集中那個不甚明顯的「她」。他在她肩上看見了「沐浴的宮女」的琥珀色;她有封建時代女郡主細長的上身;她也很像「巴爾色隆納的蒼白女人」,她尤其是天使!
「啊,我會找到的。」她說。
那是一張桃花心木做的船形大床。紅緞帳從天花板上垂下,低垂著,呈弓形,繞住寬大的床頭。襯著那深紅的底子,她的棕髮,她的白皮膚比人間任何東西都更美麗,尤其是當她因害羞而合攏雙臂用雙手遮掩面孔的時候。
時鐘指著七點一刻的時候,她走到了金獅客棧。阿德蜜絲打著呵欠為她開了門,又把埋在灰裡的煤炭剔紅。艾瑪一個人呆在廚房裡,不時走到外面去。伊維正不慌不忙地備馬,而且一面聽勒佛杭絲瓦太太說話,後者把戴著棉布帽子的頭從一個窗口伸出來,嘮嘮叨叨地吩咐他辦一些事。換一個人,早就會感到厭煩了。艾瑪用小靴敲著院子裡的石地。
她彎進了一條街。看見露在帽子外面的鬈髮,她認出了他。
她走向書桌,翻遍所有的抽屜,弄亂所有的紙張,卻找不到,終於弄昏了頭,沙勒只好勸她別為那些無聊的收據找罪受。
「妳不是有代理權嗎?」他回答。
有一天,他們像哲學家一樣在談論人世的幻滅,她說(為了試探他的嫉妒心或是因為十分需要傾吐衷曲)在他之前,她愛過一個男人,「不像愛你一樣。」她趕忙說,用她女兒的生命發誓說他們沒有發生過關係。
他們常常一同談起巴黎,這時候,她老是低聲說:
一天晚上,她沒有回雍維勒,沙勒急昏了頭,貝特哭得令人肝腸欲裂,因為媽媽不在她不肯睡。雨斯丹在公路上瞎望,歐梅先生也離開了藥房。
「啊!不必!」勒何說。
打從那時候起,她的生活就只是謊言大全。為了隱瞞她的愛情,她用謊言裹住它,像裹在面紗裡一樣。
「什麼別人?」
「你們男人都是壞蛋。」
望著她的時候,他常常覺得自己的靈魂奔向著她,像水波一樣擴散在她額頭四周,被拉下去,進入她潔白的胸部。
「發票上隨便寫什麼數字都可以呀!夫妻之間的把戲難道我不清楚?」
她叫了起來,這太過份了。
「妳猜怎麼啦?」沙勒說,「剛才在列日阿太太家看見她,曾經和她談起妳;她說不認識妳。」
「我病了。」
「郎伯赫小姐教妳鋼琴,是不是?」
他靈機一動,https://m•hetubook.com.com在一家咖啡館裡要了一本電話號碼簿,急忙找著郎伯赫小姐的姓名,她住何內勒.德.馬洛紀尼耶街,四十七號。
他一面拿起筆,一面在帳單上面寫:「茲收到波法利夫人的四千法朗,此據。」
艾瑪出去了,然後很快又回來了,一面莊嚴地遞給她一張厚厚的紙。
聽見這個好消息,艾瑪喜笑顏開。
他溜出了事務所。
是的,沙勒簽過兩張借據,艾瑪到現在還了一張。至於第二張,那商人答應她的請求,用另外兩張代替,付款期限還延得很長。然後,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未付的貨單:窗簾、地毯、做沙發的布、幾件衣服、各色化妝品,共計兩千法朗左右。
「我需要錢。」
「一定是從發票盒子裡掉下來的,」她說,「盒子放在木架邊上。」
那位代書說:「我瞭解,一位科學家管不了現實生活中許多繁瑣的細節。」
「啊!她一定忘記了我的名字!」
「孩子,你愛我嗎?」
然後,她急忙說:
「但是,妳今晚很奇怪。」他說。
「啊!他向我發過誓說毀掉代理書。」
沙勒在家裡等她。星期四「燕子」老是遲到。夫人終於到家了,幾乎不吻她女兒。晚飯還沒有準備好,沒有關係!她原諒女廚師。後者如今像是為所欲為。
他裝出一副老好人的樣子笑著說:
每轉一個彎,她就更清楚地看見城裡的燈光,那些燈光在一大團屋子上方形成透明的蒸汽。艾瑪跪在車墊上,目光迷失在燈火的輝煌中。她嗚咽著,叫著雷翁的名字,她託風把溫柔的話語和吻寄給雷翁,而這些溫柔的話語和吻都失落在風中。
然而,假如那神父不曾要她解釋,往後別人可能會追究。因此她認為每次在紅十字旅社落腳對她有利,只要村子裡的男男女女在樓梯上看見她就不會起疑心了。
「昨天誰留妳過夜了?」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爐火在假髮和生髮油之間熊熊地燒著。理髮店原就是一間太低的小屋,自然很熱。燙髮箝的味道和弄她的頭髮的油手味道立刻使她頭暈,使她在梳頭衣下面昏昏沉沉地入睡了。替她梳頭的時候,侍者常常問她要不要化裝舞會的票子。
「把帳單留給我。」艾瑪說。
她隨即把代理書扔在火裡。
「不!不!你愛她勝於愛我,你沒錯,那是順理成章的。而且,活該,你等著瞧!保重身體——因為我再不會來和她吵架,像你所說的。」
為了怕人看見,她通常不走捷徑。她沒入陰沉的小巷,流著汗到達國家街的末端,在算近泉的地方。那是戲院、酒店和妓|女的地區。常常有一輛貨車從她身旁經過,載著佈景,佈景直震動。穿著圍裙的工人把沙倒在石板上,在綠色的灌木之間。她聞到茴香酒、雪茄煙和牡蠣的味道。
她常常用溫甜而憂鬱的聲音對他說:
「也許她因為照顧杜布何依太太而住下了。可是她已經死了十年!……那麼,她在哪裡?」
艾瑪說:「不必。她剛出去。但是,將來你可以安心。假如我知道我晚回家一點你就這樣心急,我會覺得不自由,你懂嗎?」
山邊有一個可憐的人,拿看拐杖,在驛車之間徘徊。一堆破布蓋著他們的肩膀,一頂破水獺帽,圓圓的,像一個臉盆,蓋著他的臉。但是,摘下帽子的時候就在眼臉下露出兩個張開的、滿佈著血絲的眼眶。眼白裂成一縷一縷的紅絲,裡面流出液體,一直流到鼻子上,凝成綠疥,同時黑鼻孔一抽一搐往裡吸鼻涕。和你說話的時候,他仰起頭,癡笑著——於是,他淺藍的瞳仁,不斷地轉動,在太陽穴附近和膿瘡碰在一起。
「我就知道是在她家!我正要去。」
一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樣穿著很少的衣服走了以後,突然下雪了。因為沙勒在窗前看天氣,他看見布尼賢神父坐著杜法施先生的車子去盧昂,於是,他走下樓,託神父把一件厚披肩交給他太太,當車子一到紅十字旅社。布尼賢神父就問雍維勒的醫生太太在哪裡。老闆娘說她很少到旅館來。因此,在傍晚當布尼賢神父看見波法利夫人的時候,他告訴她他的為難,不過,她顯得並不重視那件事。因為她開始讚美一位佈道士,說他在教堂裡講得娓娓動聽,所有的女士們都跑去聽。
她聽見戲https://www•hetubook.com•com院裡呼喚伶人上演的鐘聲。看見一些臉色蒼白的男人和化妝已走了樣子的女人從對面走過,走進後臺的門。
「啊!你在乎錢!」她笑著說。
頭幾次,他們很快樂。但是不久雷翁就不再隱瞞實情:他的上司抱怨外人打擾。
當車子走動的時候,他的帽子突然被車窗絆住了,同時,他用另一隻手抓住車子的踏腳板,在車輪濺起的泥巴中。他的聲音首先是微弱的,像嬰兒的啼哭,終於變得尖銳,那聲音在夜間拖長,是一種不清晰的悲號,穿過鈴鐺的鏗鏘、樹的呢喃、車廂的轟隆,聲音中恍惚有一種遙遠的東西使艾瑪感到不安。那聲音沉入她心靈深處,彷彿深淵裡的迴漩,把她帶到一片無垠的憂鬱中。伊維覺察到車子裡多了一個人的體重,伸出鞭子亂打。鞭梢打在他的傷口上,他摔在泥巴裡,一面大聲叫喊。
第二天是可怕的,接著一連幾天都變得不可忍受,因為艾瑪急於再抓住幸福——被熟悉的形象所燃燒的強烈的貪婪,那貪婪在第七天終於在雷翁的愛撫中舒適地爆炸開來。他的熱情則蘊藏在感謝和驚訝中。艾瑪用一種謹慎的、專注的方式品嚐那份愛情,用萬種柔情維持那份愛,也有點害怕將來會失去那份愛。
艾瑪走到窗前叫沙勒。那可憐的男人被迫承認是母親逼他發誓的。
他們彼此面對,一動也不動,一再地說:
音樂教師費莉西.郎伯赫
於是,見習律師覺得自己地位卑微,他羡慕肩章、十字勳章、頭銜。她也許喜歡這一切,他也因而揣側到她有浪費的習慣。
其餘的歌詞裡有飛鳥、綠葉和太陽。
「得了!出來嘛!」她說。
「沒有。」艾瑪說。
「哎!我們能住在那兒多好!」
「他是船長,朋友。」
果然,下星期五,當沙勒在一間小黑屋裡(他的衣物全堆在那兒)穿靴子的時候,他感到鞋襪之間有一張紙,他拿出來讀:
「假如我是妳,把它賣了以後,還了債還有剩餘。」他說。
「燕子」小步跑著,跑上四分之三里就停一停,讓旅客上車,他們在路旁的柵欄門前站著等它。前夕通知過的人姍姍來遲,有幾個還沒起床,伊維又叫又喊又咒罵,然後走上車座,使勁敲門。風從破窗口吹進來。
醫生說:「也許盧昂有好幾個姓郎伯赫的女鋼琴老師。」
有些日子,她甚至一回來就上樓去臥室裡。雨斯丹正好在那兒,他輕輕地走來走去,服侍她,比一個好侍婢還要熟練。他放好火柴、燭臺、一本書,攤平一件睡衣,打開被子。
艾瑪眼前展開了一片可以實現的美夢。她曾經留意,存了一千金幣,付清頭三張到了期的期票,可是第四張不巧是星期四送到家裡的,落在沙勒的手中,沙勒心煩意亂,便耐心地等太太回來解釋。
「星期四見,星期四見!」
「可是,假如我把剩下的錢給妳,不是幫妳忙嗎?」他厚著臉皮說。
「哎!我的上帝!」沙勒說,「哎,妳呀,妳也不對,妳是來和她吵架的!」
「妳簽個字,收起來好了。」
有時,他突然光著頭出現在艾瑪背後。她一面叫,一面避開。伊維剛才和他開了玩笑,他要他在聖.羅曼市集建立一個攤位或是問他的女友一向可好?
他坐在地上,在她腳前。他把雙肘放在她的膝上,伸著頭,微笑著端詳她。
他不知道她整個的生命中有一種什麼反動力驅使她狂熱地奔向生之享樂。她變得易怒、饕餮、縱慾。她昂首闊步和他在街上散步,她說不怕連累自己,可是,有時突然想到遇見何多夫的時候,艾瑪就哆嗦起來,因為她覺得儘管他們分手了,她並沒有完全掙脫他的威力。
溫暖的屋子,潮濕的地毯,逗人的裝飾品,一切都像是為了使熱情方便。帳頂的襯竿末端呈箭頭形。太陽射進來的時候,銅鉤和爐篦的大球立刻發光。在壁爐板上的燭臺之間,有兩個粉紅色的大貝殼,舉向耳邊就能聽見潮聲。
終於,磚屋近了,地在車輪下面鏗然有聲。「燕子」在花園之間滑過,從窗孔裡可以看見一些石像,修剪了的水松,一個葡萄架,一個鞦韆。然後,一瞬之間,城市出現了。
她說找不到買主,他說希望他能替她www.hetubook.com.com找到。但是她問他是否有出售權。
可是沙勒第一次反抗了,替太太說話,使得母親不願再呆下去,她第二天就走,他試著挽留她,她站在門檻上說:
「哎!你會拋棄我的……你會結婚……你會和別人一樣……」
因為他還站著,張大著眼,垂著雙手,好像突然有一個夢纏繞著他。
他們多麼喜歡那間充滿歡樂的臥室,雖然它的華美已經有點褪色了。他們發現家具還是擺在原來的地方,有時他們還發現她上星期四忘記在鐘臺下面的髮夾。他們在爐火旁邊用餐,在一張鑲著紫檀的矮圓桌上,艾瑪切著肉,一片一片地放在他的盤子裡,一面做出種種媚態;當香檳的泡沫從薄薄的玻璃杯裡溢到她戒指上的時候,她笑得既爽朗又放蕩。他們沉緬在一種擁有的幸福中,以為是住在自己的屋子裡,以為會在那兒活到死,像一對永遠年輕的夫婦。說著「我們的臥室、地毯,沙發」,她甚至說「我的拖鞋」,那是雷翁的禮物,她早就想要一雙。那是一雙粉紅緞子拖鞋,上面繡著天鵝。當她坐在他膝上的時候,她短短的腿懸在空中。精巧的,沒有後綁的拖鞋只能靠腳趾掛在她赤|裸的腳上。
「妳有什麼不放心的,既然妳在六個月之內會收到賣房子的尾款,而我又把最後一張期票的限期移到妳收足了錢之後,還怕什麼?」
「啊!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面對著艾瑪,沙勒還是顯得非常窩囊。她一點也不隱瞞她對他的怨恨,怨他不信任她。他求了又求,她才答應重新執行代理權。他甚至陪她去紀尤曼那兒,讓他重做一張同樣的代理權狀。
座鐘上有一個青銅愛神像,擺出一副媚態,弓著雙臂托住祂上面的鍍金花環。他們常常笑那個愛神像,但是,當他們必須分手的時候,對他們來說,一切都顯得如此正經。
「啊!別動!別說話!似乎有一種非常甜美的東西從你眼睛裡流出來,令我舒適。」
「不可以不要地毯嗎?為什麼換了沙發套子?在我那個時代,家裡只有一張沙發給老年人坐——至少在我媽家裡是那樣。我母親是個誠實人,我向妳保證。並非每一個人都富有!任何錢財都經不起亂花。假如我像你們這麼舒服,我會臉紅,而我倒是需要舒服,用為老了。好啊!好啊!修改衣服,瞎講究!什麼?綢夾裡,兩法朗一尺!……用紗布做夾裡就夠好了,兩毛錢就能買到一尺,甚至還不要那麼貴。」
終於,四條小長凳都坐滿了人,車輪滾動著,一排接一排的蘋果樹一閃而過。兩條充滿著黃水的長溝夾著那條公路,越往天邊變得越窄。
然後,他裝著不在意的樣子要一張收據。
沙勒沒有辦法,只好求助於勒何,後者發誓說,假如先生簽兩張期票,一張是七百法朗,三個月內付清,他會好好安排。未雨綢繆,他給母親寫了一封動人的信。母親沒有回信,而是自己來了。當艾瑪想知道有沒有從母親那兒弄到一點錢的時候,他回答:
他這樣做不是由於虛榮而是為了取悅她。對她的觀點,他沒有異議,他接受她一切的喜好,與其說她是他的情婦,還不如說他是她的情婦。她的甜言蜜語,她的熱吻使他六神無主。她這種淫|亂的行為是從哪兒學來的?由於深沉和矯飾,她的妖艷幾乎是無形地蕩漾著。
那時,城市正在醒來。戴希臘便帽的僕人在擦店鋪的門面,街角上不時有些女人大聲叫喊,她們手裡拿著籃子,籃子垂到臀部。她低著頭,靠著牆走,在拉得低低的黑色面紗下微笑著。
不過,有許多妄想,艾瑪並沒有說出來。比方說,她希望坐一部駕著英吉利馬的藍色二輪輕馬車來盧昂,馬夫則穿反口馬筒靴。當雨斯丹求她收留他做隨身小僮的時候,使她有了那種想法。可以這樣說,沒有那種車並不減少赴幽會的樂趣,但是增加回家後的苦澀卻是真的。
她沒有聽見他回答,因為他的唇急速地封住了她的嘴。
然後,她一面沉鬱地推開他一面又說:
可是有一天,勒何看見她挽著雷翁的手從布羅尼旅社走出來。她害怕了,以為他會張揚出去。他才不會那麼笨。
見習律師住的屋子沒有門鈴,沒有門環,也沒有門房,沙勒使勁地敲著窗板。偶然有一個警察走過,沙勒害怕了,只好走開。
「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