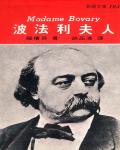第三部
11
他向病人索取未付的診費,他們給他看他妻子的收據。於是他只好向他們道歉。
母親首先試圖和解,提議把孫女帶到她家去,替她解悶。沙勒同意了。但是,動身的時候,他又沒有勇氣了。這一次,他們母子完全決裂了。
對方繼續談農作物、家畜、肥料,拿無關緊要的話填滿空檔,因為害怕沙勒趁機隱射什麼。沙勒並沒有聽,何多夫看出來了,他也看出沙勒面部表情的變動,那變動似乎表示著回憶的掠過。沙勒的臉漸漸地變紅了,鼻孔快速地一開一合,嘴唇也抖動有一會兒的功夫,沙勒帶著陰沉的憤怒用眼睛瞪著何多夫,後者害怕了,不再說話。但是不久,他臉上又恢復了同樣的悲哀表情。
第二天,沙勒叫人把女兒接回來了。她要媽媽。他們告訴她說媽媽出去了,會給她帶玩具回來。貝特說了好幾次,然後就不再想了。孩子的歡樂令波法利傷心,他還得忍受藥劑師不可忍受的安慰。
現在沒有誰來看他們父女,因為雨斯丹逃到盧昂去了,去做雜貨店的夥計。藥劑師的孩子們越來越不和小貝特玩,因為歐梅覺得兩家的社會地位不同了,最好斷絕交往。
但他的痛苦是不完整的,因為周圍沒有人和他分擔。他去看勒佛杭絲瓦太太,為了能談「她」,但是旅店女主人只用一隻耳朵聽,因為她和他一樣有煩憂,因為勒何剛剛設立了驛車站「商業寵姬」而且以推銷著名的伊維又要求加薪,否則就參與競爭。
他一連上了七天教堂,在每天黃昏的時候。布尼賢甚至拜訪了他兩三次,然後又丟下了他。而且歐梅說那教士傾向不容忍主義,傾向迷信,申斥世紀精神,而且在每兩星期講道的時候都說到伏爾泰的臨終痛苦,說他是吃自己的大便死的,大家都知道。
她以為他故意逗她玩,她輕輕地推他,他倒在地上,死了。
奇怪的是,沙勒一面老是想著艾瑪,一面又忘記她。他致力於抓住她的形象,但又覺得絕望,因為那形象老是逃避他。可是,他每晚夢見她,總是同樣的夢:他走近她,但是當他摟住她的時候,他懷裡卻是抱著一堆腐朽。
有一天,當沙勒去阿格依市場賣馬(最後的財源)的時候,他遇見了何多夫。
儘管波法利生活得很節省,他還是無法清償債務。勒何拒絕m.hetubook.com.com緩繳。沒收就在眼前。沙勒向母親乞援,她同意把她的財產做抵押,但是在信裡大罵艾瑪。為了補償她的犧牲,她向他要一條費莉西特沒有偷去的圍巾,沙勒不給,他們鬧翻了。
1.霍亂時期熱心服務;2.自費出版有益於社會的書籍(列舉他的論文「蘋果酒的釀造與功用」,曾送往國家學會的「密毛木虱的研究」,他的通誌,甚至他的藥劑學畢業論文),姑且不論他是若干學會的會員(他只是「一」個學會的會員)。
那個瞎子擦了藥膏也沒有好,又回到紀尤姆森林的山上去了,他向旅客們宣傳藥劑師的無能,因此,當歐梅上城的時候就躲在車窗簾後面,免得遇見他。他討厭他。為了維持自己的名譽,他想盡全力除掉他。他在暗中攻擊他,顯出他智慧的深沉和虛榮的險詐。一連六個月,我們可以在「盧昂港燈報」上讀到這樣的短評:
於是,大家都趁火打劫。郎伯赫小姐索取六個月的學費,雖然艾瑪從來沒有上過一堂課(儘管她曾給波法利看過一張收據),那是她們之間的默契。租書店索取三個月的租金。何雷嫂索取二十來封代發信件的郵資,沙勒要她解釋的時候,她倒是回答得很得體。
每天早晨,藥劑師忙著看報,看他是否已被任命。沒有。後來,忍不住了,他叫人把花園裡的草坪修成榮譽之星的樣子,頂尖模仿緞帶而分成兩條細帶。他交叉著雙臂,在草坪四周散步,一面想著政府的無能和人的忘恩負義。
費莉西特現在穿起夫人的衣服,不是所有的,因為他留了幾件,為了面對那些衣服,他把自己和那幾件衣服全關在她的化妝室裡。她的身材和女主人差不多。當沙勸看見她的背影的時候,他常常會有一種幻覺而且說:
夏天黃昏,他就帶小女兒去公墓。入夜以後才回來,這時,除了畢內天窗裡的光,整個廣場上不再有任何燈光。
看見女兒穿那麼壞的衣服,他非常難過,她的鞋沒有帶子,衣衫從袖口一直破到臀部,因為女傭人一點也不管她。但她是那麼溫柔,那麼可愛,她的小腦袋優美地斜著,讓美好的金髮垂在粉紅的面頰上。他因而感到無限喜悅,喜悅中卻交雜著苦澀,就像敗壞了的酒有著一股松香氣味。和*圖*書他修理她的玩具,給她剪紙人,或是縫好洋娃娃的肚子,假如他在女紅盒子裡看見一條緞帶,或是在桌縫裡看見一個髮夾,他就幻想起來,面帶憂鬱,使得女兒也和他一樣難過。
關於艾瑪的墳墓他也有美好的看法。他首先提議一根半截石柱和有褶疊的衣布,其次是一個金字塔,最後是一個家庭女神的廟,一種圓頂建築或是一堆廢墟。在所有的設計中他都堅持要有垂柳,作為的憂愁的象徵。
他並不放棄藥劑學,相反地,他注意一切新發明。他追隨巧克力大運動,是第一個把「可可」和「補力多」介紹到下色納地區的人。他熱愛普爾維馬赫式的應用水力電池的健康帶子,他自己也佩帶了一條。晚上,當他脫掉法蘭絨背心的時候,歐梅太太因為看見金螺旋而眼花撩亂,當歐梅消失在金螺旋之下,她覺得更愛丈夫了,他比一個西特人還被包裹得更緊,和一位博士一樣光彩。
「昨天,在紀尤姆森林的山坡上,一匹受驚的馬……」接著就說因那個瞎子的在場而發生了意外。
「爸,來嘛!」她說。
「法律雖然禁止流浪,我們大城市的近郊仍然有成群結隊的浪人。有些是獨來獨往的,然而他們並非最不危險的。我們的官員有何看法?」
波法利死了以後,雍維勒前前後後有三個醫生開業,但是都毫無成就,因為歐梅排斥他們,他的顧客多到不可再多。當局照顧他,輿論保護他。
就在這時候,孀居的杜布依太太寄來一張結婚請帖:「小兒雷翁.杜布依——伊伏多的律師——和邦德城的蕾歐卡迪.勒伯夫小姐舉行結婚典禮,謹此奉聞」。沙勒除了寄賀詞之外,還寫了下面這個句子:
至於銘文,歐梅認為最美的是「行人止步」,他只想得出這個。他搜盡枯腸,仍然只想到「行人止步」。最後他想到「愛妻所居」於是就採用了。
可是他覺得新聞的範圍太狹小,他感到窒息。他要寫書,要創作。於是他寫了一本雍維勒通誌,並附上氣侯調查報告。那本通誌又驅使他走向哲學。和_圖_書他關心大問題:社會問題、貧苦階級的教化、養魚法、橡膠、鐵路等等。他因自己是中產階級而感羞恥。他模仿藝術風格,他抽煙。他買了兩個朋巴都夫人時期的小雕像裝飾客廳。
再加上沙勒不是鑽牛角尖的典型,他不敢求證,他那不確定的妒嫉失落在大悲愁中。
七點鐘的時候,一整天沒有看見爸爸的貝特來找他吃飯。他的頭靠在牆上,眼睛閉著,嘴張著,手裡拿著一綹黑髮。
大家驚訝於他的失望。他不再出門,不再接待訪客,甚至拒絕看病。有人說他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酗酒。
何多夫啞口無言。沙勒把頭埋在手裡,用微弱的聲音,用忍讓的、無限悲傷的語氣說:
他向自己說:「也許他們之間只有柏拉圖式的愛情。」
「我不生你的氣。」他說。
他還說了一句偉大的話,他所說過唯一偉大的話:
「我不知道,這是她的事。」
但是,到降臨節的時候,她離開了雍維勒,和德歐多私奔了,而且偷走了艾瑪所有的衣服。
三十六小時之後,藥劑師把卡尼維先生請來了。他加以檢驗,什麼也沒有找到。
他家對面是藥劑師家,一家大小歡樂,欣欣向榮,事事如意。拿破崙幫父親做實驗,阿達莉替他繡希臘帽,薏爾瑪剪圓紙片蓋果醬,富蘭克林則能一口氣能背完九九乘法表。他是最幸福的爸爸,最幸運的男人。
因為,勒何先生又來唆使他的朋友凡薩,不久,錢的問題又開始了。沙勒的負債已達到龐大的數目,因為他不同意拍賣曾經屬於「她」的任何家具。他母親因而生氣,他氣得比她更厲害。他完全變了,氣得她只有丟下家走了。
最後,他就地轉了一個圈說:「救火工作我也曾參加。」
有一天,當沙勒在屋子裡徘徊的時候,他走上了頂樓,便鞋踩到了一個小小的紙團,他打開了,看見這幾個字:「鼓起勇氣,艾瑪!鼓起勇氣!我不願毀了妳的生活。」那是何多夫的信,掉在許多箱子之間,被天窗裡的風吹到了門口。沙勒呆呆地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而從前,艾瑪也曾站在同一的地方,絕望地,比他還更蒼白,想結束自己。最後,他在第二頁的下面看見一個簽名首字:R,是什麼?他想起了何多夫的殷勤,他突然的消失,以及其後二、三次他遇見他時的窘態。但https://www.hetubook.com.com是信的語氣很莊重,仍然讓他心存美好的幻覺。
「不,我不再生你的氣。」
錯誤!一種野心在暗中啃食他:歐梅想獲得十字勳章。他移資格:
控制這個命運的何多夫反而覺得在這種處境中的沙勒也太好說話了,甚至有點滑稽和卑劣。
於是歐梅向權勢低頭。選舉的時候,他在暗中大大地幫知事的忙。他出賣自己,行為如娼妓。他甚至給國王寫了一封請願書,求他為他主持公道,他叫他「我們的好皇帝」,把他比作亨利第四。
每逢清償一筆債務,沙勒就以為了結了。但是還有其他的源源而來。
有時,一個好奇的人踮起腳從花園的籬笆上面往裡瞧。那人驚愕地看見一個鬍鬚很長的男人,穿著骯髒的衣服,樣子很可怕,一面走,一面大聲哭。
第二天,沙勒在涼棚中的長凳上坐下了。陽光穿過藤架,葡萄葉子把陰影投在沙上,茉莉發出芳香,天很藍,斑螫圍著百合花嗡嗡而鳴,沙勒感到窒息,彷彿一個被情濤淹沒的少年,情濤使他憂傷的心鼓脹。
何多夫在他對面,雙手支頤,一面吸雪茄,一面談話;面對著艾瑪愛過的那張臉,沙勒沉入了夢幻中。他似乎又看見了她的一部份。奇怪:他還真想做那個人。
然後歐梅又編一些故事:
他成功了,瞎子被監禁了,但是又被放出來了。他又開始了攻擊,歐梅也是。那是一種鬥爭。歐梅勝利了,因為他的敵人被終身拘留在一家救濟院裡。
「是命運的錯誤。」
沙勒和他一同去了一次盧昂,去一家墓石店看墓石。還有一個名叫佛夫利拉的畫家陪同他們,他是布利都的朋友,老愛說雙關語。最後,看了一百來張圖樣,估了價,他們又去了盧昂一次。沙勒決定採用皇陵式樣,兩邊正面上雕刻一位拿著一個熄滅了的火把的神像。
這次的成功使他的膽子更大了。打從那時起,每逢有一隻狗被壓死了,有一個倉房焚燒了,有一個女人被打了,他就立刻寫文章讓大家知道,這是由於兩個動機:對進步的愛好以及對神父的憎恨。他把國民小學和教會小學加以比較,極力詆毀後者。為了捐給教會的一百法朗補助金,他提起聖.巴德勒米事件,他揭發惡習,提倡戲謔。那是他的口號。歐梅從事破壞,變成了危險人物。
他剛收到十字勳章。
www.hetubook.com.com見面時雙方的臉色都變了,何多夫只寄了一張弔唁卡,結結巴巴地道了歉,接著膽子變大了(那是八月,天氣很熱),甚至鼓起勇氣請他去酒店喝一瓶啤酒。
一切都變賣了之後,只剩下十二法朗七十五分,用作波法利小姐投靠祖母的旅費。同一年,祖母也死了;老胡歐特先生癱瘓了,是一位姑媽照顧貝特。姑媽很窮,為了謀生,把姪女送到一家棉紡織廠做工。
他想,「他」也許曾經崇拜過她。所有的男人都想得到她,那是一定的,在他眼中,她顯得更美了,他因而有一種永恆的、強烈的慾望,那慾望也使絕望變得強烈而無限,因為那慾望如今無法得到滿足。
對艾瑪的眷戀漸漸消失的時候,他就更愛女兒。她令他不安,因為她有時咳嗽,而且雙頰徘紅。
或是這樣的短文:
「所有前往畢加迪肥沃地帶的旅客一定曾經注意到在紀尤姆森林的山坡上,有一個臉上生了膿瘡的乞丐。他糾纏你,折磨你,對旅客來說,他就像是稅務員。難道我們仍然停留在可怕的中世紀嗎?在那個世紀裡,大家允許曾經參加十字軍遠征的浪人,把他們從東方帶來的痲瘋和瘰癧攤在我們的廣場上。」
「我可憐的亡妻原會感到多麼高興!」
他只好把銀器一樣一樣賣掉,然後又賣客廳裡的家具。所有的房間都一空如洗了。但是她的臥室還和從前一樣。晚飯以後,他就上樓到她的臥室裡去。他把圓桌推到爐火前面,把「她」的椅子拉近,他在那椅子對面坐下。一枝蠟燭在鍍金的燭臺裡點燃。貝特在他身邊,在紙上塗顏色。
由於尊敬,或是因為慢慢的察看使他感到快樂,沙勒始終沒有打開艾瑪經常使用的一張紅木書桌裡的隱密抽屜。有一天,他終於坐在那張書桌面前,旋轉了鑰匙,推開了彈簧。雷翁全部的書信都在裡面。這一次,沒有疑問了。他看完了最後一封,搜索所有的角落和牆背後,嗚咽著,呼叫著,茫然不知所措,他發瘋了。他發現了一個盒子,把它一腳踩破,情書中間,何多夫的畫像赫然在望。
他假想她依然活著,為了討好她,他遵照她的喜好和她的觀念行事。他為自己買了漆皮鞋,他養成了打白領帶的習慣。在他的八字鬍子上灑香水,他和她一樣簽發票。她似乎在墳墓裡教他學壞了。
「啊!別走!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