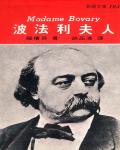附錄
一 摩利斯.巴德施的評論
這一切都是匠心獨具的,的確。那是因為紀律,因為苦修主義,而非依照某種文學理論。福樓貝的過去中,沒有什麼東西使他傾向寫實主義,致使法國小說中的寫實主義傑作,不是摸索和尋求的結果,也不是耐心地在理論家的溫室中成熟的美好果實,而是由於偶然的產生。活動空間之狹小,主題的選擇,細緻的描述是福樓貝寫實主義的淵源。在這一點上,福樓貝、馬克西姆.狄.康,或布依耶都一無所知。福樓貝只是研究諾曼第小鎮裡的一個「心靈之霉」,他也曾以同樣的細心去研究人類的宗教和哲人的幻想,以便寫「聖.安東尼的誘惑」。他不是寫實主義者,主要地是他有責任心。那是他天性中的一個特點,我們在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那個特點。當我們細讀他尚未發表的篇章和筆記的時候,那特點是顯而易見的。他靠職業良心發明了寫實主義。
4、想像力與小說創作
一開始,就有人抱怨。那種抱怨既強烈也眾多,不是一個在工作中的作者所能忍受的。一開始,作者就發覺他的小說「難於起步」。說過那句話之後,可憐的福樓貝就不休止地慨嘆。「可恨的波法利使我痛苦……使我煩厭……我疲倦了,我也失望!……我倦了……波法利折磨我……我累了,比推動一座山更累……坦白地說,波法利令我厭煩。」這些誇張的話是福樓貝在一八五二年七月寫的,也就是說甚至在寫完第一部之前,在開始「真正的小說」之前。
事實上,那本小說的結構,主題、語調、人物等,每分鐘都提醒我們說他寫這本書是為了使自己遵守紀律,為了劃定一個界限,為了反抗對巨著及百科全書的喜好,為了使偉大的抒情運動變為不可能。
所有的傑作都是神秘。經過五十年的悉心研究之後,我們還只是描寫而非詮釋。也許評論沒有別的功能,除了讓人感覺。評論只是介紹,假如它有更大的野心的話,它就變得徒然。「波法利夫人」仍然是一個奇蹟,那奇蹟把福樓貝隱藏起來,讓我們看不見他、他的力、他絕對的虛無主義,或是他淵博的「透視畫」,這一切都不存在於這本書中,我們使他把這本書拿在手裡作為上帝叫他呈獻的祭品,而福樓貝卻為自己架構了那淵博如百科全書的透視畫,他在其上悲苦地讀出了人之命運。法國讀者多麼喜愛完美的花園!在那種花園裡,灌木是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視野柔和而不寬廣,樹群和園徑都適合他們的審美觀念。欣賞「歐琴妮・葛蘭德」的人令巴爾札克生氣。而討厭中產階級的福樓貝居然因最能代表中產階級的一本小說而萬古留芳。在那本「不透明」的小說後面,我們不覺得沉悶,難於呼吸或難於生活。那是一種新的對人生的看法,是一種從來沒有聽過的新音樂,為小說家的小說。那像是現實反映在銅鏡上的光,那閃光使我們欽佩但卻不會使我們著迷。那是形式藝術的勝利,而那本書居然是由這麼一個人所寫的:他曾試圖傾聽一切矮人之歌,他曾讓人為他演奏一切邪惡的音樂。多麼似是而非!假如說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使命,是使我們發現一個沒有他我們原來就永遠看不見的世界,或是把世界的明朗、遼闊、強烈的形象給我們,那麼福樓貝就錯過了作家的命運,而他卻是沙多布里昂之後法國散文中最偉大的魔術師。許多福樓貝的崇拜者下結論的時候總是向你說:「但是,假如你讀他的書簡,那真令人感到狂熱。多麼偉大的傑作!他的書簡向我們洩露他是一個https://m.hetubook•com•com多麼令人感到狂熱的人!」
在此,我們正面對一個體系的、學說的態度。關於作家客觀性的最明確格言並非在「宣言」中找到的,而是在福樓貝給路易絲.柯蕾的書信中找到的。寫那些信的時候,正是他寫「波法利夫人」的時候。
那些句子聽起來像格言,也讓我們看見表達現實那個體系中的絕對。福樓貝曾把那個體系強加在自己身上,那些句子也讓我們看見那種體系有何種限度以及導向何種錯誤。福樓貝是帶著狂熱去宣揚他的法則的。「在我的作品中,我不要有作者的『一』個動向,『一』句話語……這本書裡,沒有任何東西是來自我身上的,我的個性對這本書毫無用處。……在這本書中,沒有作者的個性,沒有作者的話語。」這句話常常被誤解為:「波法利夫人沒有真實性。是一個完全編出來的故事,其中沒有我的情感,沒有我的生活。」其實,波法利夫人是有資料來源的,福樓貝的話不可被誤解為否認資料的蒐集,而是該解釋為對資料的再組織,而作者沒有把自己放入那種再組織中。
假如說作家們的靑年時期就包藏著他們天才的萌蘖,福樓貝的靑年時期並非「波法利夫人」的先聲。自然,在那種破壞偶像的敎徒的不修邊幅中,有一種強烈的苛求,但是那只是引起憐憫的苛求,只是無紀律的強硬。在那段歲月裡,福樓貝的作品卻是雄辯式的、華麗的,只是軟綿綿的畫面上的燦爛裝飾,是嚴格的反面。說實話,評論「波法利夫人」的書佔滿一整個圖書館,可是從來沒有人敘述過波法利夫人的誕生。知道福樓貝如何從德兒芬・德拉瑪變到艾瑪・波法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為何、靠了什麼奇蹟、靠了什麼啟示,他才能經由「情感敎育」中的粗俗和「誘惑」中的喧鬧的畫面到達「波法利夫人」中的和諧線條,靑銅的音響,以及不斷的努力,努力傾向於違反他本性的東西:樸實、線條的純美、敘述的溫柔和流暢。
這種「變成另一個人」的「能」導致了一個結果,那個結果卻和福樓貝天才的另一種形式相距甚遠——「喧鬧」的天賦,因為哈伯雷的這個弟子首先喜愛偏激的語法,喜愛高盧人的大笑,以及厚顏等。他抽煙斗抽得厲害,酒量也大,又是淫穢大字典,於是他在十九歲的時候,把自己看成亞爾西利的輕步兵,他就是那樣的人也想做那樣的人。他和朋友們發明了「男孩」那個角色,由他們每人輪流扮演,使得每次的散步或戲謔的對話更為美麗。尤其在「男孩」一書中,我們看見一個諷刺的人物,但也是佛拉芒地區義賣中的巨人,那群年輕人塑造的「北部英雄」,後者因語言的淫穢而令人害怕。邦達格呂艾的伙伴們同時也是拜倫式的。在「男孩」兩次外出之間的那一段時間裡,他們就評判女人、世界大事和人的聖哲。他們什麼也不相信,他們衡量過所有的大國,參觀過所有的港口。他們的虛無主義就是他們的麻醉劑。他們哈伯雷式的大笑就是對一切問題的答案,也同時是他們的自衛。因為他們原來是弱者就像百年以後出現的和他們類似的人。他們之中有兩人自殺了,人們對那種意外也未加追究。
之後,有關該書之寫作日程就不太精確了,因為從一八五四年八月起,福樓貝突然停正了和路易絲.柯蕾通信。我們只知道,在一八五五年五月hetubook.com.com,福樓貝開始寫第二部了,第二部描述艾瑪與何多夫的戀情,剩下待寫的是第三部。第三部敘述艾瑪和雷翁的戀情以及艾瑪的自殺。當他寫第三部的時候,那本書已經開始了三年半。
然而,福樓貝的秘訣很簡單,那是一種天賦。在「發明實驗室」裡也有一個「高談闊論室」。福樓貝最大的能力(嚴格地說是他的天才)一直是想像力。打從童年時代起,就是想像力給他雄辯,因為他帶著這種力量和這種卓絕看見輝煌的色彩,使得他首先無法避免華美的著色。一般說來,人們以為那只是視覺上的想像。顯然地,確實是視覺上的想像,但是不止於此。也可以說是再現想像。他有「變成別人」的天賦,有把另一種生活給予自己的天賦。睡在沙發上,抽著烟斗,他不僅看見風景,他真是「交趾支那」的皇帝。他暫時變成交趾支那的皇帝,他感覺交趾支那王所感覺的,想交趾支那王所想的。這就是他能為什麼那麼精確地,那麼有深度地描寫想像力在我們身上形成的蹂躪。但是,想像力也是他塑造人物的學說以及他主張作家的客觀性的理由。小說家應該消滅自己,遺忘自己,不再存在,為了變成他所描寫的那個人。在一封寫給他母親的信裡,他說:「你描寫生活、愛情、女人、榮譽,但是有一個條件,你不應該是酒徒、情人、丈夫,或是常備兵。捲入生活裡的時候,你就無法好好觀察,你或是太悲痛或是太高興。」在寫給路易絲.柯蕾的信裡,他的話更像學說:「對於一件事,你越是感覺得少,越能真切地描寫。但必須有一種『能』——使自己感覺到那件事的『能』。『這種能』不是別的,就是天才:觀看時讓眼前有個擺姿勢的模特兒。」福樓貝的書信中,很少有比這句話更重要的句子。那句話向我們洩露他的生活秘訣。對福樓貝來說,藝術代替了一切,甚至生活。別人所設想的生活,他拒絕了,因為他有用想像代替真實的天賦,也因為喜愛想像甚於真實。他過著一百種生活,他是雷翁,他是沙勒.波法利,他是何多夫,他是艾瑪,他體驗過他在「聖.安東尼的誘惑」中描述的薩芭皇后之訪;在宴饗廳裡,他曾坐在皇帝身邊,君士但丁曾在那兒向他請教過。他一寫完何多夫和艾瑪散步那一章以後,他就寫了一封出名的書信給路易絲.柯蕾。沒有任何東西比那一封書信更能為那種卓越的想像力加以界說:「比方說,今天我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既是情夫也是情婦。我曾在森林裡騎馬,在一個秋天午後,在黃葉下面,我是馬、是樹葉、是風、是情侶所說的話、是使他們把眼睛閉上一半的紅太陽,他們的眼皮浸浴在愛情中……在享受了這一切之後,當我回憶時,我想向仁慈的上帝祈禱,表示感恩,假如我知道祂能聽見。」在福樓貝的書信中,約有二十段說及這種「代替能」,用的也是同様偏激的詞句。那些詞句全是這一句名言的變奏:「波法利夫人就是我」。把福樓貝視為小說的榜樣是對的。他固然缺少做一個偉大小說家的成份,但是從來沒有誰像他那樣具有「變成另一個人」的「能」,那種「能」便是天賦,當一個人想把生命賦予假想的人物的時候。
3、寫實主義與古典主義
假如要瞭解小說的真正性質以及小說在福樓貝作品中所佔的地位,我們必須記得他是把波法利夫人作為一種懲戒。波法利夫人是一種練習,他寫波法利夫人的目的是要洗淨他的調色板以及把樸實強加在自己身上。這本作品是一種決裂——和以前一切決裂,和他所喜愛的一切決裂,也是和他一切深厚的傾向之決裂。他用了五年功夫寫波法利夫人。在那五年期間,他不停地說那本作品是一種難題。
那像是畫架上的一幅畫,畫家自願地劃定了畫幅的空間。佈景:首先和圖書是多斯特,幽暗的、一個十字路口,然後是雍維勒,一個鄉鎮。平板的線條,沒有視野,也沒有遠景。主題:一個感到無聊的女人,一個呆板的丈夫,形式最平凡的奸|情。人物的數目也是最少的:四個主角,兩個傀儡,一些跑龍套。結構:非常直線形的,沒有異樣,沒有花腔,沒有技術上的巧妙,一串穿得規規矩矩的唸珠,一個接一個。語調:一層音樂性的表皮使表面光亮,磨去粗糙,像一片潔白的雪覆蓋著不平的地勢,一句接一句的流暢的句子,沒有顛簸,沒有撞擊,滑得像油,柔柔的,懸得很好,由於完美,它像一種幾乎不可覺察的呢喃。
第三部(即最後一部)之進度更不規則了。一八五五年十月,福樓貝寫到艾瑪毒死自己前所想的種種辦法。一八五六年十月初,福樓貝才答應讓他的友人馬克西姆.狄.康在「巴黎評論」上連載,那時,他才定稿,也就是說他費了四年半的功夫寫波法利夫人。
5、一個把福樓貝隱藏起來的奇蹟
2、福樓貝的「學說」
這種清教徒式的小說觀使福樓貝的挑戰變得更嚴重。事實上,那種小說觀的結果不是寫實主義,而是結構上的古典主義,我覺得那種古典主義是「波法利夫人」中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因為這個緣綠故,將近一個世紀之久,「波法利夫人」被視為法國小說的範本,被視為完美的作品,這是由於比例的適中,由於樸實,由於描畫的清純、自然,也由於風格的簡潔和嚴格的美。但是,我們想知道那種嚴格性,那種「波法利夫人」中的古典主義(許多作家日後都被它吸引)是否對小說史的誤解。豐富的題外話,豐富的參考,對感情及行為的不休止評語也屬於自由,幾乎應該說是屬於無政府主義的。而有始以來,自由及無政府主義原是小說的特徵。偉大的小說是大江,席捲全部人生經驗。敘述像流瀉,在敘述的流瀉中,大江拖著論文、私語、哲學架構、詩句。就是形式上的彈性和韌性使小說變得富有。「波法利夫人」不是一條大江,而是一條澄清的運河。在照亮靜靜的運河的日光中,儘管主題大膽,讀者卻可以看出一種恬靜,屬於生活在久遠年代裡的藝術家,那種屬於良好的審美觀和端正的年代。
假如我們介紹波法利夫人只是指出形式上的長處,那是不完全的。對福樓貝的同時代人來說,對所有的人來說,福樓貝在寫「波法利夫人」的時候,改革了心理小說。畫面的細緻,感情的精確,人物的表達給我們一種印象:在小說史中,他樹立了一種全然新穎的風格。福樓貝就是畫家安格兒。那不是過獎。就某一種方式來說,人物的心理照片是福樓貝天才的中心。
總之,我們剛才引用過的福樓貝的話,只是福樓貝在寫波法利夫人時的「航海日記」的摘錄。而且,除了那些話語之外還有些教條。「客觀是力的標誌」。……作者在作品中想像上帝在宇宙中,無所不在,但又無處可見。……人什麼也不是,作品才是一切。……作家只應該留下作品。……最偉大的作品和最偉大的作家從來沒有下過結論;上帝的兒子們不做別的只是使事物再現。自然,伴隨著這些教條的是一些批判:「感情是卑微的東西……我不願把藝術視為情感的水閘。我最討厭做這種事:把自己的情感放在紙上。我甚至覺得小說家沒有表示意見的權利……藝術上的出賣自己令我反感。」
然而,一切偉大的作品所具有的第三度空間,「波法利夫人」卻沒有。「波法利夫人」是小城生活的可愛的寫生畫和照片,那種生活不能被|插入任何一種人生觀。我們只能猜測到作者的一種感覺:對發育不健全的生活的輕視,那種輕視是自然主義派的輕視。選過「波法利夫人」,福樓貝還沒有發現那種賦予意義的觀念,而他曾把深厚的,當不被人知hetubook.com.com道的意義賦予「情感教育」。那意義是:十九世紀的假慈悲,它優柔寡斷,它的對幻想及折衷的傾向,就是中產階級平凡性的詮釋。這種判斷比藝術家對中產階級的輕視要更有意義得多。
1、風格練習
就是他作品的特性解釋「波法利夫人」一書中所具有的和缺少的特質。那可欽佩的波法利主義的研究——一個嬌飾的靈魂的誕生,一位少女心中的劣等貴族主義,那貴族主義使她走入邪途,使她不自覺地變得邪惡,使她變得不可饜足,變得輕蔑,使她面對著無光彩的、繁重的家務事時變得矯飾——自有淵源,但是福樓貝無須尋覓資料和記筆記,因為路易絲.柯蕾本身便是與日俱增的資料,那種資料一定比「露多維卡夫人」的資料還更加重要。因為歐梅、沙勒.波法利、何多夫好像也是現實世界中的忠實抄本,雖然我們沒有找到激發福樓貝塑造那些人物的靈感之源。至於雷翁,他太像「情感教育」中的佛雷德利克,我們只要在福樓貝的青年時期中,去尋找雷翁的怯弱與戇傻的範本,而不必他求。對福樓貝來說,那些小城生活的樣品多得像爬行的蟲——他在「布法和貝丘雪」一書中將用這些字——像在有青苔的石頭下蠕動的黑色、奇怪的昆蟲,像昏睡著的人。他觀察他們,他描畫他們,耐心地、精確地,而不用感情,因為那是他願意做的工作。他也不從中獲得結論。他不批判那種生活,他只是描畫。他也不塑造對比。他也不把那種生活放在社會或生活的更普遍組織中,在那種組織中,小城生活只會像一個縣,像巴爾札克作品中的小城生活。他沒有什麼東西教給人類,他沒有什麼向他們解釋,他甚至沒有向他們描寫什麼。他只願意做個「玩擲柱戲的人」,馬雷布為詩人下定義的時候,也曾說及福樓貝只是答應過自己要畫一個諾曼第的鄉鎮,他畫了一個諾曼第的鄉鎮,如此而已。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福樓貝東遊歸來之後,就開始寫波法利夫人,但是進度很慢。一年以後,一八五二年十月,福樓貝還只寫到金獅客店那一景,當沙勒.波法利和妻子到達雍維勒鎮的時候。第一部只是一種「引入」,而他卻費了一年的功夫。一八五三年七月,他終於寫到了情節的開始:他寫情夫何多夫之出現的那一章。可是,在情節開始之前,還要一段間奏:農產品競賽會的描述。福樓貝說起那段出名的描寫時總是引以為榮,但是他卻費了六個月的功夫才寫完,時為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對福樓貝來說,那種進度還算快的,因為在那次努力之後,寫作速度又慢了下來。一八五四年五月,在兩年半的工作之後,福樓貝還只寫到有關跛腳那一段插曲。那段插曲發生在何多夫引誘艾瑪之前,也就是說發生在真正的情節開始之前。
自然,在他之前還有巴爾札克。在巴爾札克的作品中,畫像的力量並不來自同一的淵源,作畫的方式也不一樣。巴爾札克憑直覺瞭解他的人物,在他們身上把社會喜劇暴露出來。他看出他們之中每個人都是社會動物園中的動物,他開始把那隻野獸歸類,開始以自然主義者的方式描寫那隻動物。他的作品就是那齣龐大的社會喜劇,他讓我們看那隻動物在那龐大社會喜劇中所演的喜劇。那喜劇是由人物的定義所抉擇,那定義是公爵夫人的定義,是小城女人的定義,是「高級環境」的定義,是銀行家的定義,是紈袴兒的定義。當巴爾札克有深度的時候,那是由於他直覺的探測器,是由於天才猝然的占卜術。那種直覺探測器和天才的占卜術突然把人們以為是單純的人内心的後台和深淵(不被人知曉的)揭露出來。但是在福樓貝的作品中缺乏這種東西。儘管在「波法利夫人」一書中有巴爾札克式的小標題,福樓貝對任何歸類漠不關心,他一點也不是布魯式的自然主義者。福樓貝比巴https://m.hetubook.com.com爾札克更精確,更有耐心。他筆下的傻瓜因精確性而令人驚訝,他以完美的方式把他們描寫出來。在巴爾札克的作品中,沒有一個人物可以和歐梅、沙勒.波法利、何多夫比擬的。巴爾札克對傻瓜本身不感興趣,他筆下的傻瓜是傻傻呆呆的收年俸者,或者是傻傻呆呆的退休人員,從這兩種人的定義中,收年俸者或退休人員那幾個字非常重要。艾瑪.波法利,甚至平凡的雷翁都不在巴爾札克的記事簿裡。當巴爾札克發明「波法利主義」的時候,他設想「行省中的繆司」一書中的蒂拿.德.拉.波德黑。那時,令巴爾札克感興趣的不是一個女人的「腐敗」,相反地是她的精力和野心。蒂拿不凋萎,她「燃燒」,她去巴黎,她把女人的生活視為賭博,她帶著賭注,勇敢的賭。至於福樓貝,他看人生活以及毁滅。他像一位做實驗的化學家,他突然看見溶液的顏色,褪色,他揭示溶液表面的薄膜和變色,他注視醋的形成。他在一段什麼描述文中說過「心靈之霉」,他是多麼有理由!他帶著放大鏡在那兒等著。他記載每一種改變,每一條皺紋。他的觀察是「點線畫家」式的,但是沒有中斷。最後他給我們一幅均匀的、延續的、細緻的畫面。我向自己說沒有人能比他更忠實地使現實再現。結構都是顯而易見的。福樓貝的文章一點也不晦澀。他只是把人物的性格配在一起,正如我們讓衣服配合體型一樣。這不是什麼深度。他的作品不像巴爾札克的作品,其中的人物沒有不可預測的動向,沒有突然顯示出來的雙重人格,像我們一不小心踩在一片泥濘的地上。雷翁、何多夫、艾瑪都不令人感到驚訝,因為他們的行為正包括在他們的心理定義之中。只有沙勒.波法利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人物,而作者沒有給他一個公道。福樓貝只在他身上讓我們窺見了不可識辨的心靈底層。那本小說的整個結尾,當沙勒.波法利愛艾瑪,因為她曾對他不忠,因為她那麼美,那麼香,那麼有別於他認識的一切,當他愛墳墓中的她,把她當作娼妓去愛,把她當作一個邪惡的、如皇后的女神去愛(那女神來自另一世界,在路上向他迎面而來),我們好像突然看見另一個福樓貝——那個看到鏡子彼方的那個人,在心靈的彼方瞻望的那個人。
之後,那些格言變得非常出名。那些格言不僅宣揚作家的客觀性而且尤有過之。那些格言把完全的抽離強加在作家身上,而且不許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和超越作品的東西扯上關係,也阻止作家用內心的亮光闡述作品,那亮光是作者將對人及生活的看法偷偷地投射在作品上的。巴爾札克也和福摟貝一樣,在大部份的作品中,他自己都不參與。但是,作者無所不在,由於他在他所描畫的場景和他的作品之間建立的關聯,他的作品是一件巨大的鑲嵌細工,那場景只是鑲嵌細工的一部份,結果,那場景被照亮了,或者不如說那場景有遠景,有幅度,那遠景和幅度不是來自場景自身,而是因為它是現實世界再現的樣本,那世界是全球性的,連貫的,巴爾札克的每本小說只是那世界的一個代表。
在往後的那幾年中,他還是不停地說那種誇張話。他討厭他所描寫的小城的「中產階級人士」。「我幾乎每分鐘都搖身在變,變成令我起反感的人……內容的惡臭令我嘔吐……主題的庸俗也令我嘔吐。在『聖.朱利安傳』一書中,我有如歸的感覺。在這本書裡,主題、人物、效果,一切都非出自我的內心……這本書和我沒有血統關係,像一個不是我所懷的孩子,我覺得是勉強自己寫的,是一件很費力的束西……耗費了非常大的努力。」那主題對他的才能來說是陌生的,因此,他必須強迫自己服從一種紀律。他用這句有暗示性的話概括那種紀律:「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像是一個每個指骨上都有鉛球的人在彈著鋼琴……我患了史詩技癢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