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地下鐵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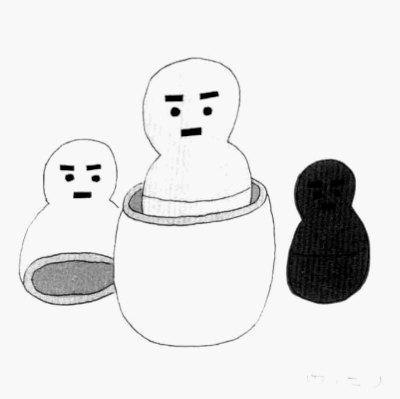
東京地下的黑色魔法
一九二九年十月股價大暴跌的新聞,F.史考特.費滋傑羅是在遙遠的大西洋彼岸北非的沙漠中聽到的。那聲音聽起來像遙遠的空虛回聲般(We heard a dull distant crash which echoed to the farthest wastes of the desert),他事後這樣回顧。對費滋傑羅來說,那個事件在世界歷史上會造成多大的影響,他當時是否能理解?或者華爾街的騷動對他而言,不如妻子塞爾妲精神上的疾病和自己身爲小說家的萎靡不振等個人問題,讓他更心碎也不一定。
這類型的人——周圍可能會稱他們爲「怪人」、「御宅族」——任何社會應該都存在著一定的百分比。而且日本過去的社會往往會視他們爲有益的專家而主動接受他們。他們中有很多進入企業成爲研究者,或留在大學成爲學者,開發新產品,或做專門研究收到成果。他們各自以「日本產業株式會社」的成員被賦予活躍的場所。社會有積極接受他們的餘地,他們也由於被接受,而各自成熟並完成「社會化。」
奧姆真理教的教祖麻原彰晃提供給信徒們的世界觀中,對世界、對生命,可能包含某種貴重的真實。就承認這個吧。我並沒有要連根否定麻原彰晃的宗教思想。就算那只是西藏密教教理方便的翻版,其中——至少在初期階段——似乎確實具有吸引很多人心的primitive(原始的、樸素的、幼稚的)吸引力。而且很多人證言麻原對引出人們體內各種潛能的技術,擁有超越常人的能力。尤其初期的信徒們(說)體驗過麻原親手引發的多數奇蹟式事象,因此他們對麻原發誓一〇〇%忠誠。
那不祥之年,我在遠遠隔著太平洋的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迎接。在波士頓郊外的大學開了一堂日本文學的小班課,每年春天來臨,就參加美麗的波士頓馬拉松跑步,在那之間則寫著長篇小說。離開日本開始在美國東海岸生活已經過了四年。月曆變成一九九五年不久,兩則陰鬱的新聞從日本傳來。不過那時我耳裡聽到的,並不像費滋傑羅所聽到的那樣像「遠方空虛的回聲」。而是聽得很清楚的,不祥的轟聲。
但「社會的經濟發展,並不會就那樣帶來個人的幸福」這件事以實際感受領悟到的第一個世代在這裡出現了。例如就算收入變成兩倍,土地卻比那漲更多,人們也無法在職場附近買到像樣的房子。他們在遙遠的郊外買房子,每天花一小時半到二小時在擠死人的客滿電車搖晃下通勤,爲了還貸款而加班,把寶貴的健康和時間都耗損掉。企業競爭過於嚴酷,也難爭取到帶薪休假。夜晚遲遲回到家時孩子們已經在床上睡熟了。周末假日主要用來休息以消除疲勞。
「你聽到了嗎?」
他們被稱爲「白色世代」。先行的「團塊世代」傾向上是熱烈的、集團性的、攻擊性的、容易落入垂直性思考。相較之下,一般認爲「白色世代」則是冷酷的、個人主義的、防禦性的、思考型態是水平性的。在這樣的意義上,他們或許可以說是在經濟富裕的背景下所出場的日本新人類。
任何國家的歷史,或任何人的歷史,都有幾個戲劇分歧點。例如對美國來說的一九二九年,對凱撒來說的盧比肯河,對希特勒來說的史達林格勒,對披頭四來說的《花椒軍曹》……。在有些情況下,那些是誰都不會漏看的明白轉折點。人們會屏氣凝神,肅靜地通過那地點。但有些情況,要同時感知那衝擊卻很困難。那事件的真正意義,就像長期支票的兌現那樣,要等後日才會安靜來臨。事隔相當歲月之後,人們才恍然大悟「啊!現在回頭看,才知道那是一個分歧點。」
一月十七日上午五時四十六分,巨大的地震沒有任何預兆地襲擊神戶和附近的都市。那是第一個惡夢。寒冷的早晨,離日出還有一段時間,大多數人還窩在溫暖的棉被裡沉沉睡著。人們被崩落的水泥牆壓扁,被房屋活埋,被火災的火焰燒焦超過六千四百人喪失性命。
例如麻原彰晃就以「空中浮揚」和「水中困拔」(在水中不呼吸能停留長時間的修行)當成大賣點。稍早之前,那應該會被當成荒唐無稽的事而從腦子裡排除的。但跑進奧姆真理教裡的「菁英」們,卻不認爲那是荒唐無稽的。他們不僅完全相信那種超能力的存在,還試圖使用電腦來將這些和_圖_書能力理論化、計量化。
日本經濟現在還很富裕,企業和個人都還有足夠儲蓄和餘力可以吸收損失。經濟活動的下降在許多層面,被接受爲軟著陸(soft landing)所帶來的過渡現象。日本經濟確實受了傷,雖然如此依然像「不沉戰艦」般堂堂浮在太平洋的西端。美國經濟還從衰退的傷中尚未完全復原,路上還留有斑斑血跡。德國統一後陷入經濟混亂的泥沼中,辛辛苦苦難以拔腳。
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所出現的日本新宗教,很多和舊有宗教的各派色彩不同,受到從一九六〇年代後半到七〇年代中期對抗文化(counter culture)影響的色彩濃厚。在日本,不像美國那樣受到毒品文化和社區運動的巨大影響,代替的是朝瑜珈開始的東洋神祕思想傾斜的現象很顯著。以這爲主,以崇尚自然爲本提倡重新重視身體性。這些宗派很多情況,標榜超越科學整合性的「超能力」。
他們的世代的一部分會驚人地無防備地被神祕主義式運動所吸引,或許那窒息性可以成爲原因。擁有強烈神祕氛圍的誰從體制外來到,嘩啦嘩啦打開窗戶,送進新鮮空氣,招呼他說「什麼個別差異,沒必要做那麼麻煩的事。到這裡來照我說的做吧」時,他們無法抗拒。因爲沒有足以對抗那引誘的思想支柱。
但地下鐵沙林事件,是日本人——至少就我所能想得起的範圍內——從來沒見沒經驗過的完全不同類的新災難。那是⑴宗教團體以教義的延長所引起的,⑵使用特殊毒氣武器的計畫性犯罪,⑶日本人事實上以無差別殺害日本人爲目的。那所顯示的是,日本是「世界罕見安全而和平的國家」這共有觀念的崩潰。人們一直以爲「我們的社會或許確實有些缺陷」,「但至少,我們是住在安全的社會裡。任何城鄉的任何道路上,都不用害怕遇到犯罪,可以自由走動。這難道不是一種成就?」然而現在連那都變成只是空虛的幻想了。
2正確說是他們證言「察覺師父命令我這樣做」。這可能是只有日本人才有的高等技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爭責任的最終部分消失在黑洞中一樣。
要說是皮肉或許只是皮肉的小事——但也可能完全不只是皮肉的小事——他們所殺的人,並不是企業的菁英,也不是擔負日本體制的高級官僚(據推測他們本來是目標)。在地下鐵車站吸進沙林毒氣陷入呼吸困難,在莫名其妙之下,激烈痛苦中,猛抓喉嚨地死去的,是在體制內每天辛苦勤勞地努力工作的極「普通的人」。我爲了寫成書而採訪了這事件六十多位受害者,知道其中半數以上的人並沒有受大學教育,感到相當驚訝。只有極少數擁有足以和實行犯相匹敵的高學歷。
然而從某個時間點,他們對被社會體制「接受」這件開始猶豫、拒絕。這是重大的轉變。到底是什麼讓他們這樣改變的?答案很清楚。社會本身喪失目的了。說得稍微具體一點,是喪失了眼睛看得見的目的。當被「社會化」變成不是顯而易見的善時,他們開始宣言「No」。那與其說是反抗,不如說處於直率的疑問的延長上。他們所發出的疑問,往往是有道理的。(戰後五十年這麼熱心地工作,繼續追求物質的豐富,結果我們到達什麼地方了呢?我們的社會最終所指向的地點,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呢?)
時間是一九九五年三月二日。星期一。很舒服的初春晴朗的早晨。風還有點冷,走在路上的人都穿著大衣。昨天是星期天,明天是放假日——換句話說是夾在兩個假日的夾縫中,您可能正想「今天眞想休息。」但很遺憾因爲種種原因您無法休假。
事件進行搜查,犯人陸續被逮捕,人們從震驚變成困惑。因爲地下鐵沙林事件的五個實行犯,全都不是一般所熟悉的單純而狂信的「宗教狂熱者」,而是受過極高教育的知性「菁英」。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因此當麻原彰晃的虛構被致命的臭蟲——我想像那可能是他的靈魂裡潛在含有的東西——汙染了時,他們也就被那臭蟲汙染了。一個人的噩夢和妄想把許多人同時並同質地包含進去。於是他們就依照麻原的妄想,或那故事所發揮的黑色魔法,所命令(或暗示)的那樣,抱著沙林的袋子對所謂「統治階層」勇敢地實施虛妄的會錯意的攻擊。他們脫離了一個大體制,接受他們的應該是柔軟的網子,但其實卻是極危險的蜘蛛網。
剛開始從CBS的新聞聽到這則報導時,還沒辦法相信那事件是事實。因爲神戶在全日本是以地震最少的地區之一爲人所知的。我少年時代在神戶近郊度過,在那十八年間記憶中www•hetubook.com.com並沒有經驗過像地震的地震。住在那裡的人應該任誰(包括因地震失去家園的我父母在內)做夢都沒想到,大地震有一天可能會襲擊自己。
因此您在平常的時間醒來,洗過臉,吃過早餐,穿上西裝走向車站。而且和平常一樣上了擁擠的電車要去公司上班。那是沒有任何改變和平常一樣的早晨。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只是人生中的一天而已。
很多人從這事件中感覺到,一個「無邪時代」宣告結束的事實。奧姆眞理教團所嘗試的無差別殺人的被害者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而且那武器可能是比這次所用的沙林毒氣更具破壞力更致命的「什麼」,因爲奧姆眞理教實際上就在開發細菌武器,連核子也納進他們的視野中。他們擁有俄國製軍用大型直升機,甚至意圖購入戰車。
死者人數雖然遠不及阪神大地震,但這地下鐵沙林事件本大大動搖了日本人的精神基礎。日本人是和地震和颱風等自然所帶來的災難共存的民族。說得極端一點,自然所帶來的暴力性已經在精神中無意識地程式化了。人們心中某個角落經常準備著災難的來臨,無論那被害有多巨大、多不講理,都學會咬緊牙根忍耐度過。所謂「諸行無常」是日本人最愛的詞句之一,也就是一切東西都在變遷。日本人是一直繼續忍受崩潰,知道萬事皆空,耐力堅強,會朝設定目標努力前進的民族。
知道了這些事實,許多人大爲震驚。原來他們還想以組織殺害更多人!人們深深不解。到底是什麼樣的精神會鼓舞人衝向那戰鬥性的憎恨?而且那憎恨,是突然變異地產生的嗎?或是我們自己所製造的體制必然地生出來的東西?
4在海外很多情況,彙集沙林事件的被害者、遺族的證言所編成的《地下鐵事件》,和彙集奧姆眞理教信徒、原信徒的證言所編成的《約束的場所》,以合而爲一(並縮短些)的形式出版。
3東京都上班族年收入的五倍能買得到的適當新建獨棟房子(土地一〇〇平方米),一九七〇年是離都心二〇公里的車站附近,泡沫經濟全盛時期的一九九〇年拉遠到距離都心六〇公里的地點。泡沫崩潰後的現在拉回到距離都心四十五公里的地點。
無論如何,後世歷史學家要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歷史時,一九九五年這一年可能成爲一個重要里程碑。那是日本這個國家,大爲激烈轉變她的航跡的年度。話雖如此,但並沒有任何特定個人對那轉變負有責任。就像基里柯(Chirico)畫中出現的那樣,沒有臉和名字的神祕的誰,誰都不是的誰,在昏暗的掌舵室安靜地操著舵。
直到戴著假髮,貼上假鬍子的五個年輕男人,用砂輪磨尖的傘尖,刺破裝了奇怪液體的塑膠袋爲止。
在那樣的狀況下,他們所追求的差異,是無限細分化、技巧化的。結果,不再追求爲了確立自己身分的建設性差異,而變質爲光以差異化爲目的的「沒有出口的差異」。而且和泡沫經濟的出現互相呼應,那差異化變成越需要花錢。朝名牌Armani、BMW,有年分、名貴的Vintage葡萄酒,事情往商品目錄式進展。六〇年代的年輕人所提倡的「理想主義」像鴿子鐘般變成過去的遺物。那種競爭所帶來的東西,在很多情況下,是無限的閉塞感,是喪失目的所帶來的挫折。
在採訪幾個歸依奧姆眞理教的人時,我對他們全體問了一個共同的問題。「你在思春期有沒有熱心讀過小說?」。答案大體一樣。都是No。他們幾乎都對小說不感興趣,甚至有點排斥。有人對哲學和宗教非常感興趣,很熱心地讀那類的書。也有很多人著迷於漫畫。換句話說,他們的心或許主要在形而上的思考和視覺虛構之間來回(形而上思考的視覺虛構化,或相反)。
但很多歸依奧姆真理教的人手上拿到的,是極危險的單程車票。那裡似乎沒有賣往返車票的窗口存在。缺乏像這種公正的informed consent(聽過說明後同意)的虛構,真是非常容易變成「體制方的虛構」。我們很多人可以憑經驗感覺而知道。但沒有「習慣虛構」的信徒,很多沒考慮到那樣的危險,把麻原所提示的虛構和事實混淆在一起,從正面接受下來。而且一度被全面接受的虛構,就會乘著流勢,一直封閉地體制化下去。而結果,正如他們所說的同心圓式地,被吞進麻原彰晃內在的個人的虛構中去。簡直像被鯨魚吞下的約拿那樣。麻原彰晃的虛構一動他們的也動,麻原彰晃的虛構膨脹的話他們的也膨脹。
這篇文章是美國一家雜誌請我對地下鐵沙林事件和《地下鐵事件》這本書寫一篇稿子而寫的,但結果沒被採用。我想大約是2000年稍前寫的。因此,這次是第一次刊出。為了讓外國讀者能更正確理解地下鐵沙林事件的真相,而花時間仔細寫的文章,但我覺得雜誌方面可能期待和這不同類的東西。這種事日本也往往會有。hetubook.com.com
在千代田線造成兩個站員死去的林郁夫(當時48歲)曾經是評語很高的心臟外科專科醫師。在丸之內線造成一個乘客死去的廣瀨健一(當時30歲)是早稻田大學(我的母校)理工學院應用物理學系第一名畢業,進了研究所。同樣在丸之內線造成二百人輕重傷的橫山眞人(當時31歲)在東海大學主修應用物理學。在日比谷線造成一個乘客死亡的豐田亨(當時27歲)從東京大學理學院應用物理學系,進入日本屈指可數的優秀研究室上博士課程。同樣在日比谷線事實上造成八個乘客死亡的林泰男(當時37歲)在工學院大學研究人工智能。
或許聽起來顯得奇怪,但在戰後的日本歷史上,能發出這種根本性疑問是很稀罕的。因爲對先行世代的大半日本人來說,答案是自然明白的。「我們爲了更豐足而努力工作。雖然我們確實還有幾個問題,但當社會本身富裕起來時,問題應該會自然解決」。那是對未來的基本願景。「只要肯努力,事情就會發展性地變好下去。」那認識是無限接近烏托邦幻想的東西,同時也是徹底實效性的命題。
我所採訪的日比谷線通勤的上班族,一邊自嘲地笑著說「不用誰來特地撒沙林毒氣,這電車沒有擠死人本身已經很奇怪了。」這麼擁擠的程度——簡直就是殺人的。有時不能呼吸。因爲車門附近尖峰時間的推擠,就有人手腕骨折。一個女人說在通勤電車上常常站著睡覺。因為從上車後到下車爲止,身體幾乎可以不用動一下。「那簡直就是戰爭。」一個上班族這樣述說感想。「而且,我們每天早晨、每天早晨,一星期五天,到退休爲止三十年以上都不得不繼續這樣。」
「回國來確認一下比較好吧?」
⑵我們的社會體制,似乎有什麼錯誤的地方。
不過麻原對信徒們所提示的世界觀,基本上是一種虛構的故事。也就是說「是超出實證框架之外的東西」。不,我並不是在批判這個。不怕被誤解地說,所有的宗教基本上都成立在故事和虛構上。而且在許多局面上,故事——也就是以白色魔術——能發揮無與倫比的強大治癒力。那也是我們讀到優良小說時往往能體驗到的事。一本小說,一行文字,可以治癒我們的傷,拯救我們的靈魂。但不用說,fiction(虛構的故事或小說)經常必須和現實區分開來才行。有的情況fiction會把我們的實在深深吞噬掉。例如康拉德的小說好像會把我們實際上帶到非洲的叢林深處去似的。但人們什麼時候總會把書頁闔上,不得不從那個地方回到現實來。我們在和那個fiction不同的地方,可能以和fiction相互交換力量的形式,不得不建立起面對現實世界的自己。
這五個實行犯除了全體都是研究理工系學問的「菁英」之外,還擁有另外一個共通項目。當時大多三十幾歲。他們是六〇年代後半的學生運動時代之後進來的「遲到」世代。進大學時,大的政治、文化運動已經結束。鐘擺改變方向,統治階層再度掌握權力。他們眼睛所見的是「宴會後」的慵懶安靜。過去所高舉的理想已經失去光輝,尖銳叫喊的口號已經失去力量,應該具有挑戰性的對抗文化也失去了尖銳性。已經沒有吉姆.莫里森和吉米.韓雀克斯,從收音機聽到的,只是有點莫名悲哀的迪斯可音樂而已。散發著「好東西都被前一個世代吃光了」似的漠然失望感。
他們本來應該是負起日本產業社會中樞任務的人。如果早生十年或十五年,他們可能會活用自己的頭腦和技能貢獻日本經濟耀眼的發展,成爲社會棟樑——非常自然,可能不會懷疑自己。然而他們卻沒有意願朝那條路前進。他們主動脫離社會體制,從世間一般認爲荒唐無稽而危險的神祕主義新宗教中,找到一個代替的新體制。他們辭去社會所尊敬的職位,離開大學的研究室,把所有的財產捐給教團,捨棄了家人,爲追求宗教的理想而出家。而且最後,在教祖麻原彰晃的命令下,執行了殘忍的無差別殺人的事。
「團塊世代」把政治色彩濃厚的意識型態爲主軸的「共有感」放在中心命題,相對地,白色世代反而重視製造和他人間的差異。例如著眼在穿和他人不同的服飾,聽不同的音樂,讀不同的書。當然這沒錯和_圖_書。人應該是自由的,人應該是「不是任何別人的自己」。但事情卻沒那麼簡單。在這裡有個很大的暗中默契的社會規則。所謂「那差異不可超出世間一般認可的範圍」的規則。一方面大主幹是「相同的」,在個別的局面上「和別人稍微不同」。極單純地說,日本還沒有充分整備好接受全面個人主義的基本土壤。這是他們的世代所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麻原彰晃還對人們預言,不久的將來末世決戰(Harmagedon)即將來臨,並強烈主張因此教團必須高度武裝才行。我們在日本這個國家之內要建立另一個國家,必須爲正義而戰。麻原舉出日本國、美國和共濟會爲假想敵。因此他們建立起生產化學武器沙林的全套巨大設備。從俄國購入武器,把信徒團體送進俄國,讓他們在俄國軍人的指導下接受射擊訓練。從信徒的捐獻累積巨額財產充當資金,「菁英」們則收集網站上的情報,調查各種化學武器的製造方法(透過網際網路一般人可以多簡單地得到許多致命性情報,您知道嗎?)。麻原彰晃無疑是個反社會的偏執狂。他高度評價希特勒,把他當成模範角色之一。但他那樣的偏執狂熱,藉著和宗教教義和神祕能力的混合,而獲得一種催眠性幻覺(vision)。在封閉的集團生活中,信徒們徹底接受心靈控制,多數信徒或多或少,都共有那偏執的幻覺。
(史考特.費滋傑羅,《我失落的城市》)
「沒什麼啊。」
相對的,我想嘗試的,是傳達他們被害者也有活生生臉孔和聲音這個事實。他們是不可替換的個體,分別擁有不同固有故事的活著的寶貴存在這回事(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這回事),我想盡量在這本書中顯示出來。我想這應該是小說家的任務之一。小說家或許不得要領,或許很愚笨。但我們不會輕易把事情一般化。
他們可能對所謂故事的成立方式並沒有十分了解。正如您所知道的,通過幾個不同故事的人,對虛構的小說或故事和實際的現實之間所畫的一條線,能自然地找出來。在那之上能判斷「這是好故事」「這是不太好的故事」。但被奧姆眞理教吸引的人,似乎無法找到那重要的一條線。換句話說可能對虛構本來所發揮的作用沒有免疫性。
不管日本在數字上多麼誇耀經濟的繁榮,構成社會的「普通人」,卻很難實際感受到自己得到相應的豐足生活。就像不管多接近,經常都會再遠離而去的沙漠海市蜃樓一樣。所以他們——歸依奧姆眞理教的人們——自己不可能不對容易的社會化說「No」。他們說「或許大家都這樣做,不過我不想這樣。」
在通勤途中遇到地下鐵沙林事件的被害者,三十多歲的上班族中,很多人口中雖一邊對犯行感到憤怒,一邊還——稍微小聲地——補充說「他們會被奧姆真理教吸引的心情,我個人並不是不了解。」令我有點驚訝,也讓我沉思。
我希望您能側耳傾聽人們說話的聲音。
「不——沒什麼啦。」
1二〇一〇年三月的現在,死者人數變成十三人。
「不覺得苦嗎?」我問。
加上日本政府對大地震的危機處理能力,難以相信的拙劣。他們名副其實因驚愕而呆住了,未能迅速敏捷地適當對應。對幾個申請派出救援隊的國家猶豫該接受或拒絕,延遲自衛隊趕赴現地的派遣。時間在無作爲中過去。在那之間許多人在瓦礫下喪失性命。政治家的束手無策和官僚系統的僵硬是很大原因。權力中樞沒有一個人敢說「我下決斷,決斷的責任由我負。」
當我在寫《地下鐵事件》時,想盡量多收集被害者方面而不是加害者方面的採訪,動機是過去日本的媒體上幾乎沒有出現被害者的聲音。大眾媒體的關心集中在奧姆眞理教這個宗教集團,和那身爲師父相貌異樣的半盲男人——從地方上的小瑜珈教室的主持人爬升到巨大宗教組織的師父,謎樣的人物——麻原彰晃身上。因此受傷這邊的人們只受到一種「背景」程度般的對待。他們只是「在電車上共乘的可憐人」。說得極端一點,他們是誰都沒關係。只是在那輛電車上共乘的,吸了沙林毒氣受到傷害的「普通市民」他們沒有臉,也沒有被賦予固有的聲音。像電影上的路人一樣。
然而和表面所見的相反,世界的潮流即將大爲扭轉乾坤。這年春天日圓對美元匯率跌破八〇日圓和_圖_書,創下史上最高價紀錄,那一時看來像要席捲世界般,成爲日本經濟的「史達林.格勒」。像雲霄飛車般的地價暴跌和與那步調呼應的股價暴落,金融機構所保有資產的大部分,慢慢確實地化爲不良資產。就像體內危險的膿悄悄增殖下去般。然後地獄的蓋子終於被打開了。
不,在那之前請您想像如果那是您自己的事。
雖然如此,一般市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多大|波及。在這時間點,決定性受害的,是以股票和土地投機,正謳歌著自己一世春天的所謂「泡沫暴發戶」追求輕鬆容易的暴利,奔走於理財技術的企業,他們的急遽沒落,一般人反而以「健全現象」視之。人們邊搖著頭說「以前反而有點異常」「景氣實在熱過頭了。沒什麼本事的傢伙卻賺了太多錢。這樣一來日本社會總算可以顯得稍微成熟穩健一點了吧。」
一九九五年算是安靜來臨了。那開幕——當然是指現在回想起來——或許有點太安靜。如果這個世界眞的有所謂預言這東西的話,預言者可能會到處用全國的木槌去敲響全國的鐘。但就我所知,沒有一個人做過那種事。新年像平常一樣安靜地來臨,人們像平常那樣元旦到神社去,合掌祈求和平健康和繁榮。吃烤年糕,喝屠蘇酒。干支屬「豬」,在日本豬是被視爲「勇往直前的動物」。不會冷靜觀察周圍的狀況,只會一股勁往前衝。這未嘗不是對所謂日本這個國家的一種比喻,年初應該有不少人有這種感覺。雖說如此,當然比喻終究只是比喻。那只會在比喻上傷人,或殺人。
我所面談過的奧姆眞理教信徒中,許多是從還算不錯的「正常」中產家庭長大的人。他們並沒有遇到不幸的成長方式。都生在極普通的家庭,沒問題地長大。基本上也認眞用功,成績還好——至少沒有很差。面貌長相也不錯(整體上有幾分光滑,有缺乏強烈個性的傾向)。對雙親或多或少具有批判性,但也沒有特別反抗。無法喜歡學校,卻也沒打破校規拒絕上學。對社會懷有不信感,雖然批判物質主義的風潮,但並沒有從內部去改良的社會意識。交友關係大概都狹小,幾乎沒有能敞開心說話的朋友。多半孤獨、耽溺於抽象性思考,對生和死或宇宙的成立認眞地煩惱。對交異性朋友感覺困難。就算交了,也難維持健全關係。大學多半主修理科方面。
問題是,對社會的主要體制喊「No」的人們,能夠接納他們的有活力的次要體制,日本社會還沒有這種選擇存在。這可能是現代日本社會所擁有的不幸和悲劇。只要這種次要體制的缺乏狀況無法根本解決,類似的犯罪就很有可能再度發生。並不是把奧姆眞理教消滅掉就能解決問題。
他稍微歪一下頭。當然不能說不苦吧,臉上表情這樣說。但刻意不說出。因為如果說出口,可能自己內部有什麼會崩潰。他代替地這樣說「你知道嗎?大家都在這樣做。不是只有我這樣。」
然而不安定的暴力性東西,不僅停留在地面而已。在阪神大地震的僅僅兩個月後,人們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三月二十日一個叫「奧姆真理教」的新興宗教團體,用沙林毒氣(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開發的劇烈毒氣,因薩達姆.海珊用來鎮壓庫特人而爲人所知)襲擊東京地下鐵車輛。五個變裝的實行犯,在東京的三條路線進入五輛列車,把裝有二〇〇毫升的液態沙林毒氣的塑膠袋兩個重疊放在地板上,用尖銳的雨傘尖端刺破。星期一早晨的尖峰時段。結果,乘客及地下鐵站員十二人喪生,超過三千個市民被送進醫院。這是不分對象無差別的恐怖行動。東京都內陷入戰後最大的混亂狀態。「這裡簡直就是戰場」電視播報員對著鏡頭喊叫。
「或許該回國的時候已經到了。」我記得這樣想。並開始準備離開新英格蘭。
⑴我們終究是活在,不安定而暴力的地面上。
但當然事情並沒有在這裡結束。奧姆眞理教團,甚至在引起這麼大的淒慘事件之後,許多主宰者已經進了監獄正在接受審判中,然而新的信徒依然繼續加入行列。網路上他們的網站現在還依舊在吸引著許多年輕讀者。人們說這是危險的事。不過那只是,日本社會在結構上所擁有的更大危險的預兆之一而已。
一九九五年,是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敗戰後正好過五十年告一段落的年度。但許多日本人,在這值得紀念的年度,卻下不了決心到底該以什麼樣的心情、什麼樣的評價迎接新年。日本經濟在泡沫破裂的陰影籠罩下,正一點一點逐漸被吞噬。股價可怕地繼續下跌,由於日圓急遽高漲,半導體和家電產業等仰賴外銷的產業,被逼到懸崖邊緣。
這次地震給許多日本國民,帶來兩個極陰鬱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