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淖記事
作者:汪曾祺《大淖記事》是汪曾祺創作的短篇小說,發表於1981年第4期《北京文學》。小說通過書寫小錫匠十一子與挑夫之女巧雲出於自然率真的人性勇敢追求自由愛情的故事,展示了大淖地區的風土人情、民俗世態。
這些帶有濃郁市井氣息的故事,被汪曾祺興緻盎然地付諸筆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經他添些歷史文化的底料,就成了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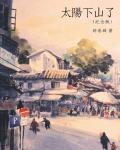
太陽下山了
作者:舒巷城《太陽下山了》是舒巷城1962年創作的長篇小說,作者以簡煉、抒情的筆觸,概括、深刻地描繪了香港某一角的生活面貌。這裡面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濃厚的生活氣息,深摯溫暖的人情;形形色色的眾生相,通過作者藝術的刻劃,細緻入微地展露在人們面前,令人感到親切和生動。
故事以戰後初期,一九四七年的西灣河為主要場景,講述家境複雜的少年人林江如何在賣藝人的情義、生活的暗礁、自身的孤零和文化的啟迪中成長。當中也穿插各種地方人物故事,包括專賣絹面唐鞋的店鋪因不敵西式鞋店的競爭,以水上人為主要客戶的「本土經濟」終於結業。另有從灣仔遷到西灣河,與林江成為鄰居的作家張凡的故事。
《太陽下山了》實為一幅四十年代末香港下層社會的浮世繪,小說沒有描寫尖銳的矛盾和階級的對壘,而以從容的筆墨抒寫香港草根大眾溫馨的人情,從而使作品洋溢著濃烈的人情味。小說通過在苦難生活中充滿憧憬的棄兒林江這一少年的視角,精心勾勒出一個個美麗意象,一種世事滄桑、浮塵變遷的淡淡傷感構成了小說的基調。

石秀
作者:施蟄存《石秀》以《水滸傳》中石秀的故事為依據。在《水滸傳》中,石秀慫恿楊雄殺妻,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為己明冤」,而在施蟄存的小說《石秀》中,石秀慫恿楊雄殺妻則是出於其變態的性慾望,石秀成了一個施虐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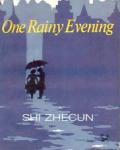
梅雨之夕
作者:施蟄存《梅雨之夕》是心理分析小說家施蟄存的代表作之一。該作同作者的其他小說一樣也描寫了性心理、揭示了潛意識,但與《鳩摩羅什》、《石秀》等小說相比較,《梅雨之夕》顯得文筆舒展,格調清新,艷而不俗。正是這種舒展而周密的心理描寫和素雅清麗的格調,使《梅雨之夕》成為吸引眾多讀者的名作。
《梅雨之夕》幾乎沒有情節,它僅僅記敘了一位下班回家的男子在途中邂逅一位少女之後的一段心靈歷程。但在新穎而豐富的心理分析學理論的指導下,作者以嫻熟的文字表現技巧對人物的心理層層剖析,把讀者帶進了主人公那豐富多彩而又微妙曲折的內心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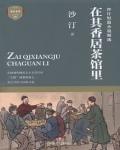
在其香居茶館裡
作者:沙汀《在其香居茶館裡》是沙汀所作的一篇短篇諷刺小說,最初在1940年第六卷第四期的《抗戰文藝》上發表。作品以抗戰時期國統區兵役問題上的內幕為素材,通過聯保主任方治國與土豪么吵吵因抽壯丁而發生的衝突,生動地描繪了一齣官紳之間互相傾軋的鬧劇,深刻揭露當時管治的腐敗,官僚土豪的卑劣,以及他們對人民的欺騙與迫害。
《在其香居茶館里》通過一場「講茶」,把鄉鎮基層兵役黑幕揭露得淋漓盡致。沙汀小說注重運用民俗事象簡潔自然地刻畫人物形象和性格,真實而有力地呈現了風雨如磐、人獸間雜的中國鄉鎮社會形態。小說含蓄,冷峻,苦澀,凝重,撼 動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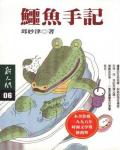
鱷魚手記
作者:邱妙津《鱷魚手記》是已故作家邱妙津最成熟的小說,以大學生活為背景,生活手記為形式,字裡行間充滿纖細的同志情感告白,真摯動人;並以詼諧手法穿插了鱷魚的故事,以「鱷魚」象徵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中的同志,必須穿著人裝、隱身生活。
本書甫發行便震驚文壇,書中「鱷魚」、「拉子」等詞也成為女同志的自稱用語,是台灣文學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
全書分為八個章節,其中大部分章節以大學生活為背景,敘述了七個男女主人公的同性、雙性戀的情感生活和心路歷程,通過解放的性及性別觀點,描繪了當時大學生全新的精神世界和得不到認同的感情經歷給彼此的成長過程帶來的痛苦和收穫。其他章節則以一隻擬人化鱷魚的獨白,另組合成獨立於主要情節之外的寓言,諷刺、影射「鱷魚╱性異常者」在人類社會孤獨、受壓迫的命運。這些彼此穿插的敘事線索以復調雙聲的結構牽動出同一主題的心理及政治層面。
『從前,我相信每個男人一生中在深處都會有一個關於女人的「原型」,他最愛的就是那個像他「原型」的女人。雖然我是個女人,但是我深處的「原型」也是關於女人。一個「原型」的女人,如高峰冰寒地凍瀕死之際升起最美的幻覺般,潛進我的現實又逸出。我相信這就是人生絕美的「原型」,如此相信四年。花去全部對生命最勇敢也最誠實的大學時代,只相信這件事……』——邱妙津

花瓶
作者:歐陽子歐陽子是20世紀60年代的台灣文壇一位有影響的女作家,《花瓶》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歐陽子筆下的「花瓶」已具有超越供人玩賞而趨於自強自立的象徵新意。歐陽子是深受現代主義文學啟蒙的作家,所以她擅長於刻劃女子內在感情的困境,以及潛藏在她們內心被壓抑的心理狀態。

臺灣軼事
作者:聶華苓《臺灣軼事》是聶華苓在臺灣(1949-1964)所寫的短篇小說選集。

死亡的幽會
作者:聶華苓1988年6月發表在香港《博益月刊》上的小說〈死亡的幽會〉,是聶華苓八十年代後期的一篇力作。小說中的主人公邁可、李莉、賽海兒都是現實中的人物,作者將國家、民族、文化、愛情觀的巨變、價值觀的顛倒、人性的升沈,通過人物命運的演進串在一起,深刻表現人性和現實。

西風.古道.斜陽
作者:羅蘭這是一個發生在對日抗戰期間,天津附近農村一個大家庭里的故事,在故事中,可以看到人性的善良,可以看到生命的無奈,也可以找到羅蘭女士年輕時候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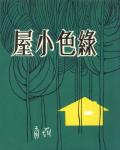
綠色小屋
作者:羅蘭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造物主給愛情以「獨佔」與「見異思遷」的雙重性,致使人間愛情的舞台永不落幕。愛情實在也是與性無關的高格調的精神的奏鳴。惟人的自尊才能抗住愛情危機和失敗所帶來的困惑、頹傷和煩惱。
在淡淡的憂傷、溫婉柔情中呈露著迷人的愛的幻想和光澤……

窮巷
作者:侶倫《窮巷》為戰後香港文壇巨構。小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之香港為背景,通過作家、教師、復員軍人、收買佬、弱女等人物在生活壓迫下的掙扎,刻劃他們在變亂時代的不同命運和際遇,以揭露社會的不平。

驚心動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紀事
作者:路遙文革時期,延川當時是兩派對立組織,一派叫紅色第四野戰軍,簡稱「紅四野」;另一派是延川文化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司令部」。路遙是「紅四野」軍長,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語言,一舉一動,都是「司令部」一派中的真實人物,而縣委書記的形象卻不是當時任延川縣委書記本人。
《驚心動魄的一幕》大約發表於文革末期,當時,延川縣革委會軍事管制小組對「司令部」人員從縣至公社,大隊一級的主要領導人進行了全面的,幾乎是一無倖免的批判、逮捕、判刑。身為縣革委會副主任的王維國便利用軍事管制小組這一行動,把聽到的一句話,見到的一個字都寫到了作品裡;所以,凡看過這篇小說的人都明白,這是一篇完全的、徹底的派性小說。派性就是把本派別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的立場、見解或習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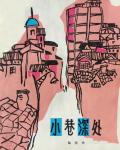
小巷深處
作者:陸文夫在陸文夫50年代創作的短篇小說《小巷深處》中,結局裡的女主人公徐文霞並沒有死,但是她卻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男主人公張俊也是),繼續受著精神上的折磨,也許這種折磨給她帶來的威脅比死還要可怕,徐文霞與張俊的愛情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這正是作品的內涵所在。

美食家
作者:陸文夫《美食家》是陸文夫「小巷文學」的代表作,1983年發表於『收穫』。作家在《美食家》中精緻描摹了古城蘇州的風土人情,園林風景、吳越遺跡、風味小吃、吳儂軟語、石板小巷、小橋流水……無不栩栩如生。這些蘇州特有的文化與風俗,成為他小說中的重要的情節要素,具有獨特的文化地域魅力,使其小說贏得了「小巷文學」和「蘇州文學」的美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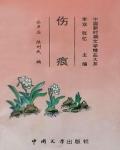
傷痕
作者:盧新華1978年初,24歲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盧新華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傷痕》。他將自己的作品交給朋友和老師閱讀,反響平平。之後,在一次班級策劃的牆報上,盧新華貼出了這篇小說。令他毫無思想準備的是,在復旦校園,這篇小說被迅速傳抄。牆報欄前人潮湧動。當年8月11日,在反覆醞釀和修改以後,《文匯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這篇7000餘字的學生作品。因為《傷痕》,當天的《文匯報》加印至150萬份。一夜之間,「盧新華」這個名字為國人所熟知,「傷痕」一詞很快成為一種文學思潮的名稱,「傷痕文學」也經由這篇小說發軔、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