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喜憂國
作者:張大春《四喜憂國》為張大春短篇小說集,收錄了張大春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創作。這些小說多發表於八〇年代,震撼了當時的台灣文壇,是張大春最初的小說經典。基本囊括了他初期的成名代表作:1975年得到第九屆時報小說甄選首獎的《將軍碑》、當年題材大胆「犯禁」的《四喜憂國》等一篇篇熱鬧又有門道的短篇作品。
《四喜憂國》於一九八七年發表後,被譽為張大春「黑色幽默」的代表作。故事中的主人公朱四喜,他是一位極為愛國,但身份渺小、知識不多、且生活艱難的退伍軍人,他的心願只是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藉以喚醒國民謹記要提防共產黨、反攻大陸。而他這個憂國憂民的心,正好與文中那個「越來越糟的世界」形成強烈對照。

公寓導遊
作者:張大春本書由14篇小說,在不同的時間完成,但卻一致的表現張大春語言遊戲,新的小說遊戲特色,一部部掠影而過的情節,都像解嘲式的笑話,披露人與人,人與環境間不斷衍生的、破滅的。
此小說集雖非作者自傳體小說,也無作者的正面自白——書中,張大春完全似局外人,為讀者平淡敘述一個又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但正是這些貌似無奇的故事,顯示了作者的創作能量和藝術活力。

朋友
作者:余華《朋友》是余華小說裡尤其是描寫暴力的小說裡少有的帶有亮色的小說,這種亮色讓人會輕易陷入余華設給我們的陷阱。小說敘述了兩個男人在經歷一番惡鬥之後成為惺惺相惜的朋友的故事。也是余華沉寂七年之後發表的第一短篇。
其實故事本身並沒有透露什麼,關鍵是小說的敘述人——11歲的男孩「我」在敘述中流露出來的情感傾向和心理反應。崑山是一個可以借錢不還、攔路搶劫的十足的地痞,「連嬰兒都知道崑山這兩個字所發出的聲音和害怕緊密相連」,可「我」卻強調大家其實都喜歡崑山。儘管「我」沒有明說給大家——或者乾脆說「我」——為何會如此喜歡這樣一個明明可恨的人物,但從其後的敘述中我們不難找到答案。當崑山靠在橋欄上一邊吸煙一邊大口吐著痰時,他那種大大咧咧的樣子,還有他臉上像是風中的旗幟一樣抖動的肌肉,他厚實得連刺刀都捅不穿的胸膛,以及他的腿和胳膊,都使「我」為之入迷。顯然,真正讓我著迷的是崑山的蠻悍之力,而正是這種力量使崑山能夠在鎮上享有某種特權。接下來的敘述則更具有說服力:「這是一個讓我激動的中午,我第一次走在這麼多的成年人中問,他們簇擁著崑山的同時簇擁著我……那時我從心底裡希望這條通往煉油廠的街道能夠像夜晚一樣漫長,因為我不時地遇上了我的同學,他們驚喜地看著我,他們的眼光裡全是羨慕的顏色。我感到自己出了風頭。」
在「我」稚氣的驕傲裡包含著的正是對權力的渴望,儘管「我」對此還缺乏充分的自我意識。其後,「我」學著石剛的樣子提著濕淋淋的毛巾,在一幫同學的簇擁下,在學校的操場上走來走去,尋找挑釁者,那段日子之所以美好,就因為對成人暴力行為的模仿使「我」迅速地在自己的世界裡建立了權威,可見歡樂和陶醉都來自於權力。而這在余華的許多文本裡都有著類似的情感傾向。

河邊的錯誤
作者:余華一個被河溪環繞的小鎮上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殺人案,警察馬哲奉命去調查,不料案件陷入困境,整個小鎮都被恐慌的氣氛所籠罩……
小說以一種冷靜的筆調描寫死亡、血腥與暴力,並在此基礎上揭示人性的殘酷與存在的荒謬。

未完的懺悔錄
作者:葉靈鳳《未完的懺悔錄》是葉靈鳳的三部長篇小說之一。主要描寫韓斐君擔當不起歌舞明星陳艷珠的真愛,在自哀自憐中痛苦地消磨著青春的故事。小說採用靈活多姿的情節組合,又重於內心分析,從而突破了性愛題材的狹小性,顯示出獨特的審美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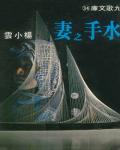
水手之妻
作者:楊小雲我愛,我寂寞;我等。
短短幾個字,是水手之妻的真愛宣言!
「水手之妻」串連三十段主旨相連貫的小說,說的是亙古不變的愛情,字裡行間流曳著至真與溫柔,細數書中夫妻二人的聚少離多,那種近似古詩描繪的「所思在遠道」,是哀愁、是心痛,令人不由得共掬一把同情之淚。
這位可人的妻子,帶點憨直,也有些癡傻,但有著異於常人的忠貞與毅力,為遠行的另一半守著這一個家,水手說她才是支撐他一切的「船長」,這種情懷在新世紀的今日更屬難得,尤彌足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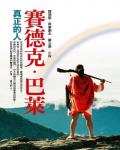
賽德克.巴萊
作者:魏德聖 嚴雲農在沒有信仰和自由的肉體裡,靈魂會因睏乏而死去!
如果有人逼迫你忘記不該忘的東西,你應該反抗、你應該戰鬥,你不該讓自己變成被豢養的野獸!
因為我們都是驕傲的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日本人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比森林的樹葉還繁密,可我反抗的決心比奇萊山還要堅定!」
對賽德克族而言,「紋面」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儀式,只有臉上有刺紋的人才能結婚擁有後代,死後也才能通過彩虹橋去見祖靈。賽德克男子必須「出草」獵回人頭、女子必須讓部落長老認同她的織布技術才能紋面,成為一個「賽德克.巴萊」,然而這樣重要的文化傳承卻在日本人來了之後被禁止了! 賽德克男子收起獵槍,被當做搬運重木的奴隸;女子被迫嫁給日本人,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當他們無法在自己的家園上抬頭挺胸,賽德克族偉大的領袖莫那魯道終於發出怒吼!為了保衛家園、找回尊嚴,一場視死如歸的浴血聖戰就要開始,賽德克.巴萊可以輸去他的身體,但是一定要贏得靈魂!
這是一個關於「夢想」的故事
小說裡的主人翁莫那魯道有一個夢想,就是將那些外來侵略者趕出賽德克族的土地,堅持驕傲的生存下去!小說幕後的主人翁「小導演」魏德聖也有一個「大夢想」,他想拍一部能讓國際影壇對台灣電影刮目相看的大製作,不僅叫好,更要叫座,讓不看國片的人都願意到電影院去!
於是他不惜傾盡積蓄、舉債度日,耗費二百萬去拍「五分鐘」的精華版電影來爭取投資,他要向大家證明,別人能,台灣電影也能!在二○○三年十一月的首映會上,這短短的五分鐘震撼了全場,觀者無不為之動容!隨後更在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佳評如潮!魏德聖朝他的「電影大夢」跨出了第一步,不認識他的人說他瘋了,認識他的人說他太傻,但他的熱情不滅、夢想無悔,他說:「一輩子真正想做的事能有幾件?如果現在不做,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這是一個關於「英雄」的故事
莫那魯道是賽德克族的英雄,也是台灣這塊土地永遠的英雄!他義無反顧地率領族人勇敢抵禦侵略者,以長矛弓箭、血肉之軀來對抗敵人的精良武器,終於用生命寫下撼動人心、流傳後世的壯烈史詩!魏德聖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範,他義無反顧地熱情追求自己的電影夢想,無怨無悔。我們每個人心底其實都曾有一部電影的夢想,但只有魏德聖無視外在環境的艱難橫逆,勇敢而堅持地走下去。而這本書,不但將是魏德聖的電影夢想最珍貴的紀錄,他的故事無疑也為我們未竟的夢想做了最動人的註腳!
魏德聖先生之原著劇本,再由嚴雲農先生改編成小說。本書以泰雅族英雄莫那魯道的生平與霧社事件為背景,清楚呈現做為一個「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是何等重要的事。故事內容不只是在描繪抗日事件,而在於讓讀者體會,原住民族群如何靠著信仰與祖靈的庇護,堅強又驕傲地生存下去。氣勢磅礡,具有史詩風格。
原著劇本作者魏德聖,台灣新生代導演,曾任楊德昌《麻將》副導演及電影《雙瞳》策劃。1999年以《七月天》驚艷台灣影壇;2004年,為了突破台灣電影市場受限於資金規模而無力拍攝大格局、大製作的現實困境,自籌250萬元資金,拍攝了《賽德克.巴萊》5分鐘試拍片,企圖證明台灣的影像創作實力,再次震驚台灣影壇。2008年推出個人首部劇情長片《海角七號》。

許地山小說選集
作者:許地山許地山早期小說取材獨特,情節奇特,想像豐富,充滿浪漫氣息,呈現出濃郁的南國風味和異域情調。他雖在執著地探索人生的意義,卻又表現出玄想成分和宗教色彩。2O年代末以後所寫的小說,保持著清新的格調,但已轉向對群眾切實的描寫和對黑暗現實的批判,寫得蒼勁而堅實。他的創作並不豐碩,但在文壇上卻獨樹一幟。
此選集中含《鐵魚的鰓》、《東野先生》、《商人婦》、《換巢鸞鳳》、《枯楊生花》、《補破衣的老婦人》、《命命鳥》、《三博士》、《無憂花》、《女兒心》等十篇。

玉官
作者:許地山許地山早年受過佛教思想的影響,早期的短篇小說,多以南洋生活為背景,有異域情調,故事曲折離奇,充滿浪漫氣息。
1939年發表的小說《玉官》,描繪了面對欲施暴的軍士挺身而出宣揚基督愛的教義的玉官的救世精神。小說主人公玉官是一個寡婦,成為基督教徒以後,整天四處奔波,不辭辛勞地四處傳播福音,最後不顧別人的勸阻,發願要孤身遠渡重洋。
由於作者對於佛學的感情、造詣很深,故他能從哲學的高度來理解和研究佛教,從而啟迪讀者獲得豐富而深邃的人生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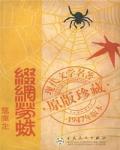
綴網勞蛛
作者:許地山《綴網勞蛛》講述童養媳尚潔逃離婆家后與長孫可望結為夫妻,后遭遺棄,到馬來半島獨自為生。長孫知錯,將尚潔接回,自己則去檳榔嶼贖罪。作品具有濃郁的宗教色彩和異域情調。

鳥語
作者:徐訏小說以回憶的方式敘述了一個傳奇唯美的故事。 「我」由於患了嚴重的精神衰弱而去鄉下迴瀾村休養。在那裡,「我」遇到了一個奇特的女孩子,這個被世人稱為「白痴」的女孩子不通世故無法融入塵世,她無法弄懂國語、算術、自然、地理等知識,卻有著一顆與自然貼近的心,她能聽懂鳥語,能夠理解詩中的情趣,並且透過文字進行詩意的賞析……

鬼戀
作者:徐訏《鬼戀》是徐訏旅法期間的作品,是他以「言情鬼才」開始蜚聲文壇的成功之作。作者充分調動了他善於編織曲折離奇神秘的「奇情、奇戀」故事的藝術才能,寫出了一段冷艷、淒迷的愛情故事,其中隱含著他對生命、人生的哲理思索。作品中那位自稱為「鬼」的女主人公,其容貌之美麗、氣質之冷峻、身世經歷之離奇,頗具仙氣或鬼氣。而故事中時時呈現的神秘、陰冷、瀰漫著森森鬼氣的藝術氛圍(如「我」兩次拜訪「鬼」的住所時所見所聞),以及女主人公在與「我」交往時表現出的忽冷忽熱、變幻莫測的性情,她的神出鬼沒、飄忽無定的行蹤,令讀者領略到一種撲朔迷離的聊齋藝術韻味。
一九九六年,導演陳逸飛把《鬼戀》改編為電影《人約黃昏》,由梁家輝、張錦秋領銜主演。

風蕭蕭
作者:徐訏徐訏 《風蕭蕭》曾居「暢銷書之首」,解放后卻被視為「特務文學」。小說將白蘋等放入抗戰的間諜鬥爭中,通過她們對國家與道德的忠貞選擇,塑造出理想的女性形象。本文將重讀這部小說,由白蘋之死分析出在救國與道德之間糾纏著的女性困境,這種理想的女性形象其實符合了傳統父權制對女性的期待。
徐訏 《風蕭蕭》於1943年3月起在重慶《掃蕩報》副刊連載,引起巨大轟動,居當年「暢銷書之首」。《風蕭蕭》在50年代曾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文藝受到嚴厲批判,甚至被視為「特務文學」而被打入文學的另冊。八十年代后,《風蕭蕭》調和雅俗的傾向、浪漫主義特徵、生命哲學意蘊等多重價值開始得到重視。本文將重讀這部小說,由白蘋之死分析出在救國與道德之間糾纏著的女性困境,這種理想的女性形象其實符合了傳統父權制對女性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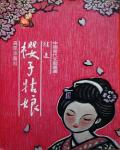
櫻子姑娘
作者:徐速本書是徐速先生繼《星星.月亮.太陽》後一部長篇鉅著。通過抗日戰爭時期一位日本少女——櫻子姑娘,在中國學校所發生的愛恨交織、凄艷動人的戀愛故事,從而對戰爭、和平、愛情、仇恨……這些困惑於當前人類心靈的諸大問題,提出莊嚴的探討和批判。本書出版後備受讚譽,成為香港少有的長期暢銷的文藝小說。
此外,本書於一九八一年被香港TVB改編成二十集電視連續劇《烽火飛花》,馮粹帆監製,鄭少秋、趙雅芝、呂良偉、馮粹帆領銜主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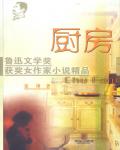
廚房
作者:徐坤本書以廚房是一個女人的出發點和停泊地講述了一個廚房的故事。一切的一切都已經寂滅,惟有心靈不可言說。廚房是一個女人的出發點和停泊地。
《廚房》中的枝子是一位事業成功的商業女星。她在年輕氣盛的時候曾十分厭惡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然而,事業成功以後,卻又開始「懷念那個遙遠的家中廚房,廚房裡一團橘黃色的溫暖燈光」。「他願意看見有一兩個食客當然是丈夫和孩子吃著她親手燒的好菜,連好吃都顧不上說,直顧低頭吃得滿嘴流油,腦滿腸肥。」她才會感到無比幸福。「愛上一個人,組成一個家,共同擁有一個廚房,這就是她目前的心願。」小說的核心故事即從這兒開始啟動。
重新對廚房感興趣的枝子從內心愛上了藝術家松澤——她自己的「經營品」。她不僅出資幫他辦畫展成功,而且還親自下廚房唱著鍋碗瓢盆的心靈交響曲,為松澤準備了一桌豐盛精美的生日晚餐。小說集中展示的即是這頓晚餐時的具體情形。
枝子一往情深地陶醉在嫋嫋升起的幻想裡,滿心都是幸福的甜蜜:這個渴望愛與被愛的女人幻想著男人盡情品嘗完第一道精美的生日晚餐後,下一個節目她仍會將自己的身體作為第二道靈魂與肉體的生日晚餐奉獻給他,而成為她終身可依的男人,留下這個「愛情」的永恆記憶。但是,男人松澤對枝子所抱的卻只是玩一玩的念頭:「在這個人人都趨功近利的時代,誰還想著給自己上套,給自己找負擔?尤其是對於他一個藝術家來說,更不願有任何形式的羈絆。家庭責任也好,社會義務也罷,能躲的就躲,能逃就逃,能推脫就推脫。」結局就可想而知了。當枝子被送回家之後:「眼淚,這時才順著她的腮邦,無比洶湧地流了下來。」沉浸在自己一廂情願愛情中的枝子,雖然對男人松澤俗惡的靈魂有所認識,但小說結尾時,枝子還是會拎著廚房的一袋垃圾直到自己家的樓門口,還緊緊地把它攥在手裡。這樣的細節,不知打動了多少讀者並編織出多少發人深思的意義。
關於「一袋垃圾」的細節,徐坤事先沒有設定的,只是寫著寫著寫到那裡,細節就自動從手指尖溜了出來。其實這正是女作家潛意識裡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形象一種令人「心痛」的女性關懷。

我們夫婦之間
作者: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發表於1950年《人民文學》第一卷第三期「新年號」上,是新中國第一篇城市小說;發表後反響強烈,多家報刊推薦轉載,很快被改編成話劇、電影 。這篇小說也較早地反映出了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農民意識對城市的本能排斥。
《我們夫婦之間》描寫知識分子丈夫與工農幹部出身的妻子在進城后的矛盾;中突及最終的相互理解、融合,描寫一瓢一飲的最日常、最普通的家庭瑣事,富有濃郁的人情味。蕭也牧的小說注重個人情感的細膩描繪,在當時的文藝界不啻一枝獨放的奇葩,由此招致猛烈的抨擊與批判,作者也因之獲罪慘死幹校。
從1951年至1970年,十九年的指責、白眼、迫害,直至慘死;所有這一切,只是因為一篇大約14000字的小說。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真實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