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死場
作者:蕭紅《生死場》是蕭紅的一部傳世名作,亦是魯迅所編「奴隸叢書」之一。魯迅在為《生死場》作的序中,稱它是「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文中對於人性、人的生存這一古老問題進行了透徹而深邃的詮釋。
其所描寫為「九一八」事變前後,哈爾濱近郊的一個偏僻村莊所發生的恩恩怨怨及村民的抗日故事,字裡行間描摹著中國人對於生命與死亡的掙扎。蕭紅以女性作者細緻的觀察角度,生動地寫出幾個農婦的悲慘命運。

塔裡的女人
作者:無名氏作者(無名氏)因情緒悶鬱,再訪華山,寓居玉泉院。初識覺空老道,但此道人很拒絕作者的接近,作者很是納悶。某個月夜,為了追尋夢境似的琴聲,作者循聲尋去,發現了一個秘密,彈琴人居然是覺空老道,這更堅定了作者的想法:這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在作者的懇請之下,覺空老道為作者講述了他的故事。
空覺老道原名羅聖提,十六年前南京著名提琴家,南京優秀的化驗專家,一身兼科學家和藝術家於一身,不能不說是矛盾而高難度的融合。「榮譽如一艘快艇,急速而平穩的載我往明亮的彼岸。」
在南京C女大建校五週年的一次晚會上,羅聖提突發奇想,著舊長衫赴宴,偶遇南京第一美女黎薇,她如一朵帶刺的玫瑰,視羅聖提為草芥,羅聖提自視見過美人無數,不服氣她的傲慢,便小小的惹了一番這刺玫瑰,未料竟因此結緣,他們兩位南京社交界的紅人有許多認識的機會,但他們都在極其巧妙的迴避。
黎薇打破了兩人之間的絕緣,她居然放下驕傲的武器前來找羅聖提學琴,看似平淡的半年交往實則兩位主人翁都是心潮暗湧,還是黎薇,率先坦露心懷,將她的心徹底的交付與羅聖提,羅聖提讀完她交與自己的日記,日記記載了一個少女火熱的激情和滿腔的愛戀,羅聖提被震驚,被點燃,他與黎薇如火如荼的戀情從此刻開始了。他們將戀情維持著地下狀態有一年半的時間,現實的陰影逐漸的上升了起來,很不幸的現實是羅聖提還在醫學院唸書時,既由家裡安排與同鄉的女孩結婚了,並且育有二子,離婚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和黎薇之間有這一個巨大的鴻溝,他為著黎薇的幸福,受人之託竟違心給她介紹了方(一位軍閥),黎薇受了巨大刺激,由愛而恨,憤而與對方結婚了。
抗戰爆發後,羅聖提飄零四方,只偶爾得知一些黎薇的近況,她的生活很不如意,方也並非想像中的可靠男人,只徒具虛名,他們的結合是羅聖提一手促成,這世上也唯有當事人方能理解親手將自己愛的人送與他人的痛苦吧。羅聖提生活在深深的苦痛之中,對黎薇滿懷歉疚,在得到黎薇離婚的消息後,羅聖提終於對自己從前的所為做了深刻反省:我必須找機會償還欠黎薇的情感,我們還來得及找回幸福!
當眼前出現光明的曙光時,人還未啟程,現實往往捷足先登,告訴人生活有多麼殘酷!羅聖提先尋著黎薇的父母,在自己的苦苦請求下,得到了黎薇的地址,經歷舟車輾轉勞頓,終於尋找到了黎薇隱身的學校,但羅聖提看到的是一個破碎的夢,任何人看到這一段,都不能不從心底深處歎息、惆悵:「這女人穿著厚厚棉袍¦¦全身顯得臃腫,笨重,脊背也有點駝¦¦從外表看來,這女子至少已有五十左右¦¦她的整個絕望形態,情態,使我聯想起一顆死滅的星球,沒有光、沒有熱、沒有運動、沒有引力,所有的只是又黑暗又空虛的一團¦¦」「這絕不是薇!」是的,這已不復是薇了。她只是輕輕說了一句:「我饒恕你。」「過去」是如此殘忍,它完全粉碎人們的現實生命,不留一點殘骸。
這就是羅聖提為什麼出現在華山的因由,現在羅聖提決定把他的秘密託付給作者,隨作者處置。
無名氏掩卷後久久不能釋懷:「在這世界上,我們還能有不釋手的東西麼?」
誰都不能給出完美的答案。能用自己手心撐握的就應當給予他們最用心呵護和最深沉的愛戀,如此美好的愛情,不該放手時卻撒手了,愛情的花朵在塵世的泥污中,鉛華褪盡,盡染沉污,除了惋惜,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挽救它出於這塵俗?
本書於一九七六年改編為電影,李翰祥執導。另於一九九○年被臺灣中視改編為電視連續劇播出。爾冬陞飾羅聖提,宋岡陵飾周薇。

上海寶貝
作者:衛慧《上海寶貝》採取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情節主要是描述上海女作家CoCo與中國男友「天天」、德籍男友馬克的戀情。天天是CoCo的知心人,卻是性無能(象徵衰微的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是駐上海外商,有家室、超強的性能力、西方男子對女性的體貼(象徵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對歐美強勢文化的崇拜、對外資的倚賴?)。馬克誘惑了和「天天」同居的CoCo。CoCo擺盪在「天天」的同志情誼和馬克雄壯的肉體誘惑之間,最後「天天」因吸毒死亡,馬克返回德國,CoCo的雙線感情於此告終。
這部作品的藝術性不在三角戀的通俗情節,而在女主角對「情慾自主」的自覺歷程、對藝術家創作與生活關係的省察、對上海這個現代都會風情的捕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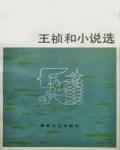
伊會唸咒
作者:王禎和寡母阿緞和兒子小全過著委屈而安份的日子,但為了不賣房子而得罪李議員,被一再的欺壓,但始終不妥協。抗爭的結果雖是勝利,但勝利的原因是耐人尋味的「神鬼意識」之作崇。本篇小說有警世之意,也希望「建立真正的法治精神,不必再『禱神雪冤』,祈求冤情大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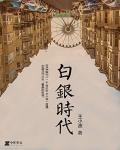
白銀時代
作者:王小波《白銀時代》是《時代三部曲》之二。
這是由一組虛擬時空的作品構成的長篇。這組作品寫的是本世紀長大而活到下世紀的知識分子,在跨世紀的生存過程中,回憶他們的上輩、描述他們的上輩、描述他們自己的人生。與其說這是對未來世界的預測,不如說是現代生活的寓言,是反烏托邦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未來世界不僅不比現在更好,反而變本加厲地發展了現代生活中的荒謬。知識分子作為個體的人,被拋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兩套敘述,在一套敘述中,他描寫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畫家、小說家,以及他們不同尋常的愛情;另一套敘述,則描寫他自己作為未來的史學家,因為處世要遵循治史原則而犯下種種「錯誤」,最後他回到原來的生活、身分,成了沒有任何慾望的「正常人」。這兩套敘述時時交叉、重合。在所謂的寫實與虛構的衝突里,作者創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諷、調侃和遊戲性分析的情境來。
《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是王小波作品的精華。 「時代三部曲」表面上是王小波作品的合集,每部之間似乎沒有什麼聯繫,但其實是有一個邏輯順序的。這個邏輯順序就是:《黃金時代》中的小說寫現實世界;《白銀時代》中的小說寫未來世界;《青銅時代》寫的故事都發生在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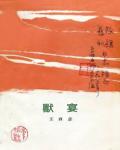
獸宴
作者:王西彥《獸宴》寫於1939年,收1940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夜宿集》。
小說借學校總辦公室內的一場酒宴,寫出了大時代洪波中的一小片浮漚。內中的所有人物,無一不是昏沉無聊者,無一不是藉著「為人師表」的招牌,顯露著污濁的靈魂。正如小說結尾華大容的感嘆,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內──「這班禽獸不如的東西……」
高度的諷刺藝術是這篇小說最重要的特色。群醜圖的構思,使作者並不訴諸典型的創造,甚至也不訴諸事件的進展,基本上是採用速寫的方式,以表現場面的氣氛和這群醜類共通的特徵為趨赴。作者選擇精微的細節,稍稍加以誇張性的勾勒,著力追尋諷刺的效果。《獸宴》上的所有角色,作者都別緻地冠以極有個性的綽號,相當貼切生動;兼而敘述從容自如,尖刻的嘲諷縱橫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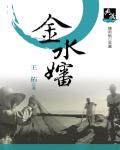
金水嬸
作者:王拓立法委員王拓成名作,曾改拍為電視劇,為台灣鄉土文學的代表作。
台灣鄉鎮母親永恆的形象,鄉土寫實文學的里程碑
《金水嬸》寫的是一系列圍繞著台灣基隆海濱八斗子,這個依海為生的小村落的故事。描述漁民生活的貧困、刻苦及堅韌的生命力,反映漁民的迷信、愚昧、無知、自私、無奈,刻劃教育界、知識份子或上階層人物的私慾、醜陋的行徑,表現了處於工商社會拜金主義下個人的感傷及人性的扭曲。
《金水嬸》雖是彰顯母愛及女性生命力的作品,但是金水嬸含辛茹苦養大的幾個兒子,在城裡過富足的生活後,對身陷困境的父母竟是萬般逃避。他們捨棄了貧窮,連親情也一併捨棄了。
王拓寫《金水嬸》,細譜台灣鄉鎮母親永恆的形象,更為台灣文學開拓一個新方向,肇生了鄉土文學運動,是寫實文學的一個新里程,一方小而醒目的碑記。王拓的小說,便是充滿著對這種貧困中人們的解析:蠶食他們的愚昧、迷信、疾病和絕望,以及他們強韌的生之毅力。
《金水嬸》是王拓最著名的小說之一,它的故事題材正是取材自他的母親。在並不長的篇幅裡,王拓細膩的刻劃了一個勤勞、樸實、守份、堅忍的台灣傳統婦女《金水嬸》。它的故事題材是取材自王拓的母親。他成功的寫出在現代功利社會的衝擊下,金水嬸因為舉債投資失敗而導至家庭破碎,丈夫死亡的慘劇。也寫出由於傳統的倫理衰微,以至成家立業的子女任憑父母在困境中掙扎而不伸出援手的悲涼。王拓寫作技巧高明,在看似平淡中蘊藏著深厚的諷刺與悲憫。
《金水嬸》亦於一九八七年改編為同名電影上映。

堅硬的稀粥
作者:王蒙一九八九年,王蒙發表了短篇小說《堅硬的稀粥》,引起很大爭論。作品寫的是一個年輕人,他認為中國足球水準太差,是因為中國人體質太差,而體質差是因為早飯喝稀飯吃鹹菜缺乏營養,他提議應由稀飯鹹菜改為喝牛奶吃牛肉,由此引起了一場家庭地震。王蒙本人說,此文是根據真人真事寫成。巴金則說這篇小說「已成世界名著」。

單身溫度
作者:王鼎鈞本書曾以《單身漢的體溫》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由大林書店出版,後大林一度將書名改為《白如玉》。民國七十六年八月,本書之著作權經作者購回。民國七十七年四月,改交爾雅出版社以《單身溫度》重排重印。所以,三個名字是同一本書,特此說明。
本書由十二個故事組合而成,以一個叫華弟的人物貫串全書,主角是十二位不同的女性,透過十二種性格、相貌截然不同的女性所發生的故事,反映五○年代社會問題與時代變遷。這十二個短篇故事雖是橫斷的,但不是絕緣的,他們互相詮釋演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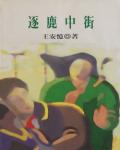
逐鹿中街
作者:王安憶表面上,他們是同床共枕,人人稱羨的夫妻;暗地裏,卻一個追一個逃,終日在上海市的千門萬戶之間穿街走巷,彼此跟蹤鬥智,彷彿一對不共戴天的死敵……
什麼樣的男女關係世界,才是女人的理想?王安憶,大陸當今最富才氣也最具爭議的女作家之一,在這本著作中細細描繪了小市民的奮勇戰鬥,以及一場場現代人世的浮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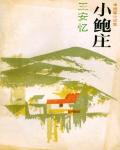
小鮑莊
作者:王安憶《小鮑庄》原載《中國作家》1985年第二期。
《小鮑庄》描繪了兩個普通村莊中人們的生活和他們之間形成的社會關係,揭示了歷史的發展和變遷。《小鮑庄》發表后曾引起文壇強烈反響,顯示了作者在創作上的探索和突破。作者力求作品生活化,雖無明顯的情節,卻更貼近於現實生活,內涵豐富,主題含蓄,具有歷史的縱深感。
《小鮑庄》以多頭交叉的敘述視角,通過對淮北一個小村莊幾戶人家的命運和生存狀態的立體描繪,尤其是撈渣這一人物具有象徵意義的死,剖析了傳統鄉村世代相傳的以「仁義」為核心的文化心理結構。作品展現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義」精神中包含有善良、忠厚、團結、抗爭等美好素質,但也對其中諸如順天從命、愚昧迷信等文化劣根性進行了反思。 《小鮑庄》被視為20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品,但比一般 「尋根小說」有著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

蜀道難
作者:王安憶《蜀道難》敘述一對私奔的男女,在搭乘渡輪沿著長江三峽離開四川的過程裡,因為急切地想要了解對方,並透過這了解穩定私奔的決定,然而愛情終究如蜀道一般難行,兩人的和諧關係產生了變化。當船行到了終點時,兩人也隨之分手,短暫的愛情在旅程中猶如一個奇異的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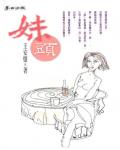
妹頭
作者:王安憶小白,妹頭,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順其自然地結為夫婦。他們一個成了小有名氣的文論家,一個變為走南闖北的生意人。他們的分手,表面上因為妹頭的婚外戀,實際上仍然是理想世界和世俗生活的衝突。當妹頭準備移民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時,這個平凡的愛情故事突然走出了真實,因為它失去了上海。這正是王安憶試圖描述的中心。王安憶最擅長的,就是對極細小瑣碎的生活細節的津津樂道中展現時代變遷中的人和城市。

好婆和李同志
作者:王安憶《好婆和李同志》藉由好婆與李同志的兩個本地與外來家庭的生活方式對比,呈現出上海市民與外來移民者價值衝突。從穿著打扮、家居生活的精緻程度,到桌上的食物……等等,李同志一家的習慣與作風皆與道地的上海人不同,不僅李同志成為本地人閒話的對象,李同志這名上海移民,亦缺乏對上海的認同,衝突於焉漸漸顯題。

悲慟之地
作者:王安憶王安憶從80年代初在新時期文學中脫穎而出,到世紀之交的今日,近20年的歲月過去了,在文學的土壤中,她保持了一種不斷生長的狀態。
在寫作長篇的同時,她又偏愛起了短篇小說。短篇小說確實是一個有限的藝術空間,是作家在寫作技術上的角力場,因此,王安憶不斷開寫短篇,其實就是不斷試刀的過程,以一把鋒利的小說刀,裁剪生活的料。她的寫實的技巧,敘述的技巧,塑造人物的技巧,其實就是小說的技巧不斷地激活和發展,擁有更大的空間與高度。這可能是《發廊情話》、《悲慟之地》等作品的意義。
《悲慟之地》描寫了幾個外鄉農民到上海賣生薑的經歷,王安憶刻畫了他們眼中的上海與上海城市生活中的他們。

雞鴨名家
作者:汪曾祺《雞鴨名家》寫了余老五和陸長庚兩個風俗人物,表現了作者對大千世界萬物的欣賞,以及對普通人的關心與尊重之情。
這些大量存在的芸芸眾生,比地球表面的雞鴨還要多,他們生死富貴,禍福難料,在汪曾祺筆下匯聚成中國小人物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