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幕
作者:保真本書為水幕所著中短篇小說集,包括了中篇小說《水幕》,短篇小說《班代表》、《初戀的故事》。
其中小說《水幕》曾獲中國文藝協會小說獎章。

遠方有個女兒國
作者:白樺這是一部從形式到內容都十分新穎獨特的長篇小說。小說的主軸有二,一是在「謝納米」湖畔(瀘沽湖)的摩梭族少女「蘇納美」在十三歲前後,如何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於摩梭族的騷擾、成年禮、走婚,最後因為善於歌舞成為文化工作的一員,離開了家鄉在各地跳摩梭族的傳統舞蹈。另一條主軸則是以一位美術系大學生「梁銳」為主角,講述他如何經歷文化大革命裡的改造教育、鬥爭與黑獄,並在最後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而獲得釋放,在遙遠的省分裡遇到蘇納美,最後還愛上了她。
作品通過蘇納美和梁銳的愛情悲劇,生動地描述了至今仍保留著母系大家庭形式的摩梭人的遠古習俗,真實地再現了「文革」中的種種怪誕,提出了古老與現代、野蠻與文明、婚姻與愛情,以及人性等值得深思的問題。
此書甫一出版即引起不少迴響,原因有二:一,這是第一本以摩梭族文化為架構的小說,讓一般民眾能透過文學認識這個少數民族;二,這本書也正面回應了文革時期的種種,勾起不少長輩對於那個動盪年代的回憶。

秋
作者:巴金本書為巴金所著「激流三部曲」第三部《秋》。
《激流三部曲》以五四運動后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地區為背景,描寫了在新的革命時期的一個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潰的歷史。作品展開了一個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全部,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墮落和封建禮教的虛偽殘酷。作者塑造了梅、蕙、瑞珏等封建家庭婦女的形象,她們的痛苦與慘死,是對封建婚姻制度和舊禮教的血淚控訴。而鳴鳳、倩兒等「下人」的死,則更深刻地揭露了階級歧視和壓迫的社會現實。作品沒有停留在暴露這個「家」的罪惡、揭示它必然崩潰的命運上,而進一步描寫了以覺慧為代表的覺醒的叛逆的一代。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五四」時期的時代特色,「宣布一個不合理制度的死刑。」
《秋》講述了蕙的靈柩停在廟中已經一年多,她的丈夫忙著續絃,根本沒想到要讓她入土為安。在覺新與覺民的 「威脅」下,蕙才得到存身之地。她糊塗的父親又將兒子枚推入火坑,枚才十七歲,就有了肺病的跡象,父親周伯濤不願承認兒子有病,卻忙著給他娶了馮家的小姐為妻,兩人感情不錯,但妻子脾氣很大,枚夾在她與長輩間受氣,婚後不久就因病去世,留下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兒。
三房的克明在女兒跑後有所悔悟。兩個弟弟卻想賣掉公館分家,兒子又不爭氣,克明在鬱悶中丟下懷孕的妻子去世。淑英的丫頭翠環敬佩覺新為人,三太太決定將她給覺新。
高公館賣掉了,高家四分五裂,在覺新給覺慧與淑英的信中,他寫到各房的情況。四房五房繼續著荒誕的生活,幾個堂弟依然頑劣成性。
三房與他們住得很近,保持著親密關係。他自己娶了翠環並將她當作妻子看待,至於覺民與琴,也按他們的意願舉行了新式婚禮並即將出外工作。

春
作者:巴金本書為巴金所著「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
《激流三部曲》以五四運動后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地區為背景,描寫了在新的革命時期的一個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潰的歷史。作品展開了一個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全部,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墮落和封建禮教的虛偽殘酷。作者塑造了梅、蕙、瑞珏等封建家庭婦女的形象,她們的痛苦與慘死,是對封建婚姻制度和舊禮教的血淚控訴。而鳴鳳、倩兒等「下人」的死,則更深刻地揭露了階級歧視和壓迫的社會現實。作品沒有停留在暴露這個「家」的罪惡、揭示它必然崩潰的命運上,而進一步描寫了以覺慧為代表的覺醒的叛逆的一代。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五四」時期的時代特色,「宣布一個不合理制度的死刑。」
《春》講述了覺慧逃出家庭後獲得了自由,但家中的悲劇還在一幕幕上演。覺新兄弟的繼母周氏的娘家人來到成都,要為覺新的表妹蕙完婚。蕙是聰明美麗的女孩,卻被頑固的父親許給荒淫的陳家,大家都替她惋惜,覺新在她身上看到梅與玨的影子,卻無力幫助。
這時,覺新的愛子海兒不幸病死,他對生活更加沒有了信心。覺民與琴則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並鼓勵家中的弟妹走出家庭。
三房的淑英被父親許給馮家,她極力想掙脫不幸的命運,甚至想過效仿鳴鳳去死,覺民與琴決心幫助她脫離家庭,去上海找覺慧。蕙完婚後過著不幸的生活,很快就患病,因為婆家不肯請西醫耽誤了醫治,默默地死去。蕙的死再次刺激了覺新,也使他開始支持覺民等人的計劃。
最終,淑英在覺民等的幫助下,被護送到了上海。在《春》的結尾,覺新等人收到她從上海的來信,信中傾吐了她獲得自由後的幸福。

家
作者:巴金本書為巴金所著「激流三部曲」第一部《家》。
《激流三部曲》以五四運動后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地區為背景,描寫了在新的革命時期的一個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潰的歷史。作品展開了一個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全部,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墮落和封建禮教的虛偽殘酷。作者塑造了梅、蕙、瑞珏等封建家庭婦女的形象,她們的痛苦與慘死,是對封建婚姻制度和舊禮教的血淚控訴。而鳴鳳、倩兒等「下人」的死,則更深刻地揭露了階級歧視和壓迫的社會現實。作品沒有停留在暴露這個「家」的罪惡、揭示它必然崩潰的命運上,而進一步描寫了以覺慧為代表的覺醒的叛逆的一代。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五四」時期的時代特色,「宣布一個不合理制度的死刑。」
《家》描寫舊式封建家庭的解體和青年人的反叛。故事集中在1920年冬到1921年秋的八九個月時間里,揭露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撕開了在溫情關係掩蓋下的大家庭的勾心鬥角,暴露了所謂"詩禮傳家"的封建大家庭的荒淫無恥,也描寫了新思潮聽喚醒的一代青年的覺醒和反抗,從而宣告了這個封建大家庭必然崩潰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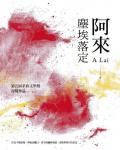
塵埃落定
作者:阿來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壩地區,當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統治著,麥琪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老麥琪土司有兩個兒子,大少爺為藏族太太所生,英武彪捍、聰明勇敢,被視為當然的土司繼承人;二少爺為被土司搶來的漢族太太酒後所生,天生愚鈍、憨癡冥魯,很早就被排除在權力繼承之外,成天混跡於丫環娃子的隊伍之中,耳聞目睹著奴隸們的悲歡離合。
麥琪土司在國民政府黃特派員的指點下在其領地上遍種罌粟,販賣鴉片。很快暴富,並迅速組建了一支實力強大的武裝力量,成為土司中的霸主。
眼見麥琪家因鴉片致富,其餘的土司用盡心計,各施手段盜得了罌粟種子廣泛播種,麥琪家的傻少爺卻鬼使神差地建議改種麥子,於是在高原地區漫山遍野罌粟花的海洋裏,麥琪家的青青麥苗倔強的生長著。
是年內地大旱,糧食顆粒無收,而鴉片供過於求,價格大跌,無人問津,阿壩地區籠罩在饑荒和死亡陰影下。大批饑民投奔到麥琪麾下,使得麥琪家族的領地和人口達到空前的規模。傻子少爺也由此得到了女土司茸貢的漂亮女兒塔娜,並深深地愛上了她。就在各路土司日坐愁城,身臨絕境之時,卻傳來二少爺開倉賣糧,公平交易的喜訊。
各路土司雲集在二少爺的官寨舉杯相慶、鑄劍為犁。很快在二少爺的官寨旁邊出現了幾頂帳篷,進而是一片帳篷,酒肆客棧、商店鋪門、歌榭勾欄、甚至妓館春樓,應有盡有。在黃師爺(當年的黃特派員)的建議下,二少爺逐步建立了稅收體制,開辦了錢莊,在古老封閉的阿壩地區第一次出現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商業集鎮雛型。
二少爺回到麥琪土司官寨,受到英雄般的歡呼,但在歡迎的盛會上,卻有大少爺那令人不寒而慄的陰毒的眼光。一場家庭內部關於繼承權的腥風血雨又悄然拉開了帷幕。
終於,在解放軍進剿國民黨殘部的隆隆炮聲中,麥琪家的官寨坍塌了。紛爭、仇殺消彌了一個舊的世界終於塵埃落定。
本書改編的同名電視劇集於2003年播出,並於2006年由香港舞蹈團改編為舞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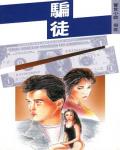
騙徒
作者:倪匡馬扁是一個天生的騙子,五歲就已在街上向成年人騙取金錢。武術大家封二先生看到馬扁自小練成鋼皮鐵骨的身體,資質奇佳,且智力過人,決定照顧他。
封二先生的三師弟蔡伯號稱天下第一巧手,大師兄金老實,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騙術之精,舉世無雙。馬扁拜了他們三人為師父,並且有一個師姐及師妹,分別名為諸弟及王燕。他們相識第一天,馬扁就藉「種錢術」騙了她們的金錢。
馬扁、諸弟及王燕在三名師父的教導下,進步神速,到了少年時期,三人關係變得敏感,馬扁周旋於兩女之間,他的騙術又能否幫助他呢?
《騙徒》共十章,每一章的最後,都有「騙徒語錄」及「反面教育」,是倪匡智慧及經驗的精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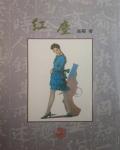
紅塵
作者:高陽《紅塵》於民國五十三年一月出版,是高陽嘗試揉合間諜與愛情為題材的一部現代背景的長篇小說,但以人性貫串期間,因而顯得意境高超,趣味雋永。至於人物刻畫之生動,情節安排之詭譎,場景描寫之簡鍊,這些高陽小說中的特色,當然完全表現在本書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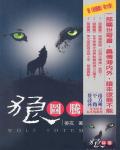
狼圖騰
作者:姜戎《狼圖騰》由幾十個有機連貫的「狼故事」組成,情節緊張激烈而又新奇神秘。讀者可從書中每一篇章、每個細節中攫取強烈的閱讀快感,令人慾罷不能。
那些精靈一般的蒙古草原狼隨時從書中呼嘯而出:狼的每一次偵察、布陣、伏擊、奇襲的高超戰術;狼對氣象、地形的巧妙利用;狼的視死如歸和不屈不撓;狼族中的友愛親情;狼與草原萬物的關係;倔強可愛的小狼在失去自由后艱難的成長過程——無不使我們聯想到人類,進而思考人類歷史中那些迄今縣置未解的一個個疑問:
當年區區十幾萬蒙古騎兵為什麼能夠橫掃歐亞大陸?
中華民族今日遼闊疆土由來的深層原因?
歷史上究竟是華夏文明徵服了游牧民族,還是游牧民族一次次為漢民族輸血才使中華文明得以延續?
為什麼中國馬背上的民族,從古至今不崇拜馬圖騰而信奉狼圖騰?
中華文明從未中斷的原因,是否在於中國還存在著一個從未中斷的狼圖騰文化?
於是,我們不能不追思遙想,不能不面對我們曾經輝煌也曾經破碎的山河和歷史發出叩問:
我們口口聲聲自詡是炎黃子孫,可知「龍圖騰」極有可能是從游牧民族的「狼圖騰」演變而來?
華廈民族的「龍圖騰崇拜」,是否將從此揭秘?
我們究竟是龍的傳人還是狼的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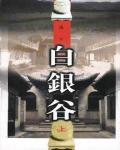
白銀谷
作者:成一明清兩朝的商業,素以南徽北晉並稱於世,而西幫商人(晉商)獨創的票號,更有著秘史般的金融傳奇。這部《白銀谷》全景式地再現了晉商望族的商業活動、社會關係、個人隱秘等諸般形態;對豪門深藏的善惡恩怨、商家周圍的官場宦海、士林儒業、武林鏢局、西洋教會都有豐滿鮮活的描繪。
《白銀谷》的主角明清時代的(山)西幫商人,他們獨創的票號,是清代的一個金融傳奇。胡雪巖因仿辦票號,成就了他個人傳奇的一生,但他成也票號,敗也票號。西幫以「博學、有恥、腿長」面世,以「賠得起」聞名,在它的大本營祁太平,似胡雪巖這種等級的富商財主,則是一個群體。票號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金融行當,它視同時期的東西洋銀行為異類。但它在自己生存的社會裡,又屬異質。
本書也談到庚子年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並沒調來重兵,總共也就一兩萬人馬,更未正經結為聯軍。等攻下京城,八國還是八股軍,各行其是。直到快入冬了,德帥瓦德西才來華就任聯軍司令。但庚子賠款的總數是四萬萬五千萬,議定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摺合下來,總共是九萬萬八千萬兩!

儒林園
作者:古華一齣風雲詭譎、生死沉浮的人生大戲……
古華說:《儒林園》寫的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也是我自己和我父輩們的命運。當然範圍要廣泛得多。有人說《芙蓉鎮》類似國畫的工筆加寫意,通過一村又一鎮為時代縮影;我想《儒林園》則有點類似大潑墨,大色塊,以一座千古天牢為人物命運的出發地,集南方北方、城市鄉村、內地邊陲,各個階層一對對小兒女的生死恩怨於一園,來寫社會的大災變,時代的大悲劇……

貞女
作者:古華古華的小說,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風情習的描寫細膩翔實,故事情節極富傳奇,十分引人入勝,人物性格鮮明,對話幽默詼諧,深刻揭示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他的小說可讀性極,高深獲讀者喜愛。 本書收入<貞女>、<「九十九堆」禮俗>和<霧界山傳奇>等三部中短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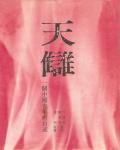
天讎
作者:凌耿《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英文著作文革紀實長篇小說,作者凌耿以紅衛兵(「廈八中」頭目)第一人稱紀錄,詳實寫出文革初期(1966年—1968年)經過,包括:福建紅衛兵鬥爭省黨委韓先楚、全中國9次紅衛兵「大串聯」、波希米亞式的浪漫到北京謁見毛主席,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頭鑽動、一片紅(毛語錄)盛大熱烈場面、批鬥王光美(清華大學紅衛兵主斗,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829公社」至北京助斗)、數百名不同派系紅衛兵持械武鬥廝殺殘忍場面、最後18歲女友「梅梅」擔任戰場護士卻不幸中彈身亡,導致18歲的凌耿萬念俱灰跳海游泳至金門大擔島,投奔台灣成為當年國民黨樣板宣傳人物……
天讎為兩岸第一本關於文革的小說,美國《紐約時報》、中華民國蔣故總統 經國先生當年皆推薦此部小說。最初發表時,為單篇英文文章"The Making of a Red Guard",由《紐約時報》於1970年發表,隨後於1972年發表"The Revenge of Heaven:Journal of a young Chinese."與中文譯本是香港新境傳播出版發行的天仇,譯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劉昆生和丁廣馨。後來因書中紅衛兵的食宿和國民政府的文宣不合,所以書給查禁了。自此文革小說罕見,直待陳若曦的《尹縣長》及古華的《芙蓉鎮》出版,我們方才再見。中文譯本是香港新境傳播出版一九七○年發行(後又數刷版再印)。
2016年2月,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社邀請原作者郭坤仁重新出版中文原著版本,並加1970年後的紀實與當時照片,命名為《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

穆斯林的葬禮
作者:霍達一個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間的興衰,三代人命運的沉浮,兩個發生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內容卻又交錯扭結的愛情悲劇。
這部五十余萬字的長篇,以獨特的視角,真摯的情感,豐厚的容量,深刻的內涵,冷峻的文筆,宏觀地回顧了中國穆斯林漫長而艱難的足跡,揭示了他們在華夏文化與穆斯林文化的撞擊和融合中獨特的心理結構,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圍中對人生真諦的困惑和追求,塑造了梁亦清、韓子奇、梁君壁、梁冰玉、韓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豐滿的人物,展現了奇異而古老的民族風情和充滿矛盾的現實生活。作品含蓄蘊藉,如泣如訴,以細膩的筆觸撥動讀者的心靈,曲終掩卷,迴腸盪氣,餘韻繞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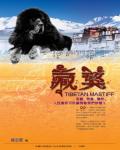
藏獒
作者:楊志軍喜歡養狗嗎?知道什麼是藏獒嗎?《藏獒》是以狗為主角的小說。
藏獒是產於青藏高原的一種大型獵犬,被譽為「中華神犬」,由一千多萬年前的喜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變而來的高原犬種,是犬類世界唯一沒有被時間和環境所改變的古老的活化石。牠曾是青藏高原橫行四方的野獸,直到六千多年前,才被馴化,開始了和人類相依為命的生活。
《藏獒》講述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隻獒王如何消除兩個草原部落之間的矛盾的故事,宣揚了和平、忠義又不失勇猛的精神。
在楊志軍的筆下這群比人類更珍惜人性的藏獒的快樂和悲傷、尊嚴和恥辱、責任和忠誠,凝聚了青藏高原的情懷、藏傳佛教的神秘、人道作家的悲憫,和傳奇巨著的酣暢。

半生緣
作者:張愛玲《半生緣》講的是三十年代上海的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女主人公顧曼楨家境貧寒,自幼喪父,老小七人全靠姐姐曼璐做舞女養活。曼楨畢業后在一家公司工作,與來自南京的沈世鈞相愛,世鈞深深同情曼楨的處境,決定與之結婚。曼璐終於也嫁人了,姐夫祝鴻才是個暴發戶,當得知曼璐不能生育,便日生厭棄之心,曼璐為了栓住祝生出一條殘計……十八年在天才作家張愛玲的筆下一晃就過去了,曼楨和世鈞又在上海相遇,而歲月變遷綠樹早已成蔭……
本書收錄張愛玲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初載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亦報》,題《十八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亦報社出版單行本;經張愛玲改寫后,以《惘然記》為題連載於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七月《皇冠》月刊,一九六九年七月皇冠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改名《半生緣》。